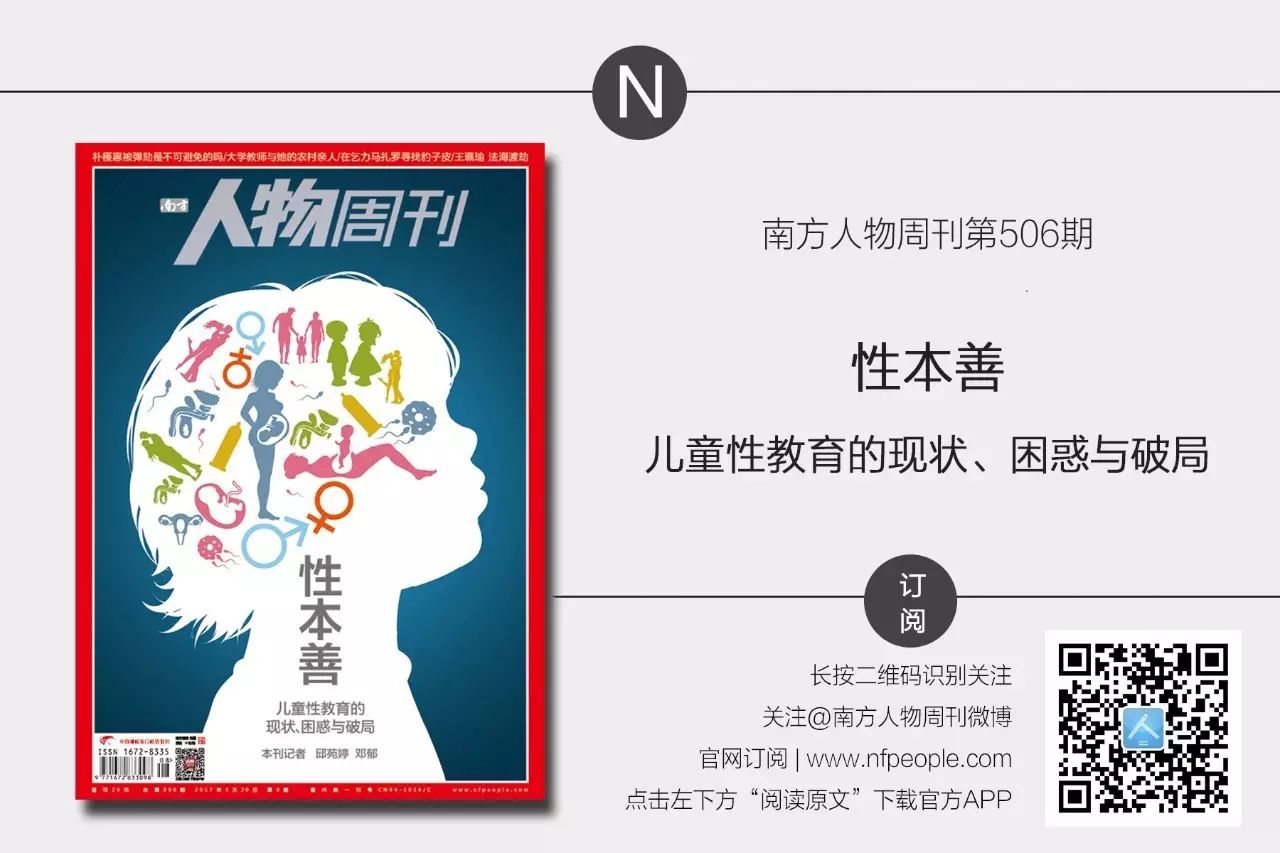德瑞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30年生于圣卢西亚,加勒比地区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曾被布罗茨基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 人”,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7年3月18日去世。
殖民者在掠夺、压榨和毁灭的同时也赋予了此间的草木以名字,所以他们成为“混种”,名为土生土长的圣卢西亚人,身上却不知有多少来自非洲和欧洲的血液。
地理会影响心理,这是常识。比如在岛屿上生活,岛民会产生两种极端的心态。一种视大海为包围圈,海水会逐渐上涨,淹没脚下的地面,或者成为海那边大陆的阻隔,那边的人时刻在觊觎这边——总之海意味着威胁。另一种则拓展了“家园”、“土地”的涵义,将海视为流动的陆地,是与棕榈树、沙滩、渔船、房屋、水果、土著人的水罐构成的人居版图的一部分。
德瑞克·沃尔科特,当然属于后者。
文学很有意思。读者永远需要听新故事,哪怕一百个作家翻来覆去都写父母子女夫妻邻里的那点事,读者也永远对诗有兴趣,哪怕一百个诗人都写大海、阳光、沙滩、棕榈。沃尔科特写大海,跟其他大诗人比如聂鲁达写大海,比如圣-琼·佩斯写大海,都不一样。现今美国最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亚当·基尔什,曾从沃尔科特不同阶段的作品里抽出关于大海的描写比照着读,那真是趣味盎然:
十来岁时的诗人,出了自己第一本诗集——一本名叫《25首诗》的小册子时,他看到的大海是“奶白色海湾的/浑圆的乳房。”二十多岁时,沃尔科特看到“绿波不留痕迹地漫过沙滩”,听到“水声咬啮着明亮的石头。”三十多岁时,水变成了“大海那穿白色法袍的唱诗班/走进它的中殿,来到一个/轻雾袅袅的香炉前”,或者,“这纯粹的光,这纯净的/无限而又无聊的天堂一般的大海。”随着星移斗转,意象积累起来:“一页又一页,大海/是一本书,被一个不在场的大师翻开”;“浅滩的被仔细地折出褶子/端正地列队行进”……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看到了不一样的海。年轻时是性感的,热烈的,急于同自己发生关联的,有了一点阅历后,就可以把大海看作一个安然的、自在的客体,年事渐高时,海与海边的景物又被诗人拿来总结自己的人生。《25首诗》是这位岛屿诗人的习作,因为他后来成了大名,也被拿来仔细研读过;《巴黎评论》用一篇专访宣告了沃尔科特位于最杰出的文学家之列,在其中,诗人说了他最早写诗时模仿的是英语现代派,是奥登,是艾略特,“某日我会像斯彭德一样写,改一天我又会像迪伦·托马斯一样写,我觉得我写得够多了的时候,就要拿去出版。”
他出生的圣卢西亚岛是没有出版社的,事实上,整个加勒比海地区都没有出版社。他问妈妈拿了钱,跑到特立尼达去打印出了自己的25首诗,回来卖给了朋友们。这年他19岁。
这堆岛屿就像美洲大陆撕裂成南北美洲时散在中间的一堆屑末,很容易被忽略。离他们很近的美国人,对加勒比的印象就是去那儿得带足防晒霜,看打扮得姹紫嫣红的棕肤姑娘和着鼓声跳林波舞,一种用于取悦度假者的异国风情罢了。但是这里也有文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大一小两个岛组成的共和国,2001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VS奈保尔就生在这里;196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语诗人圣-琼·佩斯则生在离圣卢西亚不远的瓜达卢普岛,血统高贵,在仆从车仗的簇拥下一步步成长为未来的外交官。
聂鲁达也是诗人外交官,也是大海之子。沃尔科特没有佩斯那么富贵,也不像聂鲁达那样,身无分文都敢烂醉在异国他乡的港口做美梦,但是,那种随时可以浪迹天涯的丰足感,他也有。他们是真正四“海”为家之人,哪里有海,哪里便是归宿。
圣-琼·佩斯的诗作,恢宏壮丽,写出了海上的人间天堂——就连寂寥都是荣耀,年迈都是人生的庆典。比他小43岁的沃尔科特(1930年生)说,佩斯赋予了加勒比以声音,自佩斯之后,就连棕榈树都在背诵他的诗,但他的任务栏里有一项佩斯没有做的工作:反映(或者说“触及”)加勒比海的历史。拉丁美洲曾被西方人无死角地殖民,圣卢西亚的岛民也都曾是奴隶,殖民者在加勒比群岛中开辟出一条所谓的“中央航路”来通行,沿途掳掠岛上的土著。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妇女们有着“希腊或罗马的标签”,奴隶被主人以树、花和草的拉丁名字命名。不过这些名字,用沃尔科特诗中的话说,仍然“焊进了一簇火焰”,意思是说,这些因奴隶贸易和劫掠而来的一段暗黑记录,这些无名者的痛苦,被变形重释为一种忍耐的历史,甚至于这段忍辱的过去还成了岛民文化自豪感的来源。
遗忘过去,实在是因为岛屿上物产丰饶,太养人,太让人无欲无求了。沃尔科特欲用诗来保存整个加勒比地区所受的伤害。他在《历史的缪斯》一诗中写道:
如今,一个被晒黑的躯体认可了
过去及其自身的变形——
正当她从太阳底下挪开,跪下,把
她的披肩铺在这片小树林的臂弯里
那树林默然哀伤,就像父母亲的爱。
写得很含蓄,小树林就是土生土长的圣卢西亚居民,它们的哀伤是沉默的,如同父母爱着他们被伤害的儿女(却不能做任何事)。自然地,诗人会想到那些以西方人视角写下的加勒比故事,如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就有多么猛烈的要把叙事颠倒过来的呼吁:殖民遗产应该得到清算。
但遗忘也是因为宗主国的文化吞并了岛民自己的文化,后者是缺乏传统的。岛上没有出过自己的莎士比亚和密尔顿,更不用说但丁、维吉尔、荷马。沃尔科特接受的是英国统治下的文学教育,用英语思考、写作、表达感情,他像聂鲁达一样明白,殖民者在掠夺、压榨和毁灭的同时也赋予了此间的草木以名字。你很难在清算殖民主义的时候不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所以,把主—奴关系颠倒过来并不难,但你不能就此无视高度混合。
1965年,沃尔科特发表了诗集《船难幸存者及其他诗作》。“船难幸存者”指鲁滨孙·克鲁索,既是众多荒岛想象的源头,也是“殖民文学”的鼻祖,只因鲁滨孙是个在野蛮人的领地成功生存下来的白人。沃尔科特在《巴黎评论》访谈里的话,很多讨论他的文章都会引用:
我写了一首诗,名叫《船难幸存者》。我跟太太说我要出去,到特立尼达那儿去独处一个周末。我太太同意了。我一个人坐在一间海滨的屋子里写出了这首诗。我脑子里有个西印度艺术家的形象,他守在一个船难的地点……这里的海滩一般都空荡荡的——只有你,大海,以及你周围的植被,你独自一人,你和你自己。
沃尔科特在学校里读到《鲁滨孙飘流记》时是种怎样的心情呢?他看看自己身上,不黑也不白,不明也不暗:一个“混种”,名为土生土长的圣卢西亚人,身上却不知有多少来自非洲和欧洲的血液。在他的前辈圣-琼·佩斯眼里,鲁滨孙仍然当仁不让地是“主人”,各种人类情感的策源地,有他的岛和没有他的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鲁滨孙!——在你的岛边,今晚,越来越接近的天空将要赞美洋海,
而寂静将要增添一颗颗孤星的感叹。
放了帘子吧;不要点灯:
是夜晚在你的岛上,或近或远在岛的四周,
在没有缺口的圆圆的海盆各处,
是眼皮色的黄昏,在海天交织的路上。
一切都含有盐味,一切像生命的血浆,浓厚粘稠。
鸟儿在羽毛中,在油一般润滑的梦下摇晃,自我催眠;
空果藏虫暗含声,落入小湾时,自追其音。
岛在无边的寰海中沉睡,常和肥泥接触,被暖流与粘稠的鱼所冲洗。
…………
快乐!蓝天深处解绊的快乐呵,逍遥!
……鲁滨孙!你就在那个地方!
脸儿呈献于夜的征象!
一如仰天之掌。
仍然是在为鲁滨孙的自由而欢庆,他的伤悼也是年迈后感叹往日情怀之不再。那么沃尔科特呢?他在《克鲁索之岛》中说,鲁滨孙·克鲁索有一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腐败”,将基督教的原罪说传播给岛上的“他者”,野蛮人,当然也是被殖民的对象。这是谴责。可是,当岛民服从了殖民者的文化后,他们也就慢慢得以摆脱奴隶地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混合了。
这一点是关键。沃尔科特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颠覆者、清算者的位置上来写诗,他说自己和鲁滨孙不分彼此。他们都经验了相同的生存环境:灼热的阳光,孤身一人,绝望——倘若不曾感到绝望,那么就主动把自己放逐到无人的岛屿边缘去体会它。
我看不见地狱,
看不见天堂,和人类的愿望,
我的技巧
不足,
我被这钟声
击中要害。
我立于生命的正午
被一个拷打我的太阳逼疯,
我的影子
在焦热到迷乱的沙上伸长。
在自己三十多岁“生命的正午”看书中三十多岁的鲁滨孙,沃尔科特感觉到了一种总结前半生的凝重义务(“钟声”来自教堂,提醒他一段人生结束了)。在诗集里的另一首《克鲁索之旅》中,他直说鲁滨孙是一个如同希腊神话里多面魔王普洛透斯一般的人物,许多文化—历史原型叠加在他身上,从亚当,到哥伦布,到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罗斯皮罗,到斯蒂文森《金银岛》里的海盗水手本·冈,他既是“礼拜五”的主人,将白人文明传给野蛮人的传教士,又是19世纪的海洋小说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船长笔下伶仃可怜的沙滩拾荒者,还是斯蒂文森或约瑟夫·康拉德所塑造的冒险家。他既是鲁滨孙,又是被鲁滨孙驯化的“礼拜五”,既是来到荒岛的普罗斯皮罗,又是岛上的怪物卡利班,既是笛福的创造,又是布努艾尔影片里所表现的那个超现实的克鲁索。
度过35岁后,他很快把关注点从鲁滨孙身上挪开。1976年的诗集《海葡萄》以另一个文化原型人物——亚当为主角,但是,作为创世“第一人”的亚当,其实是另一个鲁滨孙。沃尔科特说,每个来到加勒比地区的人,都应该送到他写《船难幸存者》的那个地方去体验一下,那种遭排斥、被驱逐的感觉,那种被环境强加的苦役:“你巡视周围,不得不自己造工具。不管那工具是一支笔还是一把锤子,你都在创建一个亚当式的处境……”“亚当式的”(Adamic)一词多次出现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堂堂的“第一人”,并不具备他的子孙后代的钥匙,当他孤身脚踏世界时,焉知自己不是最末一人——幸存者呢?
沃尔科特代表了“多元文化”的声音,这是当然的,但是“多元”一词还是自带局限意味,因为人们对每个“元”应该是怎样的会有固见。沃尔科特的诗作常常抵达一种无限繁衍、无限变化的意象,他经常说,加勒比世界的一切都是混杂的,语言是混杂的,美丽的自然风景蒙了尘土,宽阔的海滩上扔着报废的美制吉普车,许多人一贫如洗地生活在丰足的自然物产之间。他在《圣卢西亚》一诗中随手抓取了一帧风景就写了下来——精妙地表述目之所见,是他从小具备的能力:
拉伯里、希瓦索、维约佛、德涅里,
这些被阳光晒白了的村庄,
教堂的钟声在周围塌陷——
一间覆满灰色皮屑的茅屋,
被变形的木板、铁锈、
屋影地下爬动的螃蟹所封闭,
而孩子们正在里面过家家;
罐头盒之间的一张网,一张
阳光织造的海网打捞着阴影
一整个下午都一无所获。
短短几句话里就有着多重的混杂:衰败与生命,寂寥与热闹,收获与无所得,太阳滋养万物也炙烤万物。沃尔科特像孩子那样在风景里游弋,报出村庄的名字,这些世人闻所未闻的村庄给大海镶上可有可无的边。《克鲁索之旅》中有一段写他自己驾车在悬崖边的公路疾驰时看到的景象:海,像一块“结结巴巴的帆布”,“结结巴巴”一词将视觉上的皱褶般的海浪转化为了声音里的磕绊,代表了一种不明晰的、破碎的言词表达。人岂止听不清海语,人互相说话,又岂能时时明白对方的意思呢?
于是他就一直在感受海。他的诗摈除了几乎所有个人生活和生平信息,就连爱情和生老病死都很少以明晰的词句出现。大海的意象弥漫于行句之间,作者仿佛随时可以跨出字句去踏浪一样。大海,让人在感受存在的同时感受被擦除:“浪涛一遍遍冲刷着沙子,天上的云彩飞速变形,人永远在水中走”,别说各种肤色、语言和宗教,无常形、无常态的东西都在这里汇聚。
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以及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都是沃尔科特的好友,这两位也是他在美国和欧洲的名声的背书人。在美国,因为布罗茨基等人的推介,沃尔科特的读者非常多,各种诗歌爱好者和文艺撰稿人都专程跑去圣卢西亚找他,跟当年功成名就的圣-琼·佩斯晚年退隐鹣斯岛、接受崇拜者登门拜访的情形如出一辙。《纽约客》撰稿人黑尔芬·阿尔斯描述他的容貌:“个子短小,浅蓝灰色的眼珠,蜜色的皮肤”,像一个普通岛民那样,他喜欢在阳光下扑进大海。看过1986版《西游记》的人,会发现他也很像东海龙王的造型:卷发,阔鼻孔,眼睛周围堆积着厚厚的皮肤。
人们常常因为沃尔科特在英语诗坛的地位而忽略了他背后的一个中美洲诗人圈子,特立尼达、多巴哥、牙买加、波多黎各、古巴……整个西印度群岛到处都有诗人。沃尔科特得到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他们的集体嘉奖。但是,九年之后,一个从加勒比出走的小说家兼前诗人——VS奈保尔(Naipaul),也获得了这项荣誉。沃尔科特在一首诗中用“VS黄昏(Nightfall)”指代他,又在另一首诗中说奈保尔是“败类”,因为奈保尔将家乡与世界对立起来,暗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早早离开了小岛。
“诅咒你的出生地是终极的恶”,他在1984年发表的《盛夏》一诗中说。但是,把诅咒变成祝福,并不意味着报喜不报忧,把贫乏美言为富足:难道海的宽广可以和它的冷漠无情相区分吗?它把人的一切努力都变为白费,给刚出生的人置好了墓地。在《海即历史》一诗中,沃尔科特先是指出,这些尚未被海水吞没的小陆地缺少可以述说的伟大:“你的纪念碑在哪里?你的战役呢?你的烈士们呢?”旋即又写下了自己的回答:
藤壶像坑坑点点的石头
密布着海边的穹洞
这里,就是我们的大教堂。
特约撰稿 云也退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