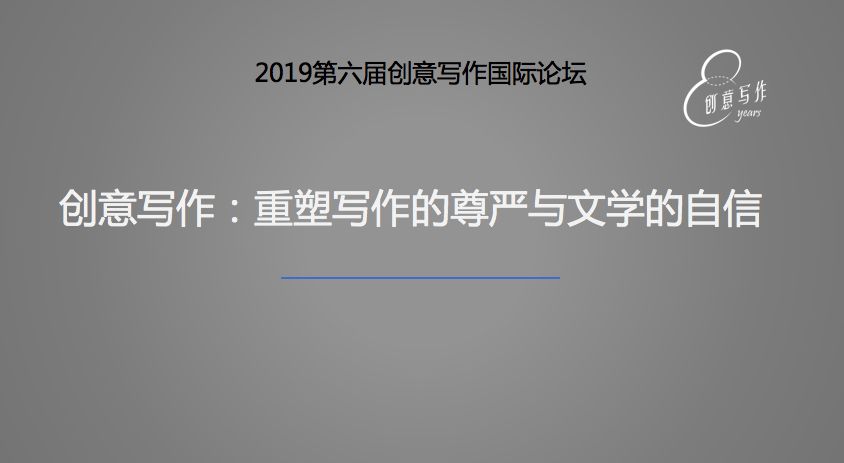
时代在不断地变化,它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而人们的脚步在其中快慢不一。我们正处于智能、方便的时代,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但同时也很容易丢失某些珍贵的事物。即使如此,我们仍坚信王宏图老师所说的:
文学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我们的创意写作大有可为。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员,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著有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风华正茂》《别了,日尔曼尼亚》《迷阳》,中短篇小说集《玫瑰婚典》《忧郁的星期天》,文学研究专著《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批评文集《快乐的随涂随抹》《眼观六路》《深谷中的霓虹》《东西跨界与都市书写》等,并译有J·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
王宏图:
创意写作的潜力及其限度
2019第六届创意写作国际论
坛
/
我们
的
MFA创意写作专业
在
2009年
经过
教育部批准,到今年
刚好是第
十届招生
。
现在很多学校也纷纷创办这个专业,特别是过去的传统写作专业也在向创意写作转型,因为传统写作专业有一点鸡肋,中文系没这个课不行,有了大家又没有兴趣。
我们从创意写作十年的发展当中可以看出很多潜力:
第一,满足很多文学爱好者的写作机能,提高了他们的写作水平。
现在有文学梦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说文学梦像终生不愈的传染病,有的人从青年时代就心怀梦想,有的人到了年老还想要创作。
第二,拓展文学内涵。
在王安忆老师培养的学生中很多都从事写作工作,他们在大学度过一段很好的时光,如果完全把培育作家的目光转移开,写作实际上还提高了他们的表达能力。
第三,激发人潜在的创造力。
几百个学写作的学生中真正成为作家的或许只有几个,但是,他们的创作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激发。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可以教的,什么是教不了的,技巧培养、人文教育是可以教的,但是很多天赋上、灵感上的东西不能教。
比如,我有一个学生是班长干部,很活跃,可我发现他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搞文学。
但他毕业之后进入了出版行业,出版行业需要沟通,正适合他,而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了知识性、情感性的元素。
还有一点是我们没有办法培养的,那就是创造的内驱力。
内驱力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你无法把它量化培养。
我指出创意写作的限度不是泼冷水,不是缺乏自信。
创作跟生命一样神秘,有很多创作是能够找到原形的,但是从原形到作品的过程十分复杂,比如说脑中符号的孵化、语言的产生与流变,都是一个很难干预的过程。
现在人工智能创作很时髦,它会绘画也会写诗,但,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进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它是把已有的主题重新输入。
因此我推测,在获得独立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之前,人工智能只能产生已有的文学组合而没有办法感知,就像前几年美国出现的几起无人驾驶汽车事故,无人驾驶设定是理想环境,但马路上总有人不守规矩。
创意写作的最大难点就在于人类生命的非理性,
但非理性又是一大创作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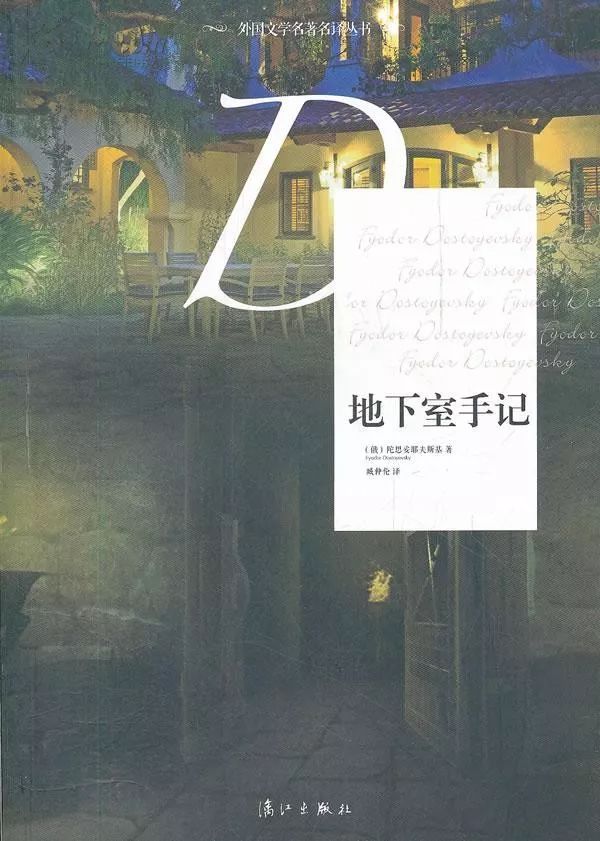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150多年前,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地下室手记》,这部小说中提到,人们明明知道某种行为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可他还是愿意不顾一切地、执拗地为人生另辟蹊径。
这样的道路走上去会无比艰难,可是,对有些人来说,执拗和任性确实比任何利益都更能带来快感。
网上常说,“有钱就是任性”,其实这不是金钱的罪恶,而是人的本性。
所以创意写作教授技巧之外还要更新大家对人的认识,引导发掘人无意识的源泉。
有人说现在文学的危机在于曾经的经典小说把能写的都写完了,已经没有什么好写的了。
这句话对,但也不对。
对的是什么?
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小说,人物环境、故事情节,都紧扣主题,再加上20世纪的意识流小说的高峰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人身上的确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再加上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一个人待在家里,只要账户里还有钱,就可以坚决地不出去,不用担心做饭也不用担心日用品,这样的生活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人类自己的生物习性变革未必与技术变革实现了同步。
将来,人类的表达形式一定会跟随媒介的变革、技术的变革一同变革。
也许电子游戏、AR、VR等等会逐步取代文学的地位,也许最后人们会回到文字形式的表达上,但是时代过去就是过去了。
莎士比亚所在的伊丽莎白时代是古典悲剧的最高峰,现在的作家再写悲剧肯定达不到那么高的高峰,但是那些经典作品的精华可以被吸收下来,采用一种新文学形式孵化,探索人的生命的奥秘、探索人性胜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