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猫儿胡同·第422辑
飞呀飞呀
看那黄色蜻蜓飞在京城天空
今年咱北京蜻蜓多了。前些天媳妇遛闺女,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继而询问很多朋友,原来不少人也注意到了。
走啊,咱们找蜻蜓去。

猜猜这是在哪里拍到的?
话说
小时候的蜻蜓
去之前嘛,额,得承认啊,我憋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得从小时候说起。
各位如果生于2000年之前,应该都见过北京遍地蜻蜓的景象吧。小时候抓蜻蜓那绝对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那时候我家住在右安门外的筒子楼,附近就是第二传染病医院。医院里面有小花园,天擦黑的时候,爸爸会带着我到医院的花池子旁,那里面都是带刺儿的月季花,而蜻蜓特别喜欢挂在枝条上。
我悄悄走上前去,伸手,就在手与蜻蜓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蜻蜓总能发觉,然后就跑了。而爸爸几乎从没有失手。

手捏蜻蜓,图片来自网络,各位看个意思。天擦黑的时候,蜻蜓看不见人,容易抓到。不过更多时候蜻蜓是竖着停在草木枝条上。
至于蜻蜓的种类嘛,普通的肯定最多,“红辣椒”其次。北京的红辣椒一般都是身上擦红,而纯红色的相对少见。“灰儿”是灰色的,最警觉,连爸爸都承认不好抓。
“老干儿”、“老子儿”是大个头的蜻蜓,一蓝一绿,好像还是一公一母,小时候我好像只抓到过一次,所以至今分不清颜色与公母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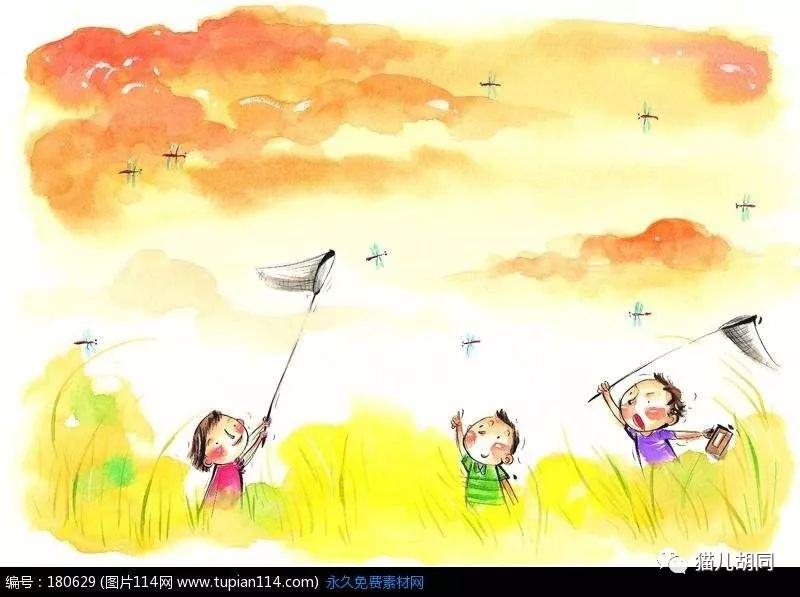
捉蜻蜓。图片来自网络。
抓到蜻蜓后,爸爸会把蜻蜓给我拿着,我用两个手指夹住翅膀。遛个弯儿的工夫,两只手指缝就夹满了。回到家里一撒手,蜻蜓飞到纱窗上。
号称这个晚上家里不用点蚊香。现在想想,不太现实啊。
也有白天抓蜻蜓的时候,家门口有条路,脑袋顶上数不清的蜻蜓。不过我的技术不好,用网抄子一下午也抓不到几个。

蜻蜓落在残荷上。
当然
不只是蜻蜓啦
可是呢,干嘛光抓蜻蜓啊,旁边有棵歪歪的榆树,树干上总能有一只黑白
花的天牛落在上面。犄角有几节?孩子们都说,九节以上就是有毒的老天牛了。

天牛。还有纯黑色的叫“老牛”。
右安门外第二传染病医院旁边,至1990年修建南二环路之前,现在二环路的位置,都是一片农田,还有蔬菜大棚,当然也少不了野地。这里有两座渣土山,我们叫它“大土坡”、“小土坡”,过了土山就是所谓的二环路,也就是沿着护城河的一条约有两车道宽的公路。
到了晚上,这条路的路灯下面,是数不清的蛐蛐。可能蛐蛐也有趋光性吧,反正根本不用进草打手电,直接用手扣住就行。
而野地里的“呱嗒扁儿”数不清——这仨字儿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那种绿色细长的蚂蚱啦,还有螳螂,都比手指头长。棕色的“土蚂蚱”根本不屑去抓。

哎就这货。
对了还有金龟子,绿色金属光泽。抓到金龟子和老干儿、老子儿后,都可以用绳子拴住,如同放风筝一样玩儿。有那手快的,看见一个闪着绿光的虫子嗡嗡飞过来,抬手一打,啪地击落,仔细一看——
靠,不是金龟子,而是超大号绿豆蝇……
也保不齐是牛蜂,如果中奖,今天的野战活动提前结束,一帮孩子赛跑搬逃回家里。

搜了一下,还真有牛蜂,学名叫“胡蜂”,不知道是不是这家伙。
一帮孩子一起抓了蚂蚱蜻蜓啥的,就该琢磨怎么虐了。小孩都有个“恶习”——爱玩火。随地捡点儿破报纸破卫生纸(额,没准是随地大便的人用过的),用火柴点着,然后把蜻蜓、蚂蚱烤一烤……
吃了。甭问我,我吃过,但我不记得什么味儿。
至于护城河嘛,呵呵,里面啥都有,甭管炉灰渣子破皮鞋,茄子竹筐自行车。就是没有鱼,因为一年四季水都是臭的。
偶尔下雨后,听说上游放水啦,就又有热闹看了。河边很常见“扳罾”的,就是用几根竹竿支起一个大鱼网……哎不知道怎么描述,看图吧。

图片来自网络。不是咱北京,各位也是看个意思吧。当年护城河边钓鱼的人很少,扳罾更常见。
网里面好像是会放几根骨头当诱饵。然而作为一个南城北京人,嗯,非常爱看各种热闹,多年来我从没见过扳罾人从护城河里捞到超过一乍长的鱼。
别看没鱼,蛤蟆从没少过。小时候看书上画的青蛙,绿绿的,真可爱,可是从没见过青蛙,河边永远是癞蛤蟆。身上真的冒白水,想想都膈应。
那现在呢?
越说越远啦。小时候好玩的东西总是那么多,但现在,都没了。
所以当我听说蜻蜓多起来的时候,有了一种——
多年没犯的、欺负小动物的心情。去找找看吧。
第一个地点:陶然亭公园。
进门的时候我就问工作人员,公园里面哪的蜻蜓多?工作人员回答,赶对了时间和天气,公园门口的那片小广场上就有很多。
可惜当天在门口没看到几个。进了公园里面走了好一会儿,三三两两,没有成群的。继续向遛弯的老人打听,有老人说,去月季园,那里很多。

这张照片上能看见三只在飞。
到月季园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天还大亮,热得要死。然而这里也并没有蜻蜓,园丁师傅说,别着急,再等等。
接近5点半的时候,大批蜻蜓突然出现在了园子里,尤其是月季花圃上,几乎是往人身上撞的架势。普遍飞得不算高,胸口高度也就是月季花圃正上方最多,还有很多飞在膝盖高度上。

园丁师傅两侧各有一只。其实数量比这个多得多得多,可太难拍,光圈小了背景乱蜻蜓融进去了,光圈大了很多蜻蜓不在焦平面上。拍这点儿蜻蜓真费了劲了。
又问了几位遛弯游客,确实是比往年多,不过往年这里也会有,并不像街边一样曾经遍布如今绝迹。
并且,我在陶然亭公园里还看见了大个的、绿色的……老干儿还是老子儿,还有中间灰色的,学名玉带蜻。可是我记得小时候的“灰儿”好像全身是灰色的吧?还是我记错了?难道它就是灰儿?

陶然亭公园里,蜻蜓落在钓鱼人的鱼竿上,抬起鱼竿它飞走,放下鱼竿它又回来。可爱。
第二个地点:北三环和平西桥东南角、中国计量科学院内。
这就是媳妇遛孩子的地方。这个单位里面有个花园,像是过去的老单位,边边角角绿化都不错。
也是下午5点,只有很少的蜻蜓。然而到了6点,在局部角落,蜻蜓突然多了起来。飞行的高度大概在三层楼的高度。

这个好拍,因为飞得高,背景是干净的天空,小光圈解决问题。
看上去数量确实有些惊人。不过它们飞行的地点似乎有着挺明确的范围,某些绿化带里特别多,某些地方特别少。而在计量院门口的三环路边,一只都看不见。

看看,松柏,人家单位院子绿化真不错。
为什么呢?
夜半时分的洋桥附近的凉水河畔已是一片蛙鸣。河边的草丛里,一盏小灯亮了起来,悄悄摸摸地走到一片灌木前。
把灯绑在头上,举起手机给蜻蜓拍个照,张洁每个月都有几天是这样度过的。

夜拍来袭~~
作为生物专业毕业、资深自然爱好者、“绿色种子计划”发起人,张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夜观”的习惯。而凉水河畔环境改善让她印象深刻。
“相比护城河,这段凉水河环境更好,因为部分河床没有用水泥砖做硬化处理,而是在下面保存了一部分泥土。水质好起来,水生植物也茂盛了。”
这也是包括蜻蜓在内的一些昆虫的天堂。

后面就是万家灯火。
今年她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蜻蜓以及三种豆娘,在观测水草时,也看到了大量蜻蜓幼虫即“水虿”。水虿在水里需要一两年时间发育,才能蜕皮成为我们常见的蜻蜓。

水虿chai4,哎好膈应~~
她注意到,以往在枯水季节,京城的部分河道均会清淤整修,很多水生动植物因此断了繁育。“所以今年蜻蜓多,除了气候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近一两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河床整修。”

能找到小蛤蟆不?
此外,城市里面对树木病虫害,曾经最常见的方法是打药。“这对于大多数昆虫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蜻蜓多起来,可能与农药用量减少、生物防治方法更多使用有关。

豆娘,蜻蜓的亲戚。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没长大的蜻蜓。
当然,气候湿度,也都是原因。
光有蜻蜓吗?
既然蜻蜓能多起来,其他的物种是否也能多起来呢?
张洁解释,以目前北京城市的状况看,虽然更适合一部分物种生长,但并不适合所有曾经存在的物种。
“城市是人类集中活动的地方,肯定需要发展建设,所以在城市里的自然环境,也少不了‘人工干预’。”野地变成规整的绿化带,便是其中表现之一。

夜晚的蜻蜓。
据她观察,北京的部分公园已经开始重视这一情况,“比如紫竹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并非没有人工干预,但相比之下并不频繁,所以在那里我曾找到过很多城市里没有的昆虫、鸟类。”

天坛公园里常见拍鸟人。

天坛里的戴胜。这个鸟挺常见的。
这些年京郊一些地区,会在秋季兴起“萤火虫热”,然而北京城里也从没见过萤火虫。“萤火虫的幼虫也生活在水里,并且对水质的要求更高。”
与之类似的一些昆虫,因城市里不具备当初的生存条件,在未来难以大规模出现,好在京郊具备这些条件,并且近年来也明显改善了环境,因此得到较好的繁衍生息。

萤火虫,图片来自网络,应该不是咱北京。我见过三次萤火虫,第一次是80年代中期,在石景山地铁站往南,当时路边是野地。哇,太奇妙了,居然有虫虫会亮啊。第二次是1996年初中军训,在昌平南口,数量也不少。第三次是在贵州大山里,卧槽,太美了。可惜咱北京城里享受不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