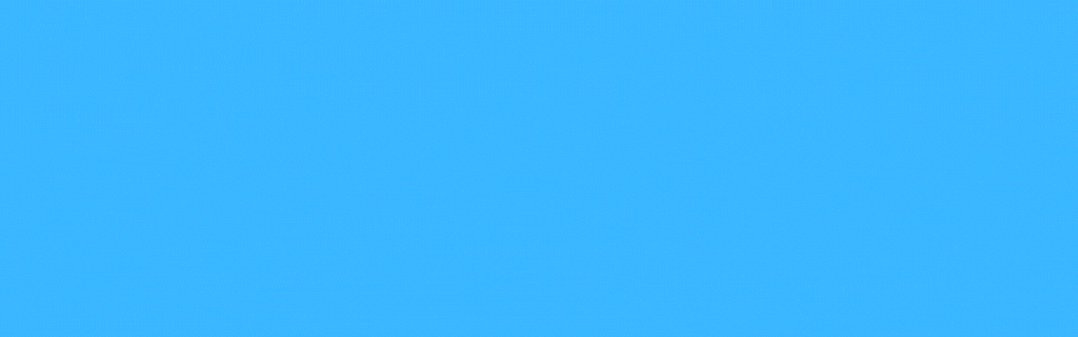
很少有什么发现比揭露思想根源的发现更惹人愤怒了。
——阿克顿勋爵
从最初时期(即18世纪晚期)以来,左和右之间的划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这种划分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
法国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泽埃夫·施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在其关于一些团体和政党——它们都将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围绕这种划分的性质所进行的论辩一直是存在的。左和右的含义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只要对政治思想的发展进行一番浏览,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在某些时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时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
左派和右派的称呼源于法国大革命,因会议中激进的革命党坐在左侧,温和的保王党坐在右侧而得名。
例如,自由市场哲学的倡导者们在19世纪被视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将其归入右翼。19世纪90年代,工团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团结的人宣称左与右之间的区别已经消亡。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就被重复一遍。虽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对这些理论提出过争议,但是,就像那些具有右翼背景的人经常所做的那样,这一主题始终不断地被展示。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ChartierAlain,即埃米尔·夏蒂埃[Emile Chartier])评述道:“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尔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与右翼为主题、富有争议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著作(这些著作这次主要是来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试图为这种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博比奥的论辩值得一听。
他说,左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关于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这种区分是两极化的。

左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政治也反过来加剧了左和右的对立。
博比奥说道,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平衡,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右划分的意义存有疑问。但是,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它看起来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the only game in town),则两边便都会趋向于对这种划分的意义产生怀疑。更为强大的那一方,会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声称的那样,做出“别无其他选择”的声明。随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渐地变得不受欢迎,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每一方都显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趋陈旧的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或是将这一区分的各个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种新的重要取向。
右翼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覆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构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优势地位,情况又发生了逆转。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关于托尼·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并将它们重新改造为某种新思维的说法,从上述立场来看,确实易于被人们理解。而这一次,从关于旧的分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论争中受益良多的却是左翼。依照博比奥的说法,就像过去一样,左和右之间的划分将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设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复兴,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变得不那么新的话,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可能很快会不再对是否放弃左和右的划分感到犹豫。

政治光谱测试:https://luckyfuy.top/compass(复制到浏览器做题即可)
在博比奥看来,左和右之间的区别不纯粹是一个正反两极的问题。一个主要的标准在将左与右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翼倾向于获取更多的平等,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
“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它,我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种平等是在什么人之间?是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是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左翼寻求减少不平等,但这一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
左与右的关键区别在于:对待平等的态度。
下述这样的一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右派却想要永远保留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与语境相关的。例如,在一个近来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国家中,左和右之间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态度差别上:是否应当给予这些移民基本公民权利和实质性的保护。
在坚持主张左和右的划分将持续下去的同时,博比奥通过承认这种区分现在未具备其过去具有的支点,而结束了对他的著作批评者们的“回应”:
不可否认,当前在左翼中方向的丧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左翼的传统运动中从来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已经在现代世界中显露出来;并且,他们为了改造社会而提出来的某些设想(他们曾为这些设想和各种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实现······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认,今日的左翼已经不再是它过去那样了。
在左和右的区分不会消失,而且将不平等视为这种区分的核心所在这一点上,博比奥无疑是正确的。虽然关于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这一观念对于左翼来说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坚持不懈的攻击。不过,对博比奥的阐述还需要进行某种提炼。
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与其这样理解社会正义,倒不如说“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来得更为准确。平等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与自尊。

平等、公平、现实和自由
正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心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匮乏、贫困者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的邻居过得更不好的事实,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一事实不只是作为不平等的罪恶而显得重要。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造成了更大的伤痛之上,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他们。
还有一些其他关心平等问题的理由。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过去确实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种姓社会。而在一个充分民主的时代,情况大为迥异。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很可能会促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全球化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同回应联合了右翼的政治家们,如美国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法国的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以及澳大利亚的保利娜·汉森(Pauline Hanson)。对于那些更广义的右翼人士(如美国那些将联合国和联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坏其国家完整之阴谋的“爱国者”)来说,情况甚至也是如此。极右派的主旨是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例如,布坎南就声称“美国优先”!他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强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辩护,认为用它们替代“全球一体论”才是适当的选择。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具有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
左和右之间的划分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是否如博比奥所言,仅仅处于左与右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确实存在着,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无论是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大多数左翼思想家与激进分子都曾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里程紧密联结起来,而且也将自己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结起来。保守派则相反,对宏大的计划向来持怀疑态度,并对社会发展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强调的是连续性。这种对立在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左和右都逐渐地接受了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双刃”性质: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而且制造了新的危险和动荡。
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使人们对宏大的计划失去信心
随着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期望推翻资本主义,并以一种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其余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这些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与过去不一样,不是在更为基本问题上的分歧。
摘自《第三条道路》
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变,大量的其他问题和可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而它们并不属于左右划分的范畴。这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价值与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些价值交互关联。我们还必须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别处所称的“生活政治”。当然,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术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 decision)。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
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盟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右的问题。/
图书简介:本书是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关于社会民主政治之未来讨论的经典之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吉登斯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创造性地提供了一条可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发展道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布莱尔政府的执政方案,还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书1998年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全球关注,对于研究当代政治思想的发展,颇有裨益,不可或缺。作者简介: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上议院议员,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99—2003),现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教授(2004)。著有《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第三条道路》等40多部著作,拓展了现代性、全球化等理论,其思想对当代社会学与政治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译者简介: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曾任教于北京大学(1998—2003)和香港大学(2004—2014),并曾在密西根大学、多伦多大学、杜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和访问教授。译有《公法的变迁》《法律的道德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