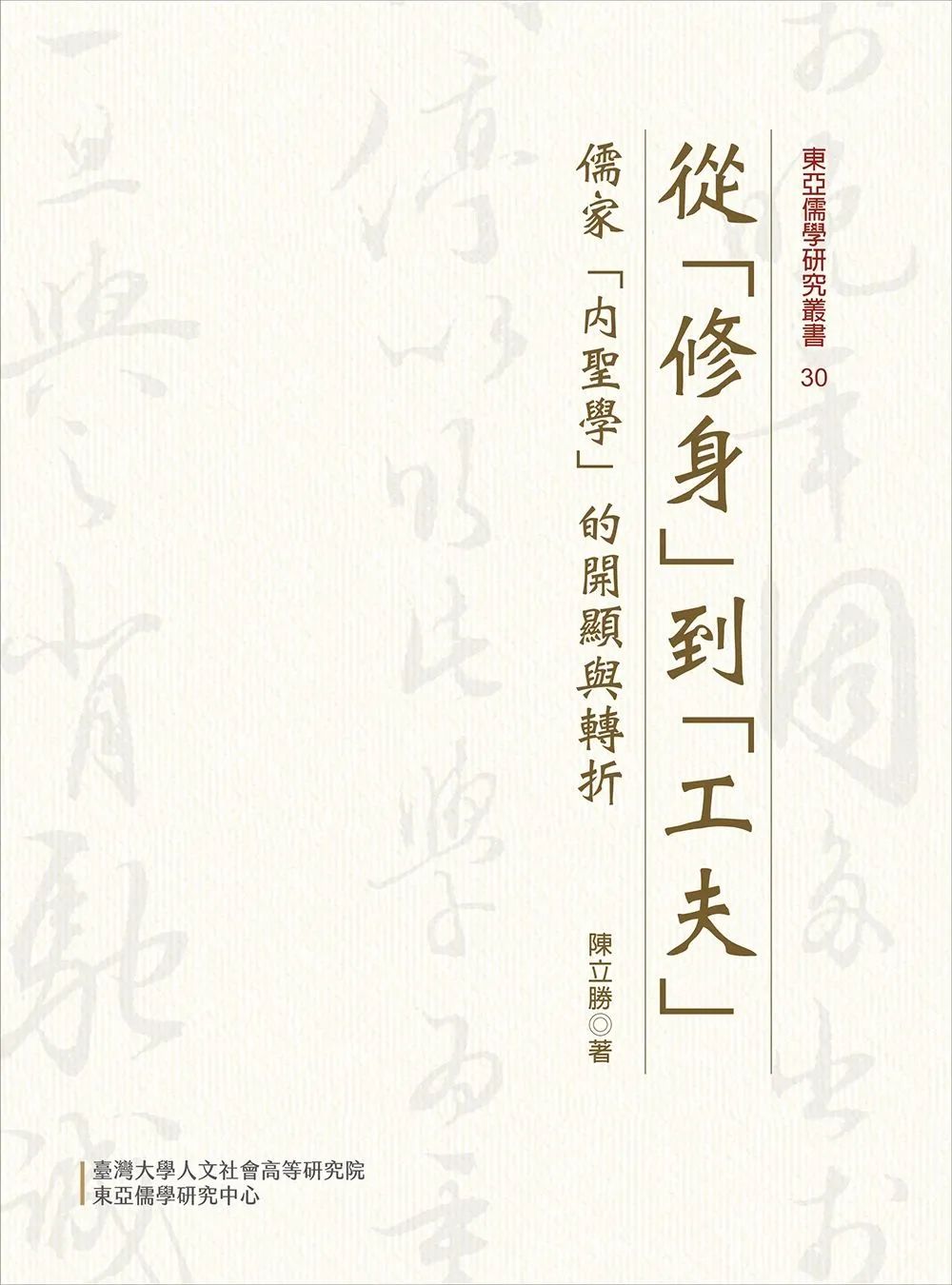
从“修身”到“工夫”:
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
陈立胜 著
丛书:东亚儒学研究丛书(30)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4月
486页,精装繁体
儒家形而上学既非“思辨的形而上学”,亦非“道德底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of morals
),而是以道德体证为入路证成的形而上学即“道德的形而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依此牟宗三先生之慧见,儒家形而上学的内容实则由“道体”与“体道”两个面向构成。形而上学的“道体”是在“体道”的过程之中证成的。我自2003年完成王阳明万物一体论的研究计划后,即自觉转向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前后两个研究领域,前者是“道体”,后者是“体道”。而王阳明的工夫论必须放在儒家修身传统之中才能得到适当的定位与理解,于是我个人的兴趣也由阳明学转向对整个儒家修身学传统的研究。
儒家修身传统渊源有自,自《尚书·皋陶谟》提出“慎厥身修”的观点起,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任何一个悠久的传统之存续都必表现出因袭与损益、变与常的辩证面向。传统作为世代延续之物在根本上是一种世代性、历史性现象,历史的时间从不是“匀质的”与量化的物理时间,而是由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时刻刻画、中断、扭转的异质的、定性化的时刻、时机。在宗教传统中,时间是由“神圣者”、“圣贤”的参与、显现而表现出一个个重要的“节点”、“时刻”,它传递出重要的精神信息,保罗所谓的“凯罗斯”(
Kairos
)是“白昼之子”期待、响应基督再临的时刻;同理,“天生仲尼”,在儒教徒那里则是打破长夜的关键时刻。而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富有“时间”意义的可能还是几个“之际”:春秋战国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清末民初。这些“之际”不仅意味着朝代的更迭,更意味着社会政治的转型乃至人生存方式的转变,而反映在思想上则是思想形态的转型。“身”之所在之“时”与“世”的变迁,当然会折射在修身思想的转折上面。刻画修身传统之中的这些重大的转折“时刻”,是修身谱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正是本书所尝试进行的工作。
本书三大部十四章(含导论)系由单篇论文构成。这些文字多发表于不同的场合,我一直对结缘的师友持有真挚的敬意。
我要感谢杜维明先生。2002-2003年,我应先生之邀,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9年与2020年春季学期,我更两次受先生之邀担任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20年春季学期因疫情而最终只能“云访”),先生把他的院长办公室提供给我使用,办公室中先生富有特色的藏书为本书的修订与结集工作提供了莫大便利。
我要感谢黄俊杰先生。黄先生担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总主持人、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期间两次邀请我担任访问学者。自2004年后,我几乎每年都受邀参加先生主持的研究计划与学术会议,我的研究成果也有幸纳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中。先生荣休后担任文德书院院长,又邀我参加他负责的《儒家思想的21世纪新意义》研究计划,本书第一章即是该研究计划的部分成果。今书付梓之际,先生更于百忙中赐序奖掖。
我要感谢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先生与台湾大学陈昭瑛先生,两位先生慨允将拙著纳入“东亚儒学研究丛书”。
我要感谢冯达文先生、陈少明教授及中大中哲团队,这个精神共同体对学术的激情、对生活的热爱,俨然形成了南国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气候。
我要感谢美国葛底斯堡学院司马黛兰(
DeborahSommer
)教授、台湾“中研院”林月惠教授,司马黛兰教授将陈荣捷生前所用的宋明理学原典转赠给了我,更多次帮我扫描我所需要的海外研究文献。林月惠教授总是把“中研院”文哲所出版的各种最新研究文献赠寄给我。
我要感谢两名匿名审稿人,两位时贤从义理表述到简繁转换均提出了具体而微的修订意见。
我要感谢安鹏博士生,他帮我排定了版式,编订了参考书目,并校正了书中多处疏漏。贵州大学刘荣茂副教授与中大珠海校区罗志达副教授通读了一遍书稿,鲁鱼亥豕,亦多有订正。台大高研院金叶明助理最后统整了格式,在此一并致谢!
全书部分章节曾以学术讲座形式发表于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韩国成均馆大学、忠南大学,部分章节系提交给复旦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台湾中山大学与辅仁大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另部分章节已刊发在《深圳社会科学》、《哲学门》、《贵阳学院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中国文化与哲学评论》、《广西大学学报》、《孔子研究》、《中国文化》、《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学术研究》等学术杂志与辑刊上。在此,谨向讲座与会议的邀请者与评论人、向期刊与辑刊的编辑致以衷心的谢意。
最后,我要一如既往地向妹妹、弟弟表达谢意,我的父母均已行开九秩,他们对父母悉心照顾,让我安心在南国问学,每每念此,心中总有一丝不安。
鸣谢
第一章 轴心期之突破──“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
第二章 “修己以敬”──儒家修身传统的“孔子时刻”
第三章 “慎独”、“自反”与“目光”──儒家修身学中的自我反省向度
第五章 “治怒之道”与两种“不动心”──儒学与斯多亚学派修身学的一个比较研究
第六章 “梦”如何成为工夫修炼的场域──以程颐说梦为中心
第九章 作为工夫范畴“独知”的提出──儒家慎独传统中的“朱子时刻”
第十二章 “独”-“几”-“意”──阳明心学一系工夫演进中的三个“关键词”
二、“念起念灭”困境、对“发处用功”的质疑与“本体工夫”意识的觉醒
第十三章 “无工夫之工夫”──潘平格的登场与理学工夫论的终结
陈立胜
山东莱阳胡城村人。南开大学哲学学士,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博士。现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员、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曾先后担任纽约大学、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人、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特邀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访问学者。
著有《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1999,广州;2017,北京)、《西方哲学初步》(与彭越合著,1999年增订再版,广州)、《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2005,台北;2008,上海;2018,北京)、《宋明理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2019,北京)、《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研究》(2019,北京)等。
在宋明理学中“工夫”与“功夫”两词并未有特别的区别,两词在同一语段之中往往混同使用,即是例证。《朱子语类》卷二十八载:
或问:“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为它功夫未到。”问:“何谓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圣门功夫自有一条坦然路径,诸公每日理会何事。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这些功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颜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穷理,功夫到此,则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即便在与“本体”对言时,功夫与工夫亦未得区别。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既有将“工夫”与本体对举的用法(《答程正思》,卷五十),亦有“功夫不到则无以见其本体之妙”乃至“本体功夫”的用法(《答何叔京》、《答廖子晦》,卷四十、卷四十五)。故本书“从修身到工夫”中“工夫”而非“功夫”,只是词语择取之方便,并无特别意义。
无论是“工夫”抑或“功夫”都是“成圣”(“复其初”、复本体)的具体实践过程(“路径”),佛教之成佛,道教之成仙自然亦有其路径,就此而言,佛教与道教皆有其相应的工夫。不仅如此,大凡各个伟大的宗教都有其各自的自我转化(
self-transformation
)的路径,故都有其各自的“工夫”。这里所谓“自我转化”不是被迫的、被动的,倘如此则是强制性的政治“改造”,也不是不经个人努力、奋斗只是通过一种人工的技术手段而获得的,倘如此则是基因编辑,而是个人的自觉、皈依而发生的人格转变(个人的重生、再生)。无疑这一转变是生命对超越者、终极实在(
the real
)的回应中发生的。撇开印度宗教不论,基督宗教源远流长的灵修传统其丰富多彩的“自我技术”实不遑多让儒家的“成圣”工夫。职是之故,“工夫”这个词或在西方传统中找不到准确的对应者,但这绝不意味着工夫论惟此中国哲学一家而别无分店。但儒家自我转化确有其独特的路径,即它始终是在这个世界中转化这个世界的同时转化自身,或者说它始终在这个世界中转化自身的同时转化这个世界。这种被称为“即凡即圣”(
the Secular as Sacred
)的总体特征,在根本上决定了儒家的修身、身心修炼的工夫践履即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展开的。换言之,在儒家这里,“道 ”—“学”—“政”是三位一体的,“成己”与“成人”“成物”、“修己”与“安人”“安百姓”本即是体用不二的关系。就此而论,一个寡头的“内圣学”绝不会是儒家的修身学、工夫论同义词。
如所周知,“内圣”与“外王”对言,出自《庄子
‧
天下》。孔、孟、荀原儒从未用过该词。宋明儒也罕用“内圣外王”一词讲学论道。宋儒品鉴人物时偶然用之,但随后,“内圣外王”便成为一帝王之学的谀词(“集内圣外王之道”用于当朝皇帝身上)。逮及熊十力,始尝试用“内圣外王”指“夫子之学”,这一新用法影响到牟宗三,其后内圣外王之学遂成为儒学的代名词。谛观熊子全书,熊子在《原儒》之《原外王》一章之后,即有《原内圣》一章,而于《原内圣》章则开宗明义指出“内圣之学,《易大传》所谓广大悉备,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显见,儒家之内圣学实则彻上彻下、彻内彻外之学,“内圣”之“内”恰恰是无远弗届的。熊子于是章内又反复指出《乐记》中“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之“反躬”即是“反己之学”,“此在哲学中最为特殊,庄子所为称之以内圣学也。返己而不自欺,宋学确承孔子精神。”在《答牟宗三》书信中,熊子又强调,庄子“内圣学”一语实本自《大学》,但强调“内外”是“顺俗为言,不可泥执”。因“《大学》经文只言本末,不言内外。”本末不二、体用不二,是个“推扩不已的整体,不可横分内外”。要之,“内圣者,深穷宇宙人生根本问题,求得正确解决,笃实践履,健以成己,是为内圣学。”显然这一“内圣学”的定义是在“广大悉备”、“体用不二”、“无内无外”的前提下所给出的一个“操作性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
),这一定义也为牟宗三所承认并继承:“什么是‘内圣’呢?就是内而治己,作圣贤的工夫,以挺立我们自己的道德人品。”牟宗三更进一步指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命脉”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线相承之道,自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即“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孟子承此而实落在“内圣之本之挺立处”,其后宋儒虽未忽视于外王,然其重点与中点亦仍是落在内圣之本之挺立处,要之:“此内圣之学,就其为学言,实有其独立之领域与本性。……自孔子立仁教后,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是最本质之发展,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永久价值之发展,此可曰孔子之传统。”故内圣学具有“独立的意义与自性”。本书副标题中的“内圣学”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本书由以下三部构成:第一部,儒家内圣学的开显:德行培育的时代;第二部,儒家内圣学中的反省向度与修炼技术;第三部,儒家内圣学的转进:心灵操练的时代。
第一部《儒家内圣学的开显:德行培育的时代》尝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刻画为轴心期突破的一个主题。
人与道、天道的内在联系这一觉醒意识在根本上是对人的特殊存在地位的觉醒、人之为人的“类意识”的觉醒、人之为人的尊严意识的觉醒。这种基于“人”与“天”的内在联系的人之“类意识”觉醒才是中国哲学突破的一个标志。尽管殷周之际,“修德”已俨然成为“精神内向运动”的主题,周人“敬德”观念背后的“忧患意识”亦确具有“道德的性格”,只是这个“德”仅限于在位者而仍未及一般人,更为重要的是,以“敬”为本的“礼”其原初动机亦不外天子、诸侯之祈福心理。孔子“为己之学”坚持“有教无类”,其“学”牢固地锚定于学者自身的修养、完整人格的培养上面。自此德性世界的普遍性、纯粹性与自足性得以证成。实际上,“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一道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一“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人文主义底色。“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儒家为何用“身”来指示西方宗教与哲学之中的“自我转化”的对象?“身”之被“修”跟一般的器具、器物被“修”其“本体论的差异”(
ontological difference
)何在?此是第一章《轴心期之突破──“身”何以成为“修”的对象?》处理的主题。
孔子不仅证成了德之普遍性、纯粹性与自足性,同时更提出了“修己以敬”这一行己、持己之道。如同“关心自己”在希腊和罗马文化中规定哲学态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真正总体的文化现象一样,“修己以敬”既是一种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态度,也是一种“自反性”的精神指向,更是一种改变自身、净化自身、变化气质的活动。由“己”出发,能够通贯人己、人物、人天而确保敬人、敬事、敬鬼神的修身践履即是“敬”。故“敬”在根本上不是一种单向的指向他者的力量,而是人之为人的整体性的生存态度。“修己以敬”将敬天、敬人、敬事的“敬”的精神彻底安顿在个己德性生命的自觉上面,因而也是孔子之前“敬”文化的哲学上的升华。此是第二章《“修己以敬”──儒家修身传统的“孔子时刻”》阐述的主题。
由孔子所奠定的修己以敬的对待自我、关心自我之道、为己之学之道,在根本上决定了儒家的修身活动是一项高度的自反性活动。在这种自反性活动中,自我通过一种特殊的“目光”、“他者的目光”将自身变成省察的对象。卷贰即集中阐发儒家内圣学的自反向度与各种不同的修炼技术。
第二部《儒家内圣学中的反省向度与修炼技术》采取历时性的思想演变考察与共时性的类型学划分这一方法论,检视儒学修身传统中自孔子孳乳而至宋明粲然大备的反省现象。
在儒家修身学中,无论在“慎独”要求抑或在“三自反”的主张之中,都设定了一种“他者的目光”,这个他者的目光首先表现为“鬼神的目光”与“他人的目光”,而随着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勃兴,他者的目光渐被每个人内在的“良知之光”(“心目之光”)所替代。在儒家修身工夫的“反省”向度之中,“鬼神的目光”、“他人的目光”与“良知之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第三章《“慎独”、“自反”与“目光”──儒家修身学中的自我反省向度》即着手揭示这三种目光各自不同的性质与作用:“鬼神的目光”是无人之际、独处之时一种超越的监视目光,我是这个目光聚焦下的“行动者”。故在鬼神的目光下,营造出的是“我必须……”(
I must
)这一当下的行为期待,伴随这种期待而来的是我当下小心翼翼的举止;“三自反”处境下所遭遇的“他人的目光”是一种责备的目光、令我不安的目光,我是对某一行为(“横逆”)的“负责者”。故在三自反的“内视目光”下,营造出的是“我本应该……”(
I should have
)这一对适才发生的行动之反省,伴随这种反省而来的是愧疚感;静坐讼过之中自我审视的“良知的目光”(“通身是眼”)是一种审判的目光,我是这一目光下的“有罪者”、“被审判者”。在自我审视的“良知的目光”下,营造出的是“我认罪……”(
I confess
)这一对心灵生活负责的忏悔态度,伴随着这种忏悔而来的是精神生命的重生。
不过,如从反省的对象、内容立论,儒家的反省活动既有对生命整体的反省,亦有对当下一念的省察,基于此,第四章《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四种反省类型》对儒家反省技术进行另一种类型学的划分:
(1)对一生经历的反省,孔子十五志学至七十不逾矩,反映了儒家“行年”意识、年龄的“临界”意识与修身的“行己”意识是紧密绾接在一起的,这种年龄现象学通过“反省”意识将其一生生命的“年轮”以一种“路标”的方式刻画为一个个不断跃升的“临界”点,警示、指引每一位“临界”的此在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2)对一天行为的反省。曾子“三省”的对象是日间所行的事情,省察之焦点在己之尽心尽责与否。这种夜间的修身“课程”发展到宋明理学则成为贯事前事后、贯动静的彻头彻尾的“常惺惺法”,无疑由对日间行为的反思、检讨转向对念虑的省察,由德行的培育转向意识生活的经营,是理学工夫论的重要转进处。
(3)对意念生活的反省。这是宋明理学心灵操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又表现出两种类型,一是课程化、仪式化的“意念管理术”,如以黑白豆点检意念的方法,一是理学家普遍认同的、以朱子为代表的“随念致察法”。
(4)对当下一念的同步反省。这种反省“同念并起”“无等待,无先后”,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的“自身意识”“内意识”反省现象。
要之,儒家的反省虽是一种“回头意识”,但这种“向后看”旨在改变自身因而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意识,故它在根本上是由一种“向前看”心态定调下的“向后看”意识。基于对未来生命进程的展望、规划而展开的对人生的反省式的回溯意识,与当下生命状况的调整、改变层层缠绕于一起,这是儒家反省意识的基本结构。
在反省成为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下,不仅一生经历、白昼言行、意念活动成为省察的对象,人之情绪领域(喜怒哀乐)与“下意识”、“无意识”的领域(梦)都成为工夫修炼的对象。这是接下来第五章《“治怒之道”与两种“不动心”──儒学与斯多亚学派修身学的一个比较研究》与第六章《“梦”如何成为工夫修炼的场域:以伊川说梦为中心》分别讨论的主题。
“怒”是人类情绪之中最难对治的一种。儒家对怒取血气之怒与义理之怒两分法。前者需要克治,后者需要培育。而种种“治怒之道”(忍怒法、忿思难法、自反治怒法、明理治怒法、克己治怒法、以敬治怒法)又可分为消极与积极两面。忍怒、忿思难均是消极的、被动的治怒法,二者均是在怒意已起时才用工克治,这种消极的治怒法在学理上无非是将“怒”对象化,怒“气”、怒“意”因此而会减弱、延宕乃至渐消渐散;而积极的治怒之道在于“克己”、体仁、明理、以敬待人,在于“自反”而成就君子德性。斯多亚学派则视怒为彻底非理性的冲动,并通过克服“冒犯”意识、培养“容忍意识”、“庆幸”意识与幽默感来化解之,亦通过“且慢”法与“反思”法来对治之。“怒”在常人处都是指涉他人的,是对他人不满的一种情绪,而无论在儒家抑或在斯多亚学派的治怒体验之中,都明确要求将这种涉他的情绪指向性加以反转,而成为一种自我关涉(
self-regarding
),于是本来是要改变他人的一种策略之怒,现在变成了一种自我警戒、自我省察、自我转化,“治怒之道”遂成为自我提升、自我精进之道。要之儒家与斯多亚学派的治怒之道在根本上是为了成就伟大人格、培育“不动心”的精神境界──当然,前者是一种热性的不动心,后者是一种冷性的不动心。
“梦”则是人之无意识领域的重要内容。在上古文化中,梦只有吉凶祸福的意义。道家“至人无梦”说首次将梦跟心灵境界之修行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儒家,二程兄弟尤其伊川彻底斩断习俗以吉凶祸福论梦这一思维定式,将“梦世界”收纳于“理世界”之中,体现出惟“理”主义的取向,并将梦世界跟心性修炼联系在一起,开启了“睡时用功”这一理学工夫论之新向度。从理学工夫论历程看,“梦”工夫计有四种类型:一曰藉梦卜学型,二曰梦后自责型,三曰梦中用功型,四曰随顺昼夜之道型。将夜梦、睡眠纳入工夫修炼的对象,不仅意味着儒家反省工夫广度之扩展,而且同时也表明省察深度之加深,反省的目光已经深入到人性之幽深晦暗之领域。梦工夫的出场反映了儒家修身传统的一大转进,伊川梦论是“梦”进入儒家工夫修炼传统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
反省与沉思固然是一种思想活动,但它也离不开身体的支持。一个人在像阿甘一样飞奔的时候是不适合反省与沉思的,毕竟人有限的血液更多地要用在机体运动上面,脑部的供血会受到限制,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艺术作品中的沉思者都保持着静坐的姿态。而静坐恰恰也是人类生命修炼现象中的一个常姿,当然苏菲舞(
Sufidance
)跟其他巫舞一样,固然能起到沟通人神乃至抵达忘我之境的作用,但显然这不是一种反省现象。静坐在儒家文化之中实则有古老的渊源,其源头确实可以追溯至祭祀文化所要求的斋戒仪式。作为修身工夫技术的儒家静坐传统通常被认为是始于宋儒。“何者最乐?静坐最乐。”两宋士人精神生活丰富,静坐成为一种有格调、有韵味的生活方式。
依照静坐在工夫修炼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七章《宋明理学中的静坐类型及其效用》将儒家的静坐技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作为默识仁体、观未发气象之静坐,(2)作为收敛身心之静坐,(3)作为观天地生物气象之静坐,(4)作为省过仪式之静坐。程朱一系之静坐注重收敛身心,澄心定气,这应是儒家各类静坐的基本要求。作为默识仁体、观未发气象之静坐则要求在从血气荡漾的感性生活摆脱出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豁然有悟”而洞见心之本体(“睹体”)。作为省过仪式之静坐,就克治私欲、妄念一面而言亦可视为是收敛身心静坐之变样,不过它更偏向一种主动性的、倒巢搜贼式的净化心灵行动,并往往又以“睹体”、“见性”而告终。以上三种工夫都是围绕“心”做功夫,就此而言,都可以说是“观心”的工夫,作为观天地生物气象的静坐侧重却是“观物”,但一者观物亦是在“静”中观(所谓“静观”),故已预设收敛身心之工夫,一者观物与察己密不可分,“观心”与观“乾坤造化心”实乃一体两面的工夫。
接下来第八章《宋明理学如何谈论“因果报应”?》则从儒家修身传统入手,讨论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传入中国后,宋明儒学如何立足于上古文化中的天道福善祸淫与德福一致的信念回应、吸纳佛教的报应论。先秦儒家对善恶有报与德福一致这一古老信念的反思最终确立了德性的纯粹性、无条件性与崇高性,并将善恶无报与德福不一的问题归咎于时命、气命等存在的偶然性。“天道”尽管仍然被赋予福善祸淫的能力,但“天道”从不被视为个人功德的算计师,而道德行动也不是在功德银行进行长线投资,人之行善去恶更不是跟“天道”做交易。然而德福不一、善恶无报的现象毕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来宗教恰恰以其严密的果报理论填补了这一空白。世人趋之若鹜,一度造成儒门淡泊的文化惨像。程朱大儒应时而起,重树“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论系统,破佛教之轮回观,以“感应”代“报应”,将先秦儒学的善恶有报的观念彻底“理性化”、“感应化”,以此彰显佛教之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论之功利性,又将佛教的因果报应与轮回观充分“现世化”、“人间化”,体现儒家“一个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顺势将佛教“念念受报”观念转化为儒家诚意、慎独话语。阳明心学力倡知行合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工夫,而将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彻底人间化、心学化、当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阳明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伦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学发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恶有报的观念即分化为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修己之学”话语系统,一套是“安人之学”话语系统。前者坚持惟道是忧、惟德是忧的道义主义原则,后者则坚持达情遂欲的现实主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