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5年的今天,萨特在巴黎降生,不到两岁,父亲即久病离世,萨特于是跟随祖父母和母亲一同生活。对萨特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如果说爱与憎是一枚奖章的正反面,我却既不爱物也不爱人,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们不可能既要恨又要讨人喜欢,既要讨人喜欢又要喜欢他人。”萨特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中真切描绘了他12岁前的童年生活,早熟世故、冷若冰霜的性格背面,我们得以窥见其思想脉络的重要线索,同时,在这面童年的镜子里,或许你也能不时看见自己。

文 字 生 涯( 节 选 )
让-保尔·萨特
沈志明 译
让
-巴蒂斯特
(父亲)
早想进海军军官学校,为的是要看大海。他当上海军军官后,在交趾支那得了疟疾,病得力竭体衰。一九〇四年他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韦泽
(母亲)
,征服了这个没有人要的高个儿姑娘,娶她为妻,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
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一个栖身之地。
但死并不容易,内热时退时起,病情时好时坏。安娜-玛丽忠心耿耿地照料他,既不失夫妻情分,也谈不上爱他。路易丝早就告诫过她要提防房事:新婚出血之后,便是无休无止的牺牲,以及忍受夜间的猥亵。
我的母亲效法她的母亲:只尽义务,不求欢快。
她不怎么了解我父亲,结婚前和结婚后一样的不了解,以致不免有时寻思为什么这个陌生人决意死在她怀里。
家人把他转移到离梯维埃几法里指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外的一座农庄里,他父亲每天坐着小篷车去看他。安娜-玛丽日夜忧心忡忡地看护病人,累得精疲力竭,她的奶水枯了,于是把我送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奶妈处寄养。我一心一意地等死,因为闹肠炎,或许因为抱恨含冤。
我母亲时年二十岁,既无经验,又无人指点,在两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之间疲于奔命。
疾病和服丧使她尝到了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滋味儿。我却从中得到了好处:那时候做母亲的自己哺育,而且喂奶的时间很长。要不是我们父子同时病危,我说不定会因断奶晚而遭受磨难。由于生病,我不得不九个月就被强行断奶,发烧以及发烧所引起的迟钝反倒使我对联系母子的脐带突然剪断毫无感觉。我投入了混沌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幻景和原始的偶像。我父亲一死,安娜-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我的病好了,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儿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

Jean-Paul Sartre,1907
让-
巴蒂斯特之死是我一生中的大事:他的死给我母亲套上了锁链,却给了我自由。
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
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要是我父亲活着,他就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幸亏他短命早死。我生活在背负安客塞斯们的埃涅阿斯埃涅阿斯,特洛亚王子。希腊人围城攻打时,他英勇抵抗;特洛亚沦陷后,他背着父亲安客塞斯并带着孩子逃亡。们中间,从苦海的此岸到彼岸,孤苦伶仃,所以憎恨一辈子无形地骑在儿子身上的传种者。
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没来得及成为我父亲的年轻死者,要是他现在复活了,可以当我的儿子。父亲早死是坏事还是好事呢?
我不知道,但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
。
①

Jean-Paul Sartre,1910
…………
①萨特用反讽的手法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叫“本我”或“伊特”,即无意识或潜意识,所谓支配人的生命的原动力;第二层叫“自我”,即现实化了的“本我”;第三层叫“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即属于道德、良心和理想的意识。这里萨特的意思是,没有受到父亲的任何影响。

Sartre in Lithuania 1965
人死了还不行,还要死的是时候。如果我父亲晚死几年,我本会感到有愧。一个懂事的孤儿应自怨自艾:父母讨厌见他,躲到天国里去了。
而我当时却乐不可支,因为我不幸的处境反倒使人敬重,显出我的重要性;我甚至把服丧也看成是一种美德。我父亲很知趣,他负疚而死,因为我外祖母老说他逃避义务,外祖父又正好对施韦泽一家的长寿引以自豪,所以他不容许别人三十岁就去世。因为女婿死得蹊跷,他甚至不相信自己有过女婿。到头来,他干脆把他给忘了。我呢,连遗忘都不需要,因为让-巴蒂斯特溜之大吉,根本不想让我认识他。直到今天,我为自己对他不甚了了感到惊讶。不过,他曾经热爱过生活,想活下去,曾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造就人的一生,这也就够了。
但家里谁也没有使我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
曾经有好几年我都看到我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肖像:一个矮小的军官,诚实无邪的眼睛,圆圆的秃顶脑袋,浓浓的胡须。等到我母亲改嫁的时候,肖像消失了。后来,我继承了父亲的书,我父亲跟他的同代人一样不善于读书。
我发现在书页空白处有他一些很难认的潦草的手迹,在我出生前后他曾有所悟,一时浮想联翩,留下这些记载。
我把这些书卖了,死者与我太不相干了。
我只是听旁人说起过他,就像听人讲“铁面人
②
”或“埃翁骑士
③
”
一样,而且我所知道有关他的事情都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就算他爱过我,抱过我,用他明亮的眼睛(
现在已经腐烂了
)饱含爱意地看过我,但谁也记不得了,真是空爱了一场。
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
家人向我暗示我不是某个死者的儿子,而是奇迹造成的孩子。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我淡泊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不是头头,也从来不想当头头。
命令与服从,其实是一码事。
连最专横的人都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以一个神圣的无用之辈——他的父亲——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把他自己遭受的无形的挨打受骂传给他的后代。
我一生中从不下达命令,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使人发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势的腐蚀:人们没有教会我服从。

Jean-Paul Sartre,1965
…………
②铁面人:传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出世后立即被宣布为王位的继承人,不料几小时后,他母亲又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应是路易十四的兄长(
据说,法国人把双胞胎中后出世的视为哥哥或姐姐
)。但王位继承人已经宣布,不能改变,于是王室把他的哥哥赶走。他长大以后,一直神秘地被路易十四关在监狱里,因为孪生兄弟长得很像,阶下囚被戴上“铁面罩”,一直到死。
③
埃翁骑士(
1728—1810
)
,法国间谍,他的神秘之处在于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是女。他被国王路易十五派到俄国执行秘密任务,后担任过驻伦敦大使馆秘书,并参加过欧洲七年战争(
1756—1763
)。一七七七年他回法国后,接到命令不许脱去女装,因此他很可能是一个男人。
 Jean-Paul Sartre,
1970
Jean-Paul Sartre,
1970
直到十岁,我单独一人跟一个老头和两个女人待在一起。
我的为人,我的性格,我的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我学会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自己。
我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一个他们带着自己的悔恨所创造的怪物。即使他们不在我的跟前,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和日光交织在一起,我每跑一步,每跳一下,都遵循着他们用目光所规定的模范孩子的标准,并继续由他们的目光来确定我的玩具和天地。在我漂亮而清澈的小脑袋里,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的思想在转动,但无一不受到他们的牵制,连一点躲藏的地方也没有。然而在天真烂漫的外表下却融入了一种难以言传、没有固定形状和确切内容的信念。这种信念搅乱了一切。我成了一个伪善者。不学习别人演戏,自己怎么演得出来?我这个人,辉煌的外表一戳就穿,这是因为我生来有缺陷,我既不能完全理解又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便求助于成年人。我要求他们确保我的价值,结果我在虚伪中越陷越深。既然必须讨人喜欢,我便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不过维持不了一会儿。我到处装作天真烂漫和神气活现的闲散模样,窥伺着良机。每当我以为抓住了良机,便摆出一副姿态,但总觉得这种姿态靠不住,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外祖父在打盹儿,身上裹着花格子毛毯。我瞥见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藏着赤裸裸的粉红双唇,颇令人难堪。幸亏他的眼镜滑了下来,我赶紧跑过去捡。他惊醒了,把我抱在怀里,于是我们演出了一场动人的天伦之爱,但这已不再是我所追求的了。那么我欲求什么呢?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也许我想在他乱蓬蓬的胡子里做窝呢。我走进厨房,宣布我要拌生菜,于是我听见一片欢呼声,欣喜若狂的笑声:“不,小乖乖,不是这样!把你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啊,对啦!玛丽,帮他一下!你们瞧瞧,他搅拌得多好啊!”我是一个做假的孩子,拎住生菜篮拌生菜只是做做样子,但我感到我的动作已变成了丰功伟绩。
演喜剧使我避开了世界和大众,我只看到角色和小道具;我小丑般地博取成年人的欢心,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忧虑当回事呢?
我真挚而急切地听凭他们摆布,以致对他们的意图毫不理会。
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他们是我的观众,一排脚灯把我和他们隔开,使我孤傲至极,但这种孤傲很快变成了焦虑。

糟糕的是,我怀疑成年人在跟我演戏。他们对我说的话似糖果般的甜蜜,而他们之间说话时则完全用另一种语调。不过有时他们也打破神圣的默契。譬如,我撅着嘴装出最可爱的样子。这是我拿手的动作,但他们用真嗓门儿对我说:“一边玩去吧,小乖乖,我们在谈话呢。”还有几次我觉得他们在利用我。譬如,母亲带我去卢森堡公园,跟家里闹翻了的爱弥尔舅舅突然出现在我们跟前。他神情忧郁地望着他妹妹,冷冰冰地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你,而是想看看小宝贝。”他说,我是家中惟一纯洁的人,只有我没有故意伤害过他,没有听信闲言碎语谴责过他。我笑了,很不好意思自己有那么大的威力,居然能在这位郁郁寡欢的人心田里点燃起爱的火焰。但很快兄妹俩议论开他们的正经事,互相一一列举自己的冤屈。爱弥尔抱怨夏尔
(外祖父)
,安娜-玛丽为夏尔辩护,但不时作些让步;后来他们谈起路易丝
(外祖母)
。我待在他们的铁椅子中间,被他们遗忘了。
外祖父是一位左派老人,他却以自己的行为给我传授右派的格言:真情实况和无稽之谈是一码事;扮演激情就能感受激情;人是有礼仪的生物。如果我当时已经到了懂这些格言的年龄,随时都可能加以接受。人们让我相信,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演滑稽剧,互相引逗发笑。我乐意当喜剧演员,但要求当喜剧的主要角色。然而在关键时刻,我却无影无踪了。
我发现我在喜剧中扮演的是一个
“
假主角
”
。我有台词,也经常出场,但没有
“
自己的
”
戏。一言以蔽之,我陪成年人排练台词。
夏尔恭维我,为的是逃避他的死神。我欢蹦乱跳,使路易丝
感到赌气有理,而使安娜-
玛丽感到处于卑贱地位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我的话,她的父母照样会很好地收养她,她也用不着对妈咪战战兢兢;没有我的话,路易丝照样能发牢骚;没有我的话,夏尔照样可以对着阿尔卑斯山脉的塞万峰,对着流星,对着别人的孩子赞叹不已。我只是他们不和或和好的偶然因素,其深刻的原因在别处:在马孔,在贡斯巴赫,在蒂维埃,在一颗生垢的年迈的心里,在我出生以前遥远的过去。
我为他们体现家庭的团结和原有的矛盾,他们运用我非凡的童年使他们各得其所。我十分苦恼,因为他们的礼仪使我确信,没有无故存在的事物,事必有因,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在宇宙中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当我确信这一点时,我自己存在的理由则站不住脚了。我突然发现我无足轻重,为自己如此不合情理地出现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上感到羞耻。

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无知变成我的知识,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
这位可敬的过客本应该给我灌输自尊,有了自尊,我便可以确立生活的权利。
生我者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如果我一生下来就决定让我将来进综合理工学院,那么我便一世有保障,无忧无虑。即使让-巴蒂斯特·萨特知道我的归宿,他也已经把这个秘密带到西天去了。我母亲只记得他说过:“我的儿子将来不要进海军。”由于没有更明确的指示,从我开始,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
如果我父亲给我留下了财产,我的童年就会大变样,我就不写作了,会变成另一种人。地产和房产给年轻的继承人照出他自己稳定的形象。他走在他的砾石路上,触到他的阳台的菱形窗玻璃,仿佛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他自己,他把财产的稳定不动变成他灵魂的长存不朽。
几天前,在一家饭馆里,老板的儿子、七岁的小男孩,对女出纳嚷嚷:“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主人。”好一个大丈夫!
在他这个年龄,我不是任何人的主人,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我稍微胡闹一下,母亲便轻声在我耳边说:
“
当心点!
我们可不在自己家啊!
”
我们从来都不在自己家
,住在勒戈夫街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我母亲改嫁后依然是这样。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一切的一切都借给了我,使我始终悬在空中。
这个世界的财富反映着所有者的本质,而我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既不稳定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钢铁生产不需要我。总而言之,我没有灵魂。
倘若我跟我的躯体相处融洽,那就十全十美了。然而,躯体与我,我们结成了奇特的一对。
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问自己是谁,他的身体受到贫困和疾病的折磨,
得不到合理解释的境遇反倒证明他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因为饥饿和随时可能死亡的危险确立了他生存的权利:他为不死而活着。而我,我既不富也不穷,既不能自认为是天生的幸运儿,也不能把我的种种欲望看成是生活的需求。我只是尽消耗食物的义务而已。
上苍有时(难得)恩赐我好胃口(不厌食)。我没精打采地呼吸着,懒懒散散地消化着,随随便便地排泄着。我生活着,因为我已经开始生活了。我的躯体,这个好吃懒做的伙伴,从来没有粗暴和野蛮的表现,只有过一连串轻微的不舒适,是一种娇气。但这正是成年人所希望的。
那个时代,一个高贵的家庭至少必须有一个娇滴滴的孩子,我正好是这样的孩子,因为我生下来就想着要死。
人们观察我,给我摸脉,给我量体温,强迫我伸出舌头。“你不觉得他脸色不太好吗?”“这是灯光照的缘故。”“我向你肯定他瘦了!”“不,爸爸,我们昨天还给他称过体重呐。”
在他们讯问的眼光下,我感到我变成了一件东西,一盆花。
末了,他们把我塞到被窝里,里面热得使我呼吸都感到困难。我把躯体和身上不舒服混为一谈,两者之间,我不知道哪一个叫人讨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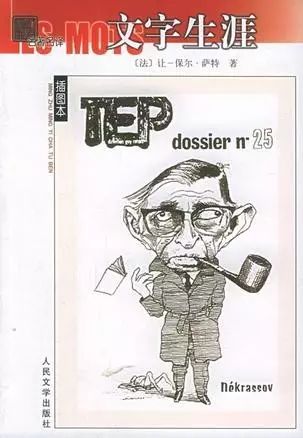
文字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01-01
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

# 飞地策划整理,转载请提前告知 #
本期编辑:野行人
[email protected]
招聘在此,点击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