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ID:ibookreview
『阅读需要主张』
“你住在北京啊!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家在东北腹地一个村庄的“三舅”说。——一句朴实自然的话,照见的是城乡差距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地域“层级”。一个不发达地区的村子,是“落后”而不受待见的。
但跟“三舅”聊天的这位美国人还是搬去住了,他住了两三年,体验生活,做调研,跟亲戚邻居们聊天。他叫迈克尔·麦尔,在美国大学里教授非虚构写作,他所去的大荒地村,是他妻子的故乡。他把自己在东北的见闻和调研写成了一本书,中文版书名为《东北游记》,他说,“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而这次,他想写写农村。
一个“老外”花这么多时间在东北农村居住、写书,当然是新奇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看到了什么?书评君采访了《东北游记》的作者迈克尔·麦尔,和他聊聊他眼中的东北、农村和变革。
东北的历史不算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一条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途径的建筑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走过的路旁,种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可以看见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木头的淡香;在溥仪的“傀儡皇宫”,曾经就关押过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频繁出现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时至今日,这片曾因担负使命而备受关注的富庶的土地却在公众话语中频繁被“唱衰”。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想要借东北触碰尚未远去的历史余温,却没料到自己在这里,瞥见到了中国的未来。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中文名:梅英东。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主要作品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并曾获多个写作奖项。
2010年到2012年,在北京与自己的中国妻子相识之后,迈克尔·麦尔决定做一次“上门女婿”,到妻子的东北老家住上几年。就这样,迈克尔·麦尔来到位于东北腹地的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他租了一间当地的房子,睡火炕,烧柴禾,在小学教英语,并且记录下这座边陲村落的兴衰变迁。他艰难地寻找柳条边遗址,四处打探能流利说满语的老人,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村落间的草木中发掘历史的残存。结果却发现,那里的历史没有写在书本上,而是存活于村民的记忆,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
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
在东北的荒地村,迈克尔·麦尔身兼多职:不仅是旅居荒地的游客,住进村庄的“倒插门女婿”,小学的志愿英语教师,更是这片土地过往与来兹的见证人,是东北盘根错节历史的挖掘者和记录者。
一向对社会大变革时期兴味浓厚的迈克尔·麦尔,为荒地村的命运忧心,他亲眼见到这里推掉农田和三姨的虞美人,建起一条条公路,东福米业骄傲地蚕食着农民们的劳动成果,同时让他们远离过去的生活。“再见古都”的梦魇于是重现:“荒地村几乎复制了同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开始这种感觉相当糟糕,就像同时踏入两条相同的河流。”
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 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
早在1995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第二批“和平队”志愿者,从明尼苏达的一个小村庄来到中国四川,担任英语教师。那时,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的他,更希望自己被派去拉丁美洲。而当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国时,面对着如此“庞杂博大”的国家,迈克尔·麦尔发现自己不会用筷子,不会说中文,除了长城,对中国一无所知。
四川的支教结束后,迈克尔·麦尔只身前往北京,在大栅栏地区的胡同深巷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并在附近的煤市街小学教起了英语。他租一间四合院,和胡同里的住户共用厕所,洗公共澡堂,读《北京晚报》,时刻关心拆迁的消息,吃当地人吃的小面馆。
2008年,麦尔的非虚构作品《再会,老北京》问世。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
前门大街改造的时候,施工方曾经用挡板遮盖沿街两旁的房屋,上面写着:“再现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路人,好事地把这个标语做了一点修改,却道出了更多人的心声:“再见古都。”
《再会,老北京》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译者:何雨珈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和当年听闻“再见古都”的遗憾心境类似,《东北游记》也是献给一段在现代化浪潮中被人飞速遗忘的历史:“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总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想要在一些事情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个细节。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从何处来,她的家又将迁往何处。等到他长大了,自己能够去了解这片土地,它估计早已永远变改。”
新京报:在抵达大荒地村之前,你想象它是什么样子?去到那里和离开之后,它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迈克尔·麦尔:我之前想象中的荒地,应该和四川,还有我在美国长大的乡下差不多。但大荒地的人民更聪明,更富有,比这些地方的人更老于世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对于生活的专注。住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归属感,不会觉得一个人能给这个地方带来什么改变——那是别人家的城市,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城市。在乡村则不同,你要想种点虞美人,让马路变得更好看,那你去种就行了。
新京报:除了想要了解妻子的故乡之外,为什么选择大荒地作为写作对象?
迈克尔·麦尔:你想读的书不存在,就是时候写一本这样的书了。之前我用了几年时间研究北京,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城市变革的书《再会,老北京》。我想了解中国另一片土地——乡村究竟在发生什么。
新京报: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在写作过程中,这个目标是否发生改变?
迈克尔·麦尔:我在北京的时候,在胡同的一家小学教过书,这些六年级的学生毕业之后必须离开那里,回到他们的故乡。按照法律规定,移民到中国城市的家庭的子女必须在他们的老家,也就是他们的户籍地进行小升初考试。我所教的班级差不多一半的学生都从北京回到乡下了。我写这本书的最初目标,是想了解他们回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他们在那边过着怎样的生活。
没想到的是,和我在北京多年的所见与所闻类似,我落脚的那个村子几乎复制了同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开始这种感觉相当糟糕,就像同时踏入两条相同的河流。
新京报:在之前的采访中,你曾表示对于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时期的兴趣。为什么变革时期这么吸引你?
迈克尔·麦尔:我对于大混乱(great disruption)的历史时期非常感兴趣,比如宋朝,清末民初,以及当下。在这些社会大变革时期,总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想要在一些事情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个细节。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从何处来,她的家又将迁往何处。等到他长大了,自己能够去了解这片土地,它估计早已永远改变。
新京报:“你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呢?”你在这本书中借三姨之口,回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否仅适用于中国,还是全球普遍存在?你如何理解?
迈克尔·麦尔:这对于中国治下的地区当然适用,而且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全球范围的社群内应该自问的问题:我们想要如何生存?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交往,我们需要从邻人或村庄那里获得什么?对于你的居住地,你是否有归属感?我们又如何参与到它的规划和发展之中?
新京报: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这里的所谓历史,是属于每个人的,活生生的,每个村民的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这就意味着,和写在博物馆、报纸、历史档案、书籍中的历史相比,荒地的历史是不稳定的、易逝的、个人化的。那么在捕捉这样的历史时,你曾遭遇何种困境?又是如何解决的?
迈克尔·麦尔:我写《再会,老北京》时,采访过冯骥才,是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大部分中国的历史都是民间史、民俗史、口述史,这意味着随着人们年岁渐长、生命消逝,这些历史就会散佚。“这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他对我说。我在寻找柳条边遗址时,或者在找能流利说满语的老人时,一直将他的话铭记在心。
困难来源于选择哪一种版本的历史更好。在这本书中,你会注意到我是如何平衡“官方史”,博物馆中的历史,以及“非官方史”,三姨等人说的话的。
作者和村民们在辽宁省西部寻访柳条边(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而修筑的土堤)。
新京报:似乎你曾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中搜寻一些历史信息,但却失败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使用同一种国家话语:“参观者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作为一名来自国外的社会历史研究者,这种国家话语究竟是丰富了你的研究,还是成为你继续深挖的阻碍?
迈克尔·麦尔:这是个非常有洞察力的问题。我在书中囊括了博物馆叙事,为的就是展现这些历史事件的官方版本。能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们并非“不真实”,它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丹东断桥上的牌匾,并不能重现中美之间那场难以想象的战争,是如何只炸掉一半桥的。民族叙事是起点,我读了那些竖在历史遗迹上的牌匾,然后开始揣摩字里行间的含义,接着通过调查研究补全整个故事,或者至少补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新京报:你说过,写你熟悉的人比写陌生人要难。在何种程度上,这一点让你写《东北游记》和《再会,老北京》有所不同?《东北游记》中,大部分的受访对象都是你的亲戚,你如何客观记录?在社会关系相对封闭的村庄,作为村民们眼中的“老外”,你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
迈克尔·麦尔:写那些你熟悉的人的确比写陌生人要难。看那些写自己父母或伴侣的,有多难。我的策略是在社群中表现得太过无聊,以至于他们最终意识不到你的存在。第一周,他们说:“看,这人是个老外。”一年后,我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了,也就没人好奇为啥一个老外站在稻田里,和一群鸭子说话。
新京报:在书中你写道:“在中国,做研究是横向的。一个人把你介绍给另一个人,就像一个个绳结。”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是怎样的?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与众不同?
迈克尔·麦尔: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在波士顿和华盛顿待了一周。你向图书馆管理员寻求帮助,然后她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写的原始文件拿给你。我手里握着他的护照,他的遗嘱,他的出版协议——所有这些都是他1800年左右签署的。任何人都可以像我这么做!没人问我要身份证,也不问我在哪里工作,或者为什么想看这些东西。当然我知道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乾隆批过的文件,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关系或者不从属于哪个单位,你得费多少力气去找到那些文件。
《东北游记》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译者:何雨珈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2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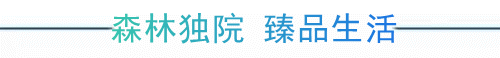


点击图片
购买《海错图笔记》《掌中花园》两件套
或者点击“阅读原文”去我们的微店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