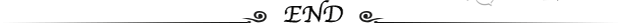乔治·巴塔耶 /文
○●○●
lightwhite /
译
拜德雅·卡戎文丛主编
泼先生执行编辑
在《眼睛的故事》之前的一年,我写了一本名为《厕所》(
W.C.
)的书:一本小书,一份相当疯狂的书写。《厕所》和《眼睛的故事》一样地忧郁,它是不成熟的。《厕所》的手稿被焚毁了,但不算损失,考虑到我当下的悲伤:一声恐怖的尖叫(对我自己的恐怖,不是因为我的放荡,而是因为哲学家的头脑,从那以后……何其悲伤!)另一方面,我甚至对《眼睛的故事》的爆发性欢愉感到满足:什么也不能将之抹去。这种欢愉,近乎天真的荒唐,将永远超乎恐怖,因为恐怖揭示了它的意义。
《厕所》的一幅画展示了一只眼睛:断头台上的眼睛。孤独的,如太阳一般,直立着睫毛;它从断头台的半月形缺口上凝望。画被题为《永恒轮回》,而它恐怖的机器是横梁、刑具和立柱。一条从地平线上而来,通往永恒的道路穿越了它。一组戏仿的诗文,源自《马约尔协奏曲》(
Concert Mayol
)的概要,补充了标题:
神啊,乐音的深渊里
死尸的血如此地悲伤。
《眼睛的故事》里有另一种对《厕所》的追忆,就在题名的一页上,它将其后的一切都置于最可怕的符号之下。笔名Lord Auch(洛德·奥什)指的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一个习惯:当他恼怒时,他不说“
aux chiottes!
”(拉屎去吧!),而是把它简化为“
auxch
”。Lord在英语里是指(《圣经》里的)上帝:LordAuch就是正在排泄的上帝。这事过于生动,不便细述;每一个造物都这个位置上容光焕发,沉溺于其中的上帝更让世界重生活力。
成为上帝,赤裸着,如太阳一般,在雨夜,在一片田野里:赤红的,神圣地,以一场暴风雨的威严,泼散粪肥,做着鬼脸,凌乱不堪,在泪水中成为
不可能
:在我面前,谁知道何为威严?
“良知的眼睛”和“正义的丛林”是永恒轮回的化身,还有什么懊悔的图像比这更加绝望?
我把《厕所》的作者命名为特罗普曼(Troppmann)。
夜晚,我赤裸地自慰,在母亲的尸旁。(一些读过《巧合》的人怀疑它是否具有小说本身的虚构特点。但就像《序言》一样,《巧合》具有一种真正的精确性:R村的许多人可以作证;何况我的一些朋友真地读过《厕所》。)
令我更加不安的是,我不知多少次看着我的父亲排泄。他会从那张盲眼的瘫痪病人专用的床上下来(父亲失明并瘫痪)。他要下床并坐到便壶那里可不容易(我会帮他),他穿着长睡衣,通常还戴一顶棉睡帽(他有一脸锐利的灰胡子,邋邋遢遢,一颗硕大的鹰钩鼻,广阔而空虚的目光盯着空中)。有时,“闪电般剧烈的疼痛”让他嚎叫如野兽,他伸出弯曲的大腿,徒然地紧抱在怀中。
当父亲失明(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母亲就怀上了我,我无法像俄狄浦斯一样挖出自己的眼睛。
和俄狄浦斯一样,我解开了谜:没有人比我领悟得更深。
1915年11月6日,在离德国边界几英里远的一座被轰炸的城镇中,我的父亲在遗弃中死去。
我的母亲和我在1914年8月德军进攻的时候抛弃了他。
我们把他留给看门人。
德军占领了小镇,随后撤出。我们如今可以回去:我的母亲,无法承受对它的想念,发了疯。那年末,母亲恢复过来:她不许我回到N镇。我们偶尔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只是在痛骂和胡言乱语。当我们得知他快要死了时,母亲才同意和我一块回去。在我们达到前的几天,父亲就死了,临死还在呼唤自己的孩子:我们在卧室里看见一口盖好的棺材。
当父亲在一夜的幻觉后发疯时(大战前的一年),母亲派我去邮局发一封电报。我记得自己在途中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自负。不幸压倒了我,永恒的嘲讽回应道:“如此之多的恐怖注定了你的命运”。几个月前,十二月的一个不错的早晨,我告诉父母,我不会再踏入高中,他们听后极其恼怒。但怎样的恼怒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心:我独自居住,很少外出,只走田野的小道,避开大路,怕会撞见朋友。
我的父亲,一个不信教的人,死前拒绝会见牧师。年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信教(母亲则不一样)。但1914年8月,我开始会见一位牧师;直到1920年,我没有一周不忏悔自己的罪!1920年,我又变了,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除了我未来的可能。我的虔诚只是一种逃避的尝试: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逃避我的命运,我正在抛弃我的父亲。今天,我知道,我是“盲的”,不可度量的,我是一个被“遗弃”在尘世的人,正如被遗弃在N镇的父亲。不论是在尘世,还是在天国,没有人关心父亲临死的恐怖。然而,我相信他无畏地面对了,一如既往地。在父亲茫然的微笑中时常浮现了怎样一种“可怕的自负”!
《眼睛的故事》序言,选自《小人物》[
Le Petit
],1943年
-
相关推荐
-

《眼睛的故事》
+
《聖神
·
死人》
喬治
·
巴塔耶 著
尉光吉 王春明 译
逗點文創結社
2018
年
4
月
文庫本
576
頁
600NTD
9789869609418
点击文末
“
阅读原文
”
查看购书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