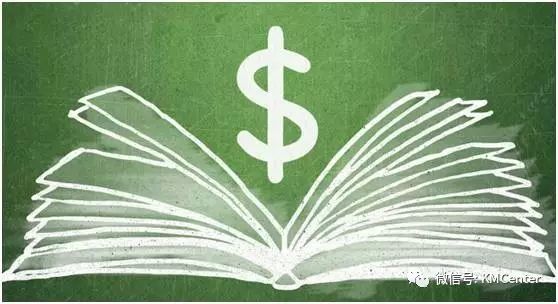1
、逄山高,逄山高,逄山只到方山腰
青州王坟镇区的东南即小有名气的逄山,数十次经行233省道过逄山北侧,早远远地惊艳于它的奇伟峭削。终于在一个夏日午后,我越过“神秘山寨”奋然从逄山南麓登顶,才一路领略了它的林木丰茂和谷幽壁静。踏上逄山山巅,顿感心胸开阔豪气内升。放眼东北西三面,群峰如涛,尺寸千里。唯独它的南方,视线却终止于约五六里处。远远望去,一排峰峦兀然壁立,森然诱人。孤立而秀出的壁峰齐削侧立,却一无尖形突起,似与东边比邻的一剑状奇峰无一丝呼应。下山好奇地询问当地人,才知道那是方山,还从他骄傲的口吻里,得了“逄山高、逄山高,逄山只到方山腰”的说法。后搜索网上的介绍,说因其远望方正、顶部成圆形而得名,原称“砚台山”,后演为方山。
转眼到去年深秋,才得第一次方山之行。一大早驱车,从“神秘山寨”山门西侧,小心翼翼驶过一大段破碎不堪面目全非的水泥路,到尽头的一个小停车场。停车场东向的一条蜿蜒向上的石阶,让我想也没想便轻松地拾级而上。两边全是密林,不时透过的一线阳光,和偶尔入目的几棵稍稍变红的黄栌,让向上的步子变得凉爽而惬意。但突然的变故却一下把沮丧丢给了我:石阶戛然而止,前面再没有路的痕迹,只剩一道一米多宽的碎石流。硬着头皮,兼手脚并用,更兼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回头往下看,终于攀爬过了最后一段几近垂直的岩壁。我顾不上后怕,我以为站上方山山顶了!
但方山还在眼前!不容我不承认,——其实我也觉得大概不会如此简单地登顶方山之巅。这次看似艰难的攀爬,只是让我比在逄山巅离方山近了一大步,可以更清晰地欣赏方山主峰罢了,虽然任由惊喜变成失望,虽然感觉与想像中的方正之山大有不同!在平坦的山顶很容易地找到了一条向方山进发的小路。伴随小路的风景,除了远山,除了“山顶草原”,我还遇见了好几棵阳光下红得耀眼的黄栌,还兴冲冲地登上了一座有十几米高的“山顶之山”。它却够陡峭,虽然在远处看起来只像山顶耸起的一支牛角。从“牛角”退下来,又从“牛角”根绕过去,才终于抵达方山绝壁下的一段缓坡。但没有找到向上的路,反而在目测中远远望见,在方山主峰西麓的一条小道上有人正在上行。而我顺着我脚下踏着的小路,继续往前竟是通向山下。“也许他们正走的才是攀登方山的‘正道’呢”,脑海里突然冒出这种想法就再也挥不去。
望望快到正午的太阳,我咬了咬牙,毅然做了下山再上山的决定。在又钻出密林,到一个像是峭壁中间的缺口,我赶上了几个正休息的攀登者。他们说这里就是方山主峰,是逄山一带山脉的最高峰,向东能登顶然后翻下去,但下行时要经过一大段很危险的地方。他们还说,从方山南侧也可以上来,车能开到山脚下,不用去跑那些破败的水泥路。但他们的“一个人尽量别去冒险翻越”的建议,却让我泄了气。看看接近下午2点的时间,我无奈地按那条“正道”下山了。
折腾了大半天,自远及近将方山的北面和西面纳入眼中,端详备至。但说好的方山之方,说好的“砚台山”呢?反正我没看到!过了一段时间,好奇让我又一次绕到方山南侧的山根下,自下而望,对于方山之“方”依然一无所得。
2
、始得方山方,偶遇桃花早
今年春节前后,偶然从233省道折道南行经过上梢村,出村南西望,见一山突兀如剑,耸然刺天(后来知道叫笔架山)。又稍往南行,升至南山半坡,回望时竟蓦然看见心目中的方山!虽止远望,一如百度图片“砚台山”的方正温雅瞬间映入眼帘,一望而入心。
正月二十七周末得闲,虽雾锁霾横,因念念不忘脑海中的方山影子,毅然驱车前往觅踪。从上梢村南寻得一小路望笔架山上行,攀行约一千米到达笔架山根,四周诸峰已尽落脚底,唯有笔架耸然独立眼前,却了无方山的影子。唏嘘着笔架的肃然而立、雄俊迫人,仍按脑海中的方位,沿小道舍笔架南行。没走几步,方山丰姿却渐行渐出,倏然现于眼前!展眼之间,方方正正的方山周畔薄雾浅绕,似乎在印证其温文尔雅、云淡风轻,又像是自敛其锋为更显笔架之雄要,而以柔情绰态示人,任从脚下从南至西诸峰,熙熙然环绕如培塿欲拜状。我听由峰顶小路带我向南,转到离方山二三里远的南山山巅一路西行,方山大方的腰身随着山势起伏,一路如影随形,若谦谦以君子之姿示于旅者,而“砚台”、“笔架”携手间的诸石林造型却如候读小童憨态而立,令人不觉忍俊中心暖。这才是我心仪的方山之方,方山的方正温雅!“古之人不余欺也”:方者,端正、方直,又喻立己方且厚,不必尽人知。
接近正午,恋恋不舍地下山时,天空已日现雾散,心情也被方山英姿渲染得大好,全然不知还有惊喜在不远处等着我呢!下行至山腰时放眼北望,蓦然间有数点亮色在初春略显干燥的山林间跳动着,像在召唤还兀自沉浸于欢欣中的我。迫不及待就前,奇观如约而现:山腰的北坡竟有十数株桃花已然竞放,在这正月天!迎着我惊诧的眼神,桃花于染红的枝条点点绽白,争先开放了朵朵如迎风展颜。周围很多树的枝条上也都微微鼓起了毛茸茸的红色花苞,如新娘般羞涩含笑,如玉般娇嫩,如雪般晶莹。俗话说,二月杏花闹枝头,三月桃花粉面羞,是不是贴近“砚台”、“笔架”,桃花才一反娇羞女儿姿,以满面洋红傲然争艳于正月?东风催绽,桃花惟早不输杏,自然之美,大概也因为这些不寻常吧。
但对于方山,还终究止于远观。
3
、南麓:方山宽厚,笔架巍峨
秋初的一场大雨后,急奔钓鱼台水库欲观雪瀑。未料先前的宏壮瀑布尽失滔滔,澎湃如雪变成窈窕的银帘倒挂,一时兴致全无。闪念间,脑海突然填满了方山的影子。
车行至方山南侧,按照去年那个攀登者的指点,我找到了一条登山的小路。由于中午还有应酬,时间有些紧张,所以一开始爬得很急,也全然没觉得铺满泥泞的小路难走,只是一会儿便气喘吁吁了。想起回头看一看风景时,才发现已将南面的那些山峰甩在了脚下。雨后的山峦,葱绿滋润,再远处竟还有如带的浅云轻绕山尖。而仰望方山,竟已全被松林遮蔽。稍作停顿喘了口气,穿过一小片松林,再抬望眼,刺天的笔架山竟如已近在咫尺,虽然目测它仍在几百米外,但已不像大致标准的圆锥那么中规中矩地坐落群峰之巅。从它往西,也由书童变作了按高低排队的一群卫兵,一路倾斜下去,像要牵手松林后面只露出一撇倩影的方山。
再向前变得义无反顾了。前面是大片的松林,林中打湿了的小路倒也并不十分难走,但我却不得不穿行一小段便离开小路,到东边树林的的边缘:除了注目仰视越来越显巍峨的笔架山,更是在渴望一睹一点点掀开面纱的方山英姿。终于在一处向东突出的松林边缘,它得偿我所愿了。眼前的方山,像一堵墙,从它西端几近90度的墙角,向东绵延着几十米。抬眼仰望,它已失却了远望时棱角分明的方正,但却凭添了几分圆厚的温柔。顶端和向南的一面,也松松地多了一些弯弯的弧形,而像大气而宽广的怀抱。匆匆沿小路穿越了几十米松林,尽头是侧立千尺的绝壁,我知道我已经触摸到心仪已久的方山了!以前的攀登者细心地留下了标记,沿小路从绝壁下折向西行,应该可以进军方山之巅。但望望脚下深得吓人的悬崖,和被雨水打得湿滑的悬崖腰间小路,我看了看时间,劝自己打消了登顶方山的念头。
三访方山,止步其足下。
4
、四访方山终登顶
转眼间又到深秋,与一驴友谈起数访方山之憾,于投机间兴致再起,相约周末再访方山。
我们依然经逄山从方山北侧进山,顺利走上了去年从山上发现的西麓“正道”。一路是轻松的石阶徐行,让我们能能移出大多的精力注目深秋的山色。石阶左手边的一处断崖上,红叶已如春花一般怒放。而远山,仍未失苍翠的山坡上,也点缀了一朵朵的红色,像一簇簇染红了的蘑菇,或南方的红山茶。流连着目不暇接的秋色,不觉已到了去年秋天攀援的终点,——那个像是在峭壁中间的缺口。缺口的左边是一段耸立的十几米的峭壁,峭壁的北边望下去就是悬崖,站在边上真怕随时会被风吹下去。而缺口的右边,就是那个攀登者讲过的要翻越的崖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