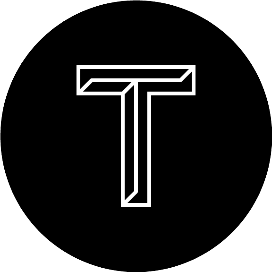德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 1989 年那一年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11 月 9 日,横亘于东西两德之间的柏林墙倒塌,连带着卷走了 28 年的历史,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融合在一起。出生于 1954 年的德国著名雕塑艺术家 Thomas Schutte 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德国:「1992 年,政治形势每周都在变化,这些问题尚未解决 —— 如何定义德国人,是由护照、血统、出生地、语言还是头脑?」
创伤是静默的,但它有痕迹。见证了这段历史的艺术家,不得不面对个人身份与集体记忆的分裂。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
的艺术界始终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Socialist Realism)
统治着,画家多技术精准、专注具象。两德统一后,长期被意识形态束缚的前东德艺术家们开始在传统技法之外,融入源自西方的现当代风格,以及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譬如其中的领军人物 Neo Rauch 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广场(方形)》看起来像一张来自苏联时期的宣传海报,标题仿佛指向一座城市的社会与政治中心,几何体、漫画气泡与拼贴似的人物显现出超现实主义的荒诞。这幅作品在 2014 年拍出逾 100 万美元的高价,令他跻身彼时世界最昂贵的在世德国艺术家之一
(在艺术网站 Artnet 于 2014 年列出的前 10 位榜单中,Rauch 名列第 6)
。

时代背景或许比艺术家的个人偏好更能解释他们的选择。如今依然位列 Artnet 榜首的 Gerhard Richter 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德累斯顿
(Dresden,1949 年起隶属于东德)
,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历经 1945 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后经受东德铁幕统治十余年。在柏林墙开始修筑的 5 个月前,他与妻子逃往西德,全新的艺术生涯始于踏入创作自由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那一刻。Richter 的抽象作品深受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 Jackson Pollock
(美国)
和 Willem de Kooning
(荷兰)
影响,同时不乏对
历史创伤与集体主义的反思。他的《比克瑙》
(Birkenau, 2014)
系列源自 4 张摄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照片,通过模糊「不可想像之物」,放大曾经的黑暗现实。

用 Rauch 的话说,他们这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注脚」。而很多下一代艺术家并没有做出同样的选择,至少看上去没有。
2024 年 11 月,Sarah Buckner 在 Longlati 经纬艺术中心展出了首场亚洲个展「浅赭深渊」,15 幅油画作品有如从一本童话书中散落的一则则故事。
沉重的历史没有落在 Buckner 的画布上,而是被隐秘地内化为更加个体化、私人化的情感与心理表达。
冷战时期的东德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下的集体叙事,而统一则带来了更加多元化和个人主义的叙事传统。
作为在
冷战余波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艺术家,Buckner 没有经受过冷战的意识形态束缚,这种世代背景使她能够以一定的超然态度探索历史,将其作为灵感来源,而非直接的政治评论。
「梦幻」「朦胧」这样的词汇常常出现在媒体对她创作风格的评论中。她在油画颜料中添加矿物原料,譬如孔雀石、朱砂与青金石,这使她的作品在初看之下,给人以厚重、粗砺的质感。随后,她会依照不同的创作主题决定颜料的稀释程度。譬如与作品《丝缎美人(孤身Ⅰ)》
[Icone Satin (Solo I), 2024]
相比,《工作室窗影》
(Studio View, 2024)
的色彩更为清浅,如同平涂了很多层的水彩而非油画。

色彩,是 Buckner 用画面讲述故事的一门「语言」。它们大多并不源于现实 —— 人的身体是斑驳的土色,被雾气笼罩的海是略显惨淡的奶白色。在创作中,Buckner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观察万物在不同光影下呈现的色彩。画《午夜》时,她曾长久地凝视卧室窗外的一棵树,观察它在由夜转昼的清晨会如何变幻,最终,她画下了一棵有着暗红色枝桠的大树。
2009 年,Buckner 入学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并师从英国当代著名画家 Peter Doig,一学就是 8 年。Doig 沉溺于风景画,且不同于印象派天光云影的柔美,着色诡谲如同邪典电影中的画面。可以说,她对超现实画面的偏爱、在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游离,以及对色彩和纹理的处理,都能回溯到 Doig 的艺术风格中。
但 Buckner 没有画成另一个 Doig。她把 2017 年,也就是离开师门的那一年,当作自己独立艺术生涯的开端,「那是我与同事分道扬镳、开始变得更自我、找到自己声音的那一刻。」古典性是其一。在她的画作中,人物与场景元素层叠平铺,没有纵深感,像在同一张图层中融为一体。这种非写实的空间处理令人联想到早期的宗教壁画,柔和的、类似矿物颜料的色调营造的自然褪色的效果,也传递出一种历史感。
其二,是 Buckner 在创作中构建的某种文学性。她将电影、文学和神话等元素混合在一起,作品没有停留在视觉层面,反而触发了观众对记忆、情感和人类境遇的深层联想。2021 年,她来到德国明斯特市参与驻地创作,工作室外时常有玩闹的孩子凑近了打扰,令她的创作难以为继。创作《儿童之家》
(Kinderhaus, 2021)
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电影《无辜的人》
(The Innocents, 1961)
中,被神秘力量附身的恶童,以及法国作家 Jean Cocteau 笔下,陷入扭曲共生关系的兄妹
[《可怕的孩子》
(Les Enfants terribles, 1929)]
。她还擅于用典,将文学与神话融入画面:《奥德赛》中男主角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以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笔下,迦太基女王黛朵为爱牺牲的悲剧,化作了 Buckner 作品中隐喻性人物的姿态与表情,勾勒出时间与情感的张力。

如今,她的背包里也常揣着几本书,其中不乏法国思想家 Simone Veil 与作家 Susan Sontag 的著作。她的爱书随她的旅程一道辗转,美国、摩洛哥、秘鲁、玻利维亚、特立尼达、意大利,一路的邂逅被她转化成艺术表达,跃然画布之上。
「我所见过的一切和我去过的所有地方都塑造了我。」Buckner 如是说。正如绘画对她而言就像生活,既是表达,也是发现 —— 一种在事件发生的同时捕捉其本质的方式。也因此,Buckner 认为自己被迫进行着即兴创作。正如德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转变,这种即兴并非简单的随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固定套路和程式化的窠臼发起挑战。此刻,她还期待着下一阶段的到来,或是新的创作媒介,抑或是另一种叙事方式。下一步是什么,她也不知道,但她知道,「它一定会让我感到兴奋。」
以下对谈经过编辑和删节。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工作和生活节奏是怎样的?
我最近会花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也开始做更多令自己感到愉快的事,比如早上洗澡。
你创作的第一件艺术作品是什么?
我会说我创作的第一件作品是在我拥有的第一个工作室里画的。我将这些作品算作我最早的创作,因为离开艺术学校后,创作变得更加严肃了。那是在 2017 年 —— 那是我与同事分道扬镳、开始变得更自我、找到自己的声音的那一刻。
你的工作室怎么样?
我现在的工作室氛围非常好,幸运的是它有高挑的天花板和充足的光线。
你最差的工作室是哪个?
最糟糕的是我毕业后住的工作室,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炉子用来烧木头。生火相当困难,所以有时我不得不穿滑雪服
(保暖)
—— 但我认为很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艺术家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当你开始创作一件新作品时,你会从哪里开始?
我开始一幅画时,通常只是随意留下几笔或几道痕迹,仿佛必须先打破一扇窗才能进入其中。每次创作的过程都完全不同,就像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

你什么时候知道一件作品完成了?
当我能感觉到这幅画有自己的存在感时,我就会停下来 —— 如果它有生命的话。
你在乎艺术市场吗?
我不太关心这类话题。我喜欢远离它们
(市场)
,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事情。艺术博览会这样的地方并不是我认为的自己作品应有的归属。
你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会听音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