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赵雷因吟唱一首《成都》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读者君没有感到意外。
之后,在群里和人聊天,讲到这事儿。大家心照不宣,嘻嘻哈哈,列出了以下歌名:《兰州,兰州》(低苦艾)、《重庆》(刺猬)、《布拉格广场》(周杰伦、蔡依林)、《秀水街》(张玮玮)、《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跟我说话》(李志)、《秦皇岛》、《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万能青年旅店)、《安阳》(痛苦的信仰)、《西安事变》(黑撒)……
当然,讲个笑话,温州还有《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你没有看错,歌唱城市的地名、街道名、街景名已经成为了民谣、摇滚惯有的表达方式。它们用难以概括的名词归纳自己无法置放的乡愁,其中不乏杰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中耳熟能详的“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所哀悼的石家庄没落、灰败的景象。在如今盛行的场景中,这些硕大而无所指的名字被准确无误地播放,激起观看电视节目的全国民众对于地名各式各样的想象(以及批评)。
而在伊塔洛•卡尔维诺著作《看不见的城市》(以及布鲁诺•舒尔茨的名篇《鳄鱼街》)中,地名消隐,文字中“看不见的城市”却时刻唤起读者对于所居城市空间深重的记忆。那种曾经广泛、精微而难以言明的爱以不可挽回的速度离去,剩下的,便是《成都》中的“成都之爱”,《北京北京》中的“北京之爱”。
而这样的爱,像是被稀释了的爱。
今天这篇文章,就讲这个。
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曾提过一个关于名字的假设:游客告知一人带他参观牛津,这人带他看了教堂、纪念馆、图书馆和几乎所有牛津的地标性建筑物。游览结束后,游客却说:“这些地方都很赞,但我还是没看到‘牛津大学’啊?”
尽管对方可能饱含真诚,但获得一个名字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直接,这大概就是最近赵雷与成都之间发生纠葛的原因。在《成都》最初的现场版本中,本地年轻人没有现在舆论中的这种不满,因为这首歌对于当时的现场观众来说是个“惊喜”——直到他唱道“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的时候,观众才知道这首歌是写给成都的。最初,这首歌是一个礼物,赵雷在玉林路的酒吧里演唱,旋律慢慢拆开包装,露出作为礼物的城市的名字。
赖尔的例子指出我们无法真的把一个名字之下所指涉的某物和盘托出,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些孤立的地点之间基于时空与历史的联系,那么对于“带我去牛津”这件事情我也就无能为力了。这个著名的语言学假设在半个世纪前看起来还显得荒诞不经,但在交通便捷、旅行成本降低、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我们却每天都在遭遇:你上传了拉斯维加斯周边公路的照片,写下心情文字并一定要加上坐标,否则人们就无法分辨出这究竟是赤峰还是拉斯维加斯。城市的名字通过定位技术被实名化了,它不是一个被拆开的礼物,而是一个被贴牌的展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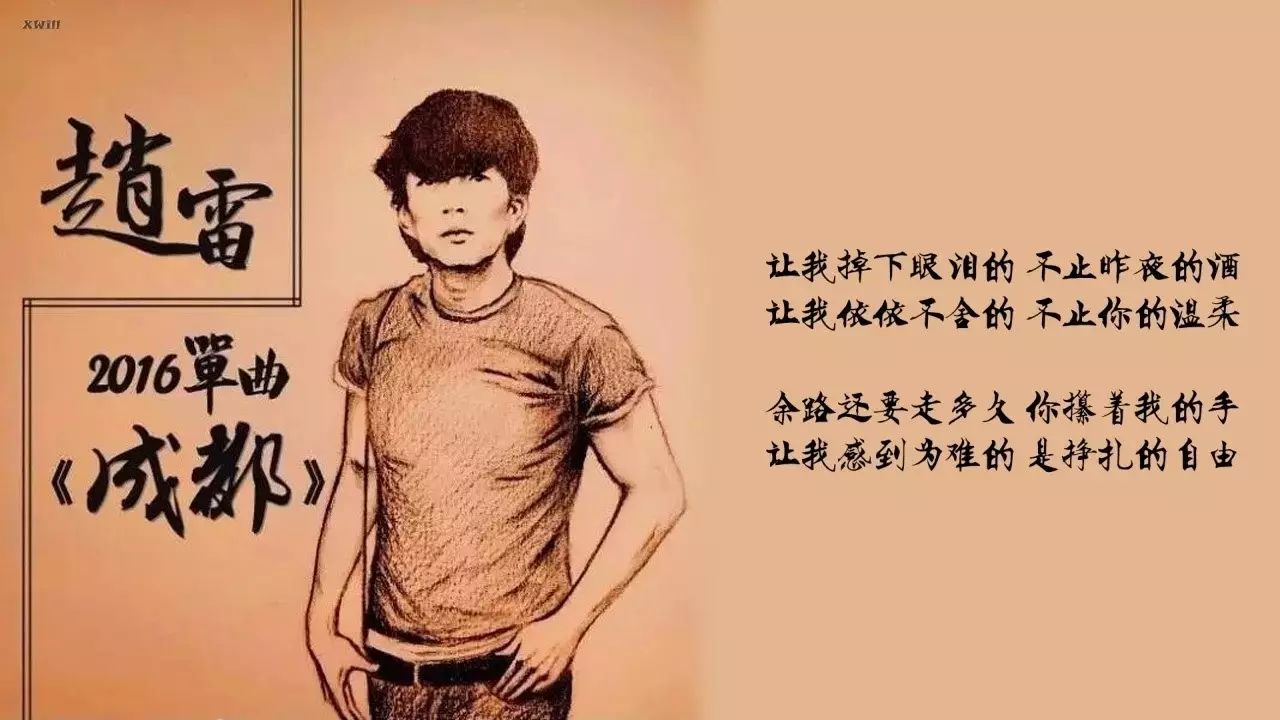
以报幕的形式被打在电视字幕上的名字就是这样的贴牌,一旦被搬上荧幕,民谣产生的最初语境就荡然无存了。民谣被赋予的职责正是弥合语言与存在之间的间隙,而非进一步撕裂它们,这意味着一个城市要在歌唱中获得它的名字。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有意识的作者甚至总是把名字抽离,让它变成一个你无法真正抵达的地点和一个无法证实的事实,这是我们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和艾柯《玫瑰的名字》中所看到的东西。早期民谣当中,老狼从未唱过“北大”字样,他只唱那些已然逝去的人。他们不是未名湖,在现有的时空中无法被找到,但是也因此我们才获得了那些名字。在传统修辞中,我们总是在“诉说”中轻轻“呼唤”名字,我们无法获得,或者已经失去。作者总是强迫自己不让一个事物以实名制的形式出现在作品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描述它,我们也就不能真正的理解它。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张密 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

民谣歌手的吟游是旋律本身的吟游,而非他到过某地的证明。一年多前赵雷在玉林路的小酒馆里唱了一首匿名歌,那时这首歌是如此恰适。但在今天的秀场上,它就太像是对歌手自身经历的实名制认证,如同简历上的条目,资格证上的钢印,它们具有来源不明的权威性,却没有任何交流的价值。这不仅因为今天的民谣已经失去了对于时光流逝的那份承担,也因为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将自己表达为一个整体。在本地青年人对赵雷的批评中充斥着很多本地的房产信息,高新区14000元/平的房价怪异地成为了批评《成都》的一个核心论据。
这种诡异的结合看起来是非常奇怪的,但也许这其中包含着民谣的批判性与城市实名化之间的根本纠葛:歌手唱地名和房产证上的署名是如此相近。在二线城市,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资产实名制泛滥的时代,这些细化到城区、学区、小区和人头上的区隔使得一个城市整体的生活形式变得支离破碎。集市和自由市场销声匿迹,路边摊合入美食城,它们有了自己的“实名”。但是就像哲学家赖尔的故事那样,这些孤立的地点怎么能够向你呈现我所“生活”的城市呢?“玉林路”怎么能安顿一份“成都之爱”呢?在对赵雷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一个地名的自然呈现,而是更多的割裂与贫富差距。这种批判中显现的东西,并不比赵雷在玉林路最初唱的那首匿名歌曲来的贴合。

赵雷
在本地闲暇的中老年人那里,成都依旧成立。他们并不清楚赵雷是谁,即使知道了,大概也会像对待客人一样宽容。这种宽容反倒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成都仍然“名副其实”。但是对于作为民谣受众的本地年轻人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还保留着本土性的生活形式,但同时也处于区域发展的拉扯之中。一面是来自一线城市的资本压力,一面则是被越抛越远的底层生活和周边地区。与一线城市的情况不一样,上海本身的城市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就是资本化的,而北京由于短期内的资本爆发,反而使其本土性借助资本优势得以保存。而像成都、武汉、郑州、西安、沈阳这样的城市,它们的本土性则在这种慢性的拉扯中不断被消磨。这些城市的本土年轻人也许仍然以地区中心自诩,但在周边地区的人们看来,它们大概更像是上海外环或者北京N环边的某个地方。

《我爱南京》,李志作品
在去年的房地产大潮中,南京、合肥乃至郑州这样的城市不再被视作省区的中心,而是上海“溢出效应”的承担者。上海只是“溢出”了一些边际效应,这些城市就失去了自己名字的载体。也许对于成都的年轻人来说,这就像一个来自北京的民谣歌手在二线城市的“新区”登记了一处房产——在本地的老一辈人看来也许根本就不算是“成都”的地方。
以地名入题的音乐也不乏好的作品,比如万年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和《秦皇岛》。当然,万青乐队是摇滚乐队而不是民谣,但是之所以他们能够把“石家庄”(rock hometown,摇滚之乡,一个巧合)这个名字唱好,也许是因为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了,它几乎就是北京高度发展的阴影本身,一个逝去的东西,一个已然消失的名字,因此乐队能够准确的抓住破败工业城市之中人的深层情绪。而秦皇岛则是一个在各种层面上“不曾出现”的地方,万青把《秦皇岛》唱出了神话色彩。崔健曾去终南山隐居创作,出来后写了一首《苍天在上》,而不是《终南山》。说到天空,中国著名的后摇乐队惘闻在《八匹马》专辑中写过一首《大连天空》,让我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听出了乡愁。后来我想,也许是因为后摇没有歌词,我能够根据我童年的经历判断这就是中山广场初冬下午四点的天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判断的这么准确,而对该区域此时所拥有的超过20000元/平的房价浑然不觉。
所以一个城市的名字本就不是城市本身,我们赋予一个地方以名字,是希望它在时间中长存,这是人们对记忆的承诺。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日本做一个面向中国人的旅游节目。这个节目中介绍的大多数地方都是日本大都市周边的区域。我曾以为这是一个旅游宣传节目,但是同学却告诉我,电视台做这个的初衷,是为了让在大都市工作的小镇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家乡还不错,不会完全不考虑回来生活,这样就可以了。也许因为这段交谈,当我后来看新海诚的《你的名字》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层面,那就是大都市要重新和小城镇建立联系,甚至从对小城镇跨时空的拯救中赎回自己的乡愁。而名字,那区分东京和小城镇的标签最终会融化在两者的相爱当中。我们最初所喜欢的那种民谣,也许应该是《你的名字》所呈现的样子。

新海诚电影,《你的名字》
关于《成都》的争论,我想根本上还是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个对个人资本占有极度敏感的时代,避免民谣甚至文艺作品带给我们这样的“误解”。也许文艺工作者们确实不该在歌曲中如此轻易的展示一个地名。虽然建议艺术家以一种无功利的态度从事文艺创作是一个苛刻而又陈旧的提醒,但是如果不是有意识的从这种对于“实名”的个人占有中抽离出来,艺术就难免会被纳入到这样的时代资本逻辑中。赵雷有一首live,也是唱地名的,叫《再见北京》,讲述了在新年清晨被迫离开北京的青年人的心情。我最初喜欢上赵雷也是因为这首歌,我想这才是民谣的力量所在,它能够在一种失望的表达中净化掉我们被迫“逃离北上广”的恐惧,从而转化成我们面对世事更迭、重获广阔天地的自由意志。
无恒产者亦有恒心,也许这才是我们寄托给民谣的最处的理想。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林云柯;编辑:一一。其它公众号、媒介,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