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这种区别在于只有人有大拇指,也有人说只有人才会笑。
或者两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只有人会自杀: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那自由的死会来到,因为我愿意死。”
瑞士作家卢卡斯·贝尔福斯的小说《考拉》最近推出了中译本,作家在这本小说中探讨的就是这种自由死亡。但是这究竟是“自由意志的英雄主义行为”,还是仅仅是人的胆小怯懦?
撰文|林晓萍
浓雾中的阴影
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自杀?
《考拉》这本小说,主要讲述了叙述者追寻哥哥自杀原因的过程。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早在20多年前就逃离了家乡,但哥哥却一直留在此地。两人之间关系相当疏远。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因为叙述者受邀回来作关于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的报告。饶是如此,两人也是匆匆一见,并未多言。数月之后,哥哥在浴缸内过量注射海洛因离世。在此之前,哥哥准备好一切:写好遗嘱,整理好住处,甚至还把房门打开,以防有人发现他死去的时候还要破门而入。
这种突如其来又轻而易举的死亡给叙述者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哥哥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就像是“归还租借的房子钥匙一般”,让他很是不安。他很伤心,随之而来的情绪就是愤怒,但是更多的则是不知所措。他要知道哥哥究竟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生命。最初的时候他仅仅是向周围的人询问,但他逐渐意识到,虽然他的熟人圈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类似的死亡体验,但是却没有人真正愿意谈论此事。唯有无尽的沉默不断蔓延。所以他转而在哲学中、在精神病理学中寻找答案。但是他最终还是不得不确定——哥哥自由死亡的原因或许只能在哥哥自己身上才能找到。
《考拉》
作者:(瑞士)卢卡斯·贝尔福斯
译者:陈壮鹰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2月
在这本并不厚重的书里,贝尔福斯探讨了世间最为厚重的话题:生与死。自杀,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终结,还是生命进程的另一种选择?
叙述者对于哥哥的回忆仅剩下一抹存在于浓雾之中的阴影。回忆中的哥哥是一个不勤奋、不工作的懒散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自杀?对哥哥自杀原因的叩问,将叙述带向了哥哥童年噩梦般的经历。那时哥哥得到了他的童子军名字:“考拉”。
卢卡斯·贝尔福斯的这本小说建立在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之上。他的哥哥在2011年12月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前提到过的关于海因里希·克莱斯特的报告是他在半年前完成的。克莱斯特作为“双重自杀者”在小说中不仅仅是叙事的一个开端,而且是小说叙述上的一个风格参照对象:贝尔福斯笔下整齐紧密排列的克莱斯特式的从属句法结构,将故事情节以及随之而来的沉思紧密结合——这使得故事情节叙述极为紧凑,并且愈发清晰。尽管贝尔福斯有时在叙述过程中显得过于冷静自持和疏远,但是他在文中从始至终都在坚持对哥哥自杀原因的追寻,完全不在乎将这种近似于拷问的探求推至痛苦的临界点,只为了得到一个可能出现的答案。
在无数次的追问之后,叙述者最终只得在关于哥哥的回忆中寻找他自杀的动因。而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哥哥身上发生的事,他愈发沉浸在幻想世界里。他此后叙述勾勒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他的脑海中的幻想。哥哥那天晚上的经历最终仅仅是叙述者纯粹的猜测。推测使得叙述者的想象空间的架构愈发变大,而哥哥的形象也逐渐在叙述者的讲述中显露出来。
此时,考拉,这一“完全无害的卡通形象”便成为叙述者的特别关注对象。叙述者没有任考拉带给他的不安消失,而是觉得“一定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这种不安的探寻最终偏移成对澳大利亚殖民历史的虚构性重塑。1788年,第一批来自英国的殖民者——囚犯和他们的看守人——出现在这片新大陆的海岸。14年后的一个炎热的11月,一个叫弗朗西斯·巴拉利尔的为英国效力的海军工程师将一只自由自在生活的考拉泡进酒精里面。但是在此期间,这些新来的殖民者并没有注意到考拉默默地从树梢上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些殖民者的澳大利亚拓荒历史表面看起来和叙述者想要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哥哥的生命——问题毫不相关。但是叙事者则是陷入了这个故事中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包括第一批运输犯人,还包括拓荒者开始尝试在这片未开发的处女大陆站稳脚跟,以及第一批大范围的深入大陆腹地的探险。这些殖民者疯狂地亵渎和羞辱考拉这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动物。考拉的迟钝反应让这些贫困的殖民者自认为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和刺激。这种行动迟缓的动物让人觉得害怕。贝尔福斯则是在这个节点上回到了叙述的出发点。
恐惧吞噬意义
一种在进取心之上的迟钝
虽然文中看起来在讲述两个无丝毫瓜葛的故事,但是作者的叙述其实相当精确和高度集中。随着考拉这一软萌形象的出现,叙述视角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个反应迟钝的动物突然成为引起害怕和恐惧的未知。考拉喜欢呆在树上一动不动,靠汲取桉树叶中的水分为生。而哥哥则是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这只动物是与他万分相称的代名词。此时,叙述者突然明白解开他迷茫的探寻之旅的关键就在于考拉的迟钝。选择顺从这种迟钝的人,是不会感到害怕的。
这是一种凌驾于人的进取心之上的迟钝。好胜的进取心是人类的道德标准。但是也正是这种好胜心使得人类不可避免地成为害怕和恐惧的牺牲品:正是这种道德标准驱使着人拼搏向前,不能无事闲坐。
“人就是恐惧,恐惧就是人。人把恐惧带到了世上。恐惧是他的创造物,是人为博物学做出的贡献。”人类为了对抗恐惧,选择了工作和拼搏进取。人类最深层的恐惧源于人类对于自身毁灭的害怕。而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工作和进取,才能在毁灭一切的恐惧和害怕面前筑起一道高墙,才能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赋予某些虚妄的意义,来美化工作带给人类的病态和卑鄙。此时,叙述者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谈论自杀的原因。一个选择自由死亡的人无需多言,无需抱怨。他已经用自己的行为为世人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还要苟活着?你们为什么不尽早结束辛劳?”为什么不行使这被工作攫取过后生命中仅剩的自由权利?
延伸阅读:《奥勃洛莫夫》
作者:(苏联)冈察洛夫
译者:陈馥/郑揆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5月
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摩夫养尊处优,尽管他设想了庞大的行动计划,却无力完成任何事情,最后只能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和废物。奥勃洛摩夫的形象标志着俄国十九世纪“多余的人”蜕化的极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
无所事事成为对这个已经完全经济化、充满了竞争和进取的社会的挑衅和反抗方式。如此,在小说开始提出来的关于自杀原因的问题就触及了核心:到底谁才是有理的那个?是像叙述者那样被生活驱赶着不断前进的一类人?还是像哥哥那样的人——除了安静地接受生活,并且等待生活的结束之外,对生活没有其他任何期待的人?叙事者慢慢明白——或许哥哥压根儿就没有不快乐。哥哥的不幸福其实只是他周围环境所认为的不幸福而已。但这根本算不上是对叙事者的安慰,更不要说是答案了。
卢卡斯·贝尔福斯打开了一个指向克莱斯特的文学共鸣空间。同样涉及此类话题的不仅有保罗·拉法格《懒惰的权利》,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加缪,还有超现实主义作家克维尔的讽刺小说《艰难的死》和像克维尔一样早早结束自己生命的瑞典作家史迪克·达格曼等等。因为就算自杀可能是约瑟夫·弗莱彻所说的“自由的标志”和人类“自主权和自由价值的体现”,它自始至终都暗含着对于生命价值的叩问。
达格曼和贝尔福斯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将这个问题和害怕相联。“现代人的一个悲剧就在于人们已经不敢去拥有‘害怕’这种情绪。这会是灾祸降临。因为如果人无所畏惧的话,他也就不再会去思考了。”——达格曼在他1945年的处女作《蛇》(Ormen)中如是说。
《考拉》这本书正是处于这样的语义场中,但是没有像奥勃洛摩夫那样寻求一种哲学上的冷静,也没有像克维尔或是达格曼那样专注于人对自身存在的绝望。克莱斯特行文风格上的冷静自持或多或少对贝尔福斯战胜这场危机有帮助。
1954年,史迪克·达格曼在自杀前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我们对慰藉的需求无法估量》。虽然贝尔福斯在一场访谈中提到,这本书压根儿就不能算是一种安慰,但是我们作为读者也不能要求仅用一本小说就能回答“人生的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终极命题。
抢先试读
人们对抗恐惧的药是勤奋。努力的人们有健壮的双腿,谁若没有双腿,却想努力的,就要来证明自己,并给出解释。干练的人是强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认真训练,保护强壮。工作再也不是惩罚,它变成一项项技能。懒惰被遗忘,被消灭,连同它的故事,它的祝福,它的花朵,它的是个。它的地方,它的床和桌,都还在那儿,却变成了作坊、厂区大街和管理机构。人类把世界变成了工作的地方。工作填充着空间,懒惰就躺进时间的怀抱,和她成了情人。懒惰喜爱伤痛,却不认得恐惧。
世间万象面前,它无动于衷,远近相融,懒惰不懂得区分现在和未来。要这个而拒绝那个,或是优先考虑其一。懒惰要评判,却不奋斗。而不懂得奋斗的,也不被允许活着。
我也沉迷在工作中,大清早就起床,完成我分内的事。睡觉也不过是为了第二天再次精力充沛地去工作。而我的工作成果不过是一堆垃圾,徒劳而已,为了工作而做的工作。告诉我你做的事吧,这一切不过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它不会帮助你,不会有益于你的孩子,也不会有益于世界,徒劳而已。我了解到,工作这个词的起源:它指的是这样一个孤儿,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为此受尽屈辱与奴役。
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活着?毫无创造。我们想吃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从日子那儿偷出来的。我们就是奴仆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而我们的上帝又是如此良心败坏,以至于我们从不曾察觉到工作已使我们变得多么病态和卑鄙。只有越来越努力才能克服重重障碍。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林晓萍;编辑:柏琳,张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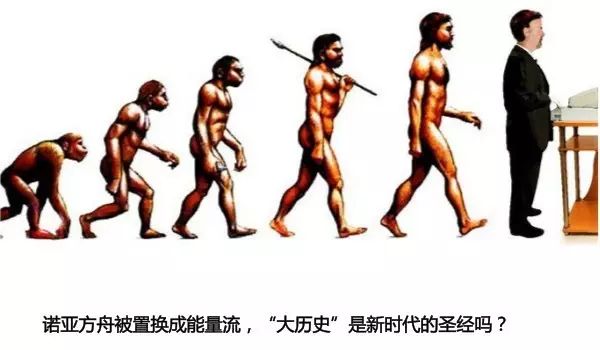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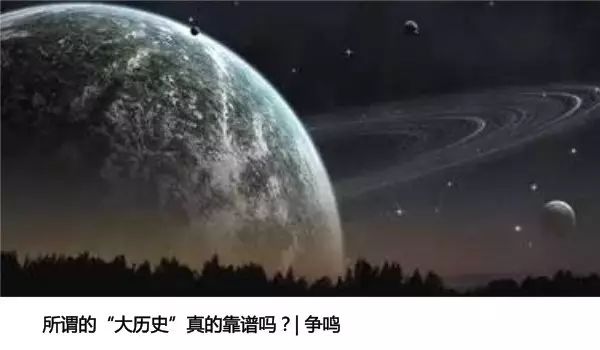
▼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