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1城市广州三年展站
|
作品分析图之一|
2008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访谈选自某次建筑杂志的同题问答活动。这一活动约请了几位作出跨界实践的建筑师/艺术家共同探讨“跨界”这一命题本身的诸多层面。其中包括,对“界”的认知,对艺术、市场、城市的理解,跨界的相关经验、计划与展望等等。
如今“跨界”已经逐渐从原本的实验状态走向成为某种人们熟识的策略和手段,甚至更进一步成为了一种常态。
而这背后真正需要考量乃至质疑的,是否并非各种跨界行为的后果,而是“跨界”这一概念本身得以成立的基础呢?这正是本次访谈点出并提请我们关注的议题。若以建筑师的实验以及跨界行动作为支点,它的力量更在于撬动了可能性与不可能之间的关系。这种行动是一种对可能性条件的选择?还是将已有的可能推向极限,面向不可能的可能性之挑战?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并不是可能性,而是选择,对恰当的可能性的选择。
访谈|A+C×王家浩 责编|
莲灿
+
BLOOM



选择恰当的可能性
|
建筑师的实验跨界?
|
访谈|2008
本文4000字以内

建筑与文化
(以下简称A+C)
:
对于建筑师而言,何谓“界”?
王家浩
(以下简称W)
:
我们可以指出两种不尽相同的界限。
首先是显在的,它
存在于建筑师与其他的社会身份(identity)之间,通过各种既定体制的相互交织、推进和递延而成。不限于建筑师的有更为普遍性的限定,例如教育、训导、奖惩、契约等,然后到专业化的限定,例如学科、建造、展示、媒体、会议等。从中,这种显在的界限得以不断地发展并巩固的。
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各种职业共同运作的系统,这一系统越趋向于成熟,它内部的关联也就越严密,同时现代社会也是由拥有不同知识与经验的主体交汇而成的,其中的差异逐步加剧的集合体。这两者是共存的,也必将在特定的个体内部形成某种潜在的界限。
这种潜在的界限才是我更感兴趣的。
在外力的作用下,它蜷曲、收缩,制造出自我监禁;它延展、拉伸,则导致自我分裂。
回到“建筑师”,无论作为个体的,抑或是职业的身份,这两者间的缝隙往往是难以弥合的。在我看来,这种身份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地具备摆脱目前的社会现实的特殊能量。
A+C:
跨界设计(合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W: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曾将将有效的跨界理解为不同知识与经验个体之间一系列的持续的波动状态,而且还要排除那些具有明确预设目的的组织方式。
如果按照这种看法,那么跨界的设计(合作)中最有意思的,并不是它直接的结果,而在于如何通过后续的检验,来判定
它偶然性的前提条件,过程中极端化的程度,以及必然导致的某种稳定的新的存在方式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A+C:
如何理解跨界合作,是商业策划,还是艺术创作?
W:
在我看来,对于跨界这一行动本身而言,商业策划和艺术创作并不构成一组相互对立的概念。
如果我们暂且相信每一次跨界合作的起点都是以创作为目的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完成的各种合作,大部分都经历了一个意义耗散的过程,其中又有大部分最终沦为商业策划的结果。
外力对特定个体的内部界限的形态变化具有绝对的作用。
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并不受个体自主的控制,
只是在某些偶然的、瞬间触发的场合中,(外力作用与个体自主)两者才得以遭遇。
这种情形正如
尼克尔森上校在
电影《桂河大桥》的结尾处,被一颗流弹所产生的推力,倒向了他并不愿意炸毁的大桥的引爆装置……悲观地讲,这种必然的巧合中充满着强烈的戏剧性。
A+C:
你认为,建筑师与艺术家的跨界合作能够带来什么?
相对于其他领域内的跨界行为,建筑师的跨界优势表现在哪里?
W:
跨界合作最理想的结果并不是为了产生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而是为了进一步地拓展各自学科原有的边界。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建筑师的工作总是以特定的地点和情境为前提的,而且一个好的建筑作品并不是以建成的那一刻为终点的。因此,并不是说建筑师具备怎样的优势,而是
要求建筑师能够以他专业的潜能,在跨界合作中保持更有力的针对性和持续性。
然而,在目前只依赖于即刻声明却没有经历过后续检验的跨界合作中,最大的危险是,各种伪命题的涌现。
例如,建筑师参加艺术展,艺术家造房子等等。
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作品或者建筑本身,而不是各自已有的身份,而另一种危险是,跨界合作的结果很容易成为可交易的时尚碎片。
例如目前不断扩散的看图解说式的城市研究方法以及浮皮潦草的呈现,这些表达方式至多成为了“专业观光客”跨国旅行中的休闲读物。

线性都市调研——利用艺术|
1999柏林、1997上海

 A+C:
对于建筑师来说,跨界设计是否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
A+C:
对于建筑师来说,跨界设计是否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变?
W:
在小说《百年孤独》中,几代主人公兄弟都只有一组相同的名字。
“阿卡蒂奥”一直没有离开过马孔多,而“奥雷连诺”总是试图到外面去闯荡。
而书的开头,一个自称为“梅尔加德斯”的吉卜赛人给村民们带来望远镜时候说,“科学缩短了距离。
在短时期内,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儿。
”事实上,这里的“望远镜”起到了“阿卡蒂奥”和“奥雷连诺”们之间的连接作用——它既在,却又远离故土的原点。
无论跨界设计的结果如何,更重要的是
既然在过程中需要改变建筑原有的专业手段,那么又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持建筑学自身的维度?
因此,我认为更准确地说,跨界设计对建筑师而言,应当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向,而不是改变。
A+C:
跨界设计对一个城市来说,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表现在哪里?
W:
如果我们将城市只看作是
一般意义上的
地理中的点,那么城市中的边界是一种对地点的确认方式。
当城市(或不同城市)之中的共同体(community)在努力维系所谓的跨界设计中的“界限”的时候,事实上,
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对于跨界设计结果的消融作用,将远超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我们从1997年开始的线性都市组有一个作品《利用艺术——线性都市调查》,它是根据到美术馆参观某一个艺术展出的观众所居住的地点,在展厅中从多到少地排列出一张张即时的线性的上海地图,它想说明的是,在现实中(共同体的)概念边界和地理边界往往是相互交错的,这种交错也必然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适的。
A+C:
谈谈你对“跨界”的理解。
例举你的跨界设计(合作)项目
W:
“跨界”是已有知识与经验之间的“集聚”,它并非来自于多个确定位置的身份,而是
由各身份所连带出的一系列异质运动构成的;
它通过聚拢,强化了不同个体间实践节奏的差异,偶发地却也是持续地制造着异质运动间的“摩擦”,从而激发共同现场的整体流动性。
从1997年开始,我们的线性都市组,参加各种艺术展出。
近几年中,比较有意思的作品“90度”,是我与艺术家王鲁炎在2005年海上海工地上举行的“间·隔”展(一个建筑师与一个艺术家共同完成一个样板间的“设计”)中的合作。
在这个方案讨论之初,艺术家希望将样板间整体做90度的翻转,把家具布置到墙上,而我希望通过多个不在场的设计师各自提出理想中的样板间,由此共同组成一个概念相互干扰的“弱形式化”的设计。

有时候自己什么都不做
比总想做些什么
或许会更好
最终,我将建筑图纸翻转了90度交给了一个不知情的室内设计师,完全按照通常的市场流程,由他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标准的样板间。回到现实中,它是再次翻转的,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作品。也就是说无论建筑师还是艺术家,在整个过程中,“什么都没做”,而只是调整了一下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观念作品也应当只适用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展出,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对象。
2006年,在“黄盒子·青浦小西门”的展出中,我把城市规划成果的展示迅速改造成一个临时的当地的迪斯科舞厅,所有常见的在政府的城市规划展示中的元素,例如灯光、多媒体、模型、声音与影像等等都没有取消,只是在节奏上、对位关系上形成急剧的变化。
2007年,与北大现代艺术档案共同合作策划设计的“十张纸斋(吴作人五十年前组织的一个晚画会)”展,因为展出内容的特殊性,涉及到原作和后期的代表作,历史文献,当事人采访录影以及画室场景还原等等,所以我们并没有按照常规的展示方式分类布置,而是借用了纪录片剪辑的方式,将各种内容组织在一个展厅中,使空间设计获得了介入展出叙事组织的能量。
之所以我经常与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专业技术上的额外支持,而是因为
过程中各自专业观念上的极限化,很有可能对已有的创作习惯起到“破坏”的作用。
而这种“破坏”既充满着风险,又带给我新的出发点。

青浦·迪厅|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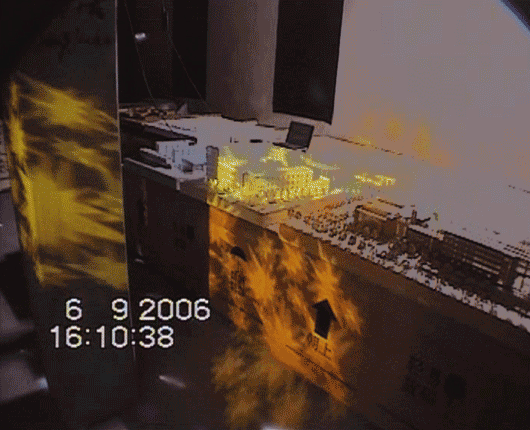
 A+C:
在你尝试跨界设计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C:
在你尝试跨界设计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W:
(建筑师与艺术家的)“共同在场”仅仅开启了一个通道的初始阶段,无论是学科内部或是学科之间,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位于同一个空间,却没有在个体之间产生已有节奏的相互波动之前,那么“可能性”仍然是一种悬置的可能。
而在跨界设计中,提供可能性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并不是可能性,而是选择,对恰当的可能性的选择。
为了“挪用”或“抄袭”已有的形式,而面向漫无依据的未来,或者刻意地遮蔽此处的现实,那么“可能性”只是即时行乐的消费品而已。
除了如何将已有的知识与经验推向极限,另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困难,还是来自于身份认同。
例如我从1997年底开始参加艺术展出,到现在参与过的艺术活动远超过建成的设计项目,尽管我自己依然认为我在创作每一个作品时并没有离开过建筑学的维度,但是人们还是会问我,究竟是建筑师和艺术家?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我而言,并不是太重要的,但这的确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A+C:
跨界会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吗?
如何看跨界作为未来的设计趋势?
W:
如果将新的生活方式定义为不确定的进行状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未来本身就是一种跨界。
事实上,之前以所谓的风格来界定的每一个建筑时期,都是对已有界限的某种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