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受害者心态”与“战狼式”爱国
——现代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世界政治观?
“道义化的高尚情感庇护的仇视,并不是保证中国国家利益、从别国争夺来利益的有效依据,而是让中国难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精神障碍。
中国必须学会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并以谈判、互利、妥协的理性方式,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仅代表作者观点
自晚清“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还,由西方人开创的现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就成为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大课题。对这个“世界”,中国处在后发现代、“被动挨打”的位置,为自己民族的现代不公遭遇感到极度的无奈、愤懑和悲悯,因此,对“世界”怀抱极深的敌意。
随着中国初步解决了发展问题,在经济总量上重回“世界”前列,国人迅即对介入甚至领导“世界”充满雄心,一种非中国莫属的、登顶“世界”之自满、自恋和自负,成为国人在“世界”各地乐于展示的精神状态和民族心理。

然而,这两种中国世界观均显乖张。
理性地融入“世界”,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并克尽自己的大国责任,恐怕才是中国需要着力塑造的现代世界观。
悲情中国的世界观
晚清中国,迅速从“天下”堕入“世界”。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建构的国际观念。
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向外扩展的古典世界观。
华夷之辨,是对之的观念奠基。五服制度,是对之的制度设计。朝贡体系,是对之的操作谋划。由这一古典世界观引导的中国古代的国际认知,自然是自信心十足,而对中国发挥的国际影响既不会陷入焦灼,也不会激越躁进。
尽管论者揭示了朝贡制度的国家设计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国际地位自认,与被中国认定的朝贡国家的承认之间并不吻合,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朝贡制度的践行。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古时制度自信。
当“天下”机制遭遇“世界”体系之后,中国便丧失了从容谋划国际事务的能力。
首先,这固然是因为“弱国无外交”,让中国很难就国际事务发挥“天下”时代的那种影响力。
其次,中国由于自身国力的急遽衰退,寻找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一艰难求存的任务,耗费了几乎全部的国家资源,因此,根本没有余力去关心和处置国际事务。
再次,中国的千年政治惯性,所熟悉的只是以我为中心的国际往来,不管远亲近邻、强国弱国,只要跟中国发生关系,中国总是以上对下的姿态处理;所陌生的则是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主动出击以应对全面强势外国对中国的挑战。一个由西方国家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激烈竞争性的世界秩序,完全为中国所不解,因此,也就很难将“天下”与“世界”无缝对接起来。
让中国最不适应的,并不是遭遇了一个与绵延千年的“天下”机制不同的“世界”替代体系。
“天下”与“世界”的生硬磨合方式,才是让中国最难应对的事情。当西方携硬实力和软实力强行打开中国关闭的大门时,中国完全无力抗拒:
硬实力,并不仅仅显示为现代工商社会产出的巨大财富实力,如果只是这种硬实力结构,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洋务运动那样的学习方式承接下来。关键是西方工商国家在拓展它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时,常常借助战争手段,让中国这些落后的农商国家情非所愿地洞开国门。
西方国家不断的战争胜利,不断地强加给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让“天朝上国”的颜面尽失。
以至于晚清时期,不得不借助自己长期千般设防、万般警惕的民间暴力,来抵抗西方国家力量对中国权力体系的侵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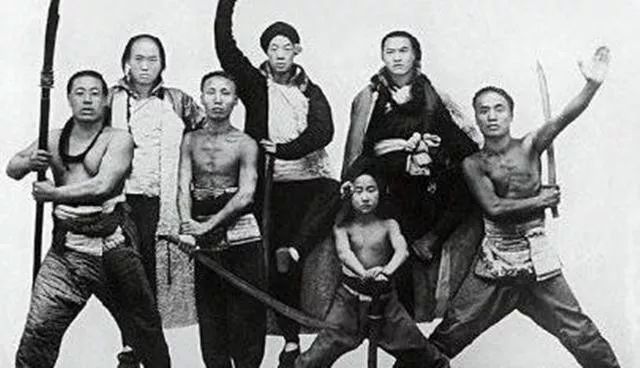
义和团口号:扶清灭洋,刀枪不入
无奈种种类似的伎俩,效用递减。终于因为内部的工商经济发展乏力、宪政改革失败,让内外部的重重难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天朝上国”面对“世界”的第一次崩盘,也因此不得不臣服于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
在被动卷入西方国家建构的现代“世界”过程中,中国陷入悲情主义的精神氛围,由此塑就被动挨打、指责侵略与爱好和平相互支撑的悲情主义历史观。“天下”体系从容运转时的国家软硬实力观,被抵抗西方侵略的道义世界观所替代。
在悲情笼罩的“被动挨打”历史观建构中,中国看待“世界”呈现出一种突兀的悖谬:
理智上中国完全认同西方国家代表的现代发展方向,并尽力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模式,但感情上坚决拒斥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源自晚明开始厉行的海禁政策,让中国人在封闭且被动挨打中逐渐固化了西方侵略者的强权角色、
中国受害者的悲情主体定位。发誓改变这一悲情角色,登顶“世界”巅峰
,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萦怀于心的国家意欲,
并直抵民族心灵世界的深处。

在悲情中确立的现代中国世界观,凸显了不是同情中国就是侵害中国的情绪性国际思维。一旦被中国认定是侵略者,不仅会被放置到审判的平台,遣用顶级的道义激愤辞藻加以痛诋,而且被视为中国不共戴天的仇敌。假如被认定是同情中国现代被动挨打遭遇,并承诺放弃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且愿意与中国结伴而行、共谋发展的,不仅让中国深怀感激,而且全情拥抱、视为挚友。
在这种受悲情支配形成的简单化国家思维中,人们很容易理解获得国家独立后何以还会出现“一面倒”的幼稚外交政策:
那是因为苏联曾经作出的友好表示,让悲情中的中国颇受安慰。
而欧美国家惯于以国家利益为名与中国打交道的举动,让中国人随时随地舔舐受其欺凌的伤痛遗痕。
因此
,一时友好与一世友好、短暂交恶与永久仇视的国家情绪化外交,
也就成为一种外交惯性。国家受面子心理的驱动,远比受利益盘算的影响为大。
受人欺凌,在实力上难以抗拒,自然就会诉诸道义的力量并将之视为抵抗侵略的精神依托。中国既然深陷在悲情中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因此,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爱好和平的国度,
把现代先行者看成是侵略成性的野蛮国家
。循此思路书写国家的历史,中国便将自己的历史书写成自古至今爱好和平、立于国际关系道义山巅的伟大国家,而把西方国家的历史书写成惯于侵略、习于战争的兽性国家史。
这样的书写,内里潜藏的历史哲学预设是,
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瑕疵;而侵略别国的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则没有托词地理应承受严厉谴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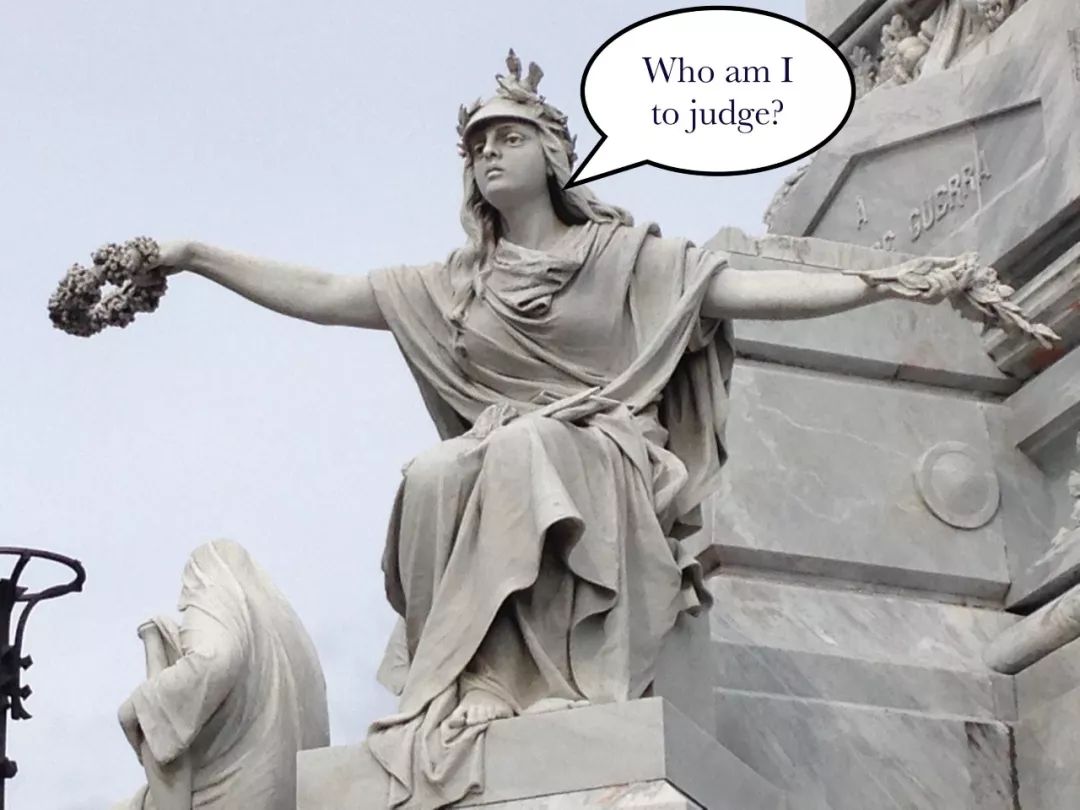
受此思维定式的影响,
中国在看待西方创制的“世界”时,总是习惯于以侵略与反侵略、道义与野蛮、和平与战争、情谊与利益的二元对立思路找寻种种问题的求解之道
,很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国家妥协中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至今国人习焉不察的、以“中西”对“古今”的表述定式,就
深藏一种中国与西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文化无意识。
在现代“世界”,中国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多么撼人心魄的悲情。“目前,世界秩序的中心不在中国;
世界秩序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学说完全不同;中国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很低
(至少到不久前为止)。”
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家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便中国的独立自主有了政权保障,但由于没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弱者的处境及其心理态势,也就没有结构上的改观。以悲情为方法审视世界的思维惯性也就延续下来,并沉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孤傲与国家主义冲动
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成长,让中国跻身GDP世界第二位。
这无疑是一项伟大成就。
这是晚清以来中国国家处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
但随之引发的国家心理变化,不是让中国回归现代国家之间理性共处的常态,而是跨越现代世界秩序,直接搭挂到古典“天下”秩序上,迅速重建起类似于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那种支配世界的当代世界秩序理念。
环顾
当今中国,孤傲的国家心理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弥漫开来。
这不是一种纯粹虚幻、自我陶醉的国家心理。相比于此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跻身GDP世界前列带给国人的自我认知变化,绝对只能以天翻地覆四个字来形容。这种对国家的世界地位采取的单一、物化认知标准,本身尽管有它的缺陷,但硬实力确实是支撑现代国家自我认知的现实基础。
随着国人对自己硬实力自信心的增强,曾经长期左右国人自我认知的、由自卑与自负混合而成的悲情,一扫而光。
不仅如此,GDP与强大国家的直接勾联,让国人的骄傲心与自豪感迅速上升,国家崛起的自认感让中国人领导世界的雄心陡然增强。
这种国家观念的塑造,除开GDP的数据鼓舞以外,主要源自三种基本动力:
第一,由权力自觉引导的“国家崛起”论说,给这种孤傲的国家观提供了权力动能
。“国家崛起”的论说,如果是一种诸国家竞相崛起的表述,自然没有什么令人惊怪的地方。但中国的崛起论说,基本上是一种霸权国家衰落、新兴中国崛起的一起一落、一胜一败的尖锐对立说辞。
由国家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电视政论片,很好地代表了
权力塑造崛起中国的社会政治心理变化
——它向国人刻画了九个大国遵循时间先后次序的崛起故事,不仅暗示人们,大国只能排斥性崛起,不能并立性飞跃,而且明示观众,当下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历史趋势、现实表现。

第二,西方国家一些人士提出的
“中国统治世界”言说
,给孤傲而尚乏自信的国人提供了自傲的间接动力。类似“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言说模式,大致建立在三个支撑点上:一是西方世界明显衰落;二是中国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增长;三是中国必然代替西方成为世界的新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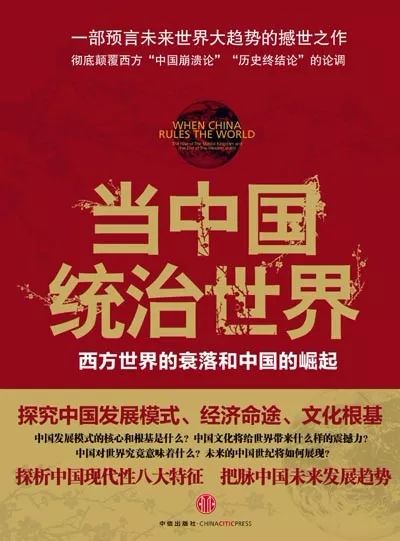
加之这种论说将西方限定为自利的民族国家,将中国确认为超越民族国家利益藩篱的文明型国家,因此,中国足以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的文明程度更高。
这类论说对一个百余年极为在意侵凌自己的西方强国对自己评价的国度来讲,自然具有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第三,崛起国家的处境给中国注入的孤傲精神动力,具有侵入国人内心深处的强大能量。
崛起中的国家,常常面临双重怨恨:一是发达国家在所谓守成与崛起的矛盾认知情况下展开的狙击;二是欠发展国家对崛起国家又恨又爱所表现出的对之必然的排斥。
崛起国家常常没有真诚的朋友,大致便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加之崛起国家本身很容易在国力的迅速增长中顾盼自怜、孤芳自赏,一种内心极为孤独的感觉与自大的自恋心态,让孤傲的国家主义理念,具有了侵入国人内心世界深处的强大能量。
当下中国人瞧不起老旧的欧洲、衰颓的美国、老化的日本,就此可以理解。
至于根本不将其他发展中和欠发展的国家放在眼里,那简直就是自近代以来一心只学西方强国的国度再正常不过的国家心态。
近期中国国家主义的盛行,与这种孤傲的国家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匮乏与错位,人们转而将自己的国家看得非常神圣,这完全合情合理——
比历史
,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
比国家韧性
,
中国多难兴邦,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形态;
比现实发展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引擎,经济增长率雄踞世界第一;
比未来
,中国代替西方国家领导世界的潜力已经展现出来。
孤傲的国家心理催生国家崇拜心态,
这是一种相倚的心理反应机制。但孤傲的国家一定无法融入真实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各个国家共生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独美其美,拒绝与其他国家美美与共,无论这个国家具有多么强大的国家崇拜心理资源,它既无法为其他国家所接纳,也无法准确认知自己国家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对中国而言,在近代历史上积累的悲情,与这种被迅速发展催生出来的孤傲相贯通,
很容易生出敌视世界各国、不惜与敢和中国争高下的强国或弱国断绝往来,甚至与所有被自己敌视的国家开战的畸形社会心理。
这种社会心态下诱发的政治理论观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劳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国家崇拜。转向传统思想资源,也就引导出中国的问题诉诸中国的传统可以完全彻底解决的封闭主义思路。
极而言之,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才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救星。“
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道出,政治上的当下义和团行径由此屡屡出现。
颠转行动:重写历史与推高现实
从沉重悲情跳跃到孤独傲慢,是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激变轨迹。之所以出现这种跳跃,是有其客观理据与主观意念的双重缘由的:从自认全面落后到中国经济总量的显著增大,不仅让国人对国家硬实力日益充满自信,也促使国人在孤傲心态下重建让人自豪的历史叙述与国际理念。
在国家崛起的自认状态中,受硬实力迅速增长的驱动,国人必然致力于增强软实力。
这样的尝试,势必引起中国国家理念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
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
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
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
“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
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
,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
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
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
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
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
,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
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
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
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二)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观,成为国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势
重构中国道义逻辑上自我肯定的传统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关论者表现出的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这样的思路中,中国人的国际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观。
在论者看来,当下世界是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完全缺乏道义基础。
一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现代重构奠基、体现出鲜明的道义言说特征的国际秩序设计,便具有了足以显示其正当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显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霸权模式”,成为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当下世界秩序高频次使用的词汇。
第二,致力国家道义取向的“新天下主义”建构。
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建设性的论说作为替代方案,否则,既定的“世界”秩序还会作用于国际社会。引人关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义”。
“新天下主义”
必须有强弱两个版本。
弱版本的天下主义是对“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天下主义的平等性修正产物,以适应平等国家的秩序建构之需;强版本的天下主义则以现代知识论证方式重审传统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强调中国传统那种内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属性,以及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独特意义。
其论说包含了两个内在关联的判断。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国”概念引导,将中国视为超国家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绝对道义化存在,
凸显一个绝对不征服别国、但所有国家心悦诚服的“旋涡模式”
;
另一方面,
由“天下”体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设想,将旨在建构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国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
那种足以超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成为论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