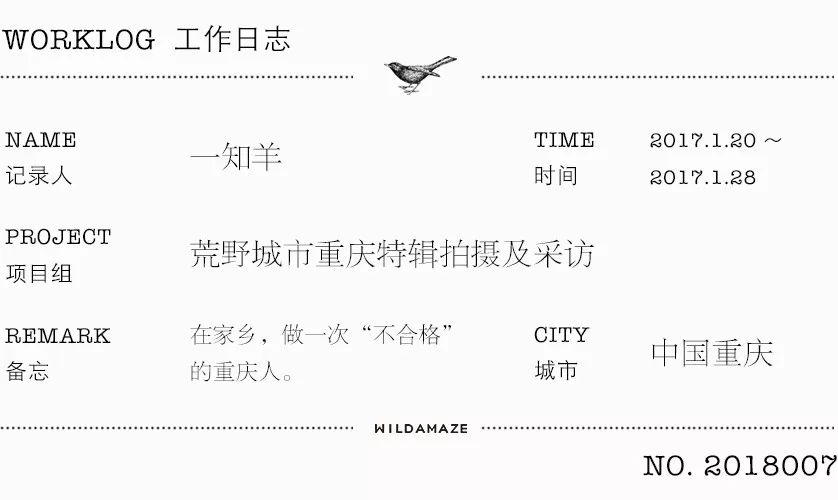
耿直、脾气火爆,掌握娴熟的麻将技艺,还拥有随时吃火锅和饱览一线江景的特权 —— 除此之外,重庆的年轻人与其他城市的并没有太大区别。
去年七月,一个朋友去观看了温顿·马萨利斯&林肯中心爵士乐团的演出。这场演出在北京和上海的反响特别好,演出的门票早早地售罄,而在重庆,取而代之的,剧院门口票贩拿着880元的门票叫卖着200元的价格。

可能这让我动了离开的念头 —— 而当我拉着一只齐腰的行李箱抵达“荒野气象台”时,随即被告知下一个城市项目将在重庆进行。
尽管我自诩是合格的重庆人
——
典型地离不开辣椒和花椒、分不清“
n
”和“
l
”,但同时也非常不典型地找不到路、认不准桥以及并不痴迷火锅。对这次出差充满不安的我,在离开北京前确认了三遍:长江是南岸区和渝中半岛中间那一条;嘉陵江在嘉华大桥下面,并且一直延伸到我最喜爱的牛角沱站和千厮门大桥。没别的,反复熟悉地图就是为了在地理常识上不给重庆人“脏班子”(丢范儿)。
然而最担心的情况在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拍摄对象的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我们的住处(国金中心)出发上经双碑大桥,比从鹅岭出发去大学城的“川美”要近一些。我的“重庆人”身份也首次遭到了同事刘老师的质疑。随后再次因为“我不知道哪里的火锅比较好吃”等突发事件,这个人设彻底崩塌了。我只好在之后几天,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是第一次到访重庆的高雄人,企图保家乡的颜面 —— 曾经在台湾念书的经历,倒让我的“台湾腔”更有说服力。
接下来几天的拜访,使我发觉丢掉当地人的包袱后,反而能找到合适的切入角度 —— 毕竟一切都是未知,我不必担心自己的推荐够不够地道,不用理会关于这座城市本身的信息是否准确,只用关心眼前的风景和人事是否足够迷人。这样一来,我意识到拍摄对象的视角对我来说反而是全新的。南岸区对我来说是一个地理上非常陌生的名词,拍摄对象带着我们穿进面临拆迁的巷子,沿着空无一人的店铺往前走,我望见了一座大桥骄傲地立在不远处。


虽然因为中学时期常在沙坪坝区补习数学的缘故,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很熟悉,可却从来没有走进过南开中学。跟着我们的拍摄对象之一进去,听他介绍的时候,我总是因为暗涌的腊梅花香而分心,看着教室涌出刚刚结束考试的学生,想起因为一篇来自微博知名博主的文章被语文老师拿来当阅读考题,并与学生平等讨论,甚至追问征询至原作者的桥段,让人觉得一所优质学校的教育该是这样开放的。此时天色已经变暗,看到堵在路上的老板发了一条微博,分享重庆出租车司机因为听到他在电话里说饿便给了他一个面包的插曲。
我们的拍摄对象之一,是当地文创园区里一家冰淇凌店的女主人推荐的。拍摄时遇上重庆的雨天,我们正好在附近,就去拜访了这家店。拍摄对象走进店里对女主人说一定要在门口铺一块垫子,不然一到这样的天气,店铺的地板很容易被踩脏。随后他又进一步建议加一圈纸包裹蛋卷,颜色会更好看,顾客拍照的时候应该会更开心吧。这样的互相关照让人觉得温暖。
另外,还尝到了“花椒味”的冰淇淋 —— 意外好吃。
在观音桥的一个商圈拍摄时,拍摄对象说他第一次下馆子就是在这里。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观影也是在这里,开心地抱着一桶彩色爆米花看“外星人”用光剑打架,还说着不明所以的语言。这样的经历在我看来像是一个隐喻,电影给我打开了一扇探究世界的门,也让我开始产生疑问,常常趋于“别处”的吸引力,是否因此忽视了身边的日常。

是这些细小的片段延展了我认知中的重庆拼图,并成为了其中格外闪耀的一部分。
我原以为重庆本地的年轻人想要的始终是离开这里,去探索更远的世界。可这次的拍摄让我逐渐感到,这片土地已经开始变得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美食和更舒适的生活氛围,还有这个城市本身不断涌现的无数可能。更多时候,他们离开是为了回来 —— 音乐、文学、艺术、美食,他们把从别处带回来的各种体验重新创造,融合进这座城市。我相信这些事情在逐渐地丰富本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像是我那第一次观影体验一样,为在重庆生活的年轻人提供了另一些不同的可能。
在工作中,很多人都问荒野城市的受众是谁?我们不是旅行宣传片,也不堆砌“到此一游”的信息,我们所提供的视角,是来自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 —— 有时甚至非常主观,以至于它会可能不是信息化的城市指南,也不是景点介绍。它所能做的不过是找出一条日常的路径,并发掘它对个体的意义罢了。当跟随生长于斯的男孩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轨迹,似乎我们也短暂地经历了一场那样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