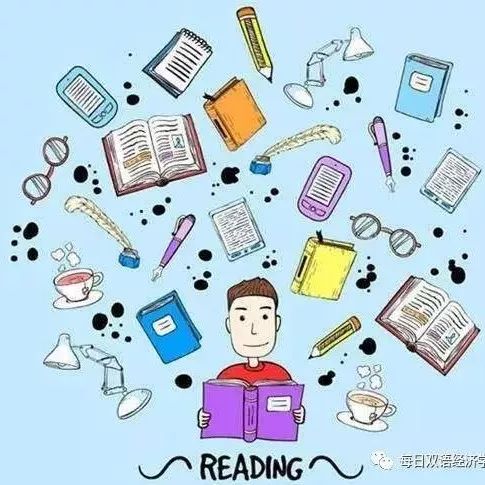一、秦穆公
在《礼运大同篇》中,孔子运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他所理解的上古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及当时的周代:“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因为此文流传于东周春秋时期,所以后一句的描述肯定不能瞎说。春秋的社会,大概确实是以天下为家,人事组织主要依赖于血缘。贵族的儿子天生就是统治者,平民的儿子天生就是被统治者。
至于此文的前一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然字面上说是上古时代,但其实阐述的是孔子的理想世界,并不见得真实存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实现管理权与受益权的分离。
所谓“选贤与能”,人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怎么选”上面。其实无论是让君主来选也好,还是让人民来选也好。它的目的无非就是把管理权交给别人,并且使得自己的收益增加。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人种其因,自食其果。这才是常理。受益权是管理权的天然衍生品。凭什么别人承担管理,而你享受收益呢?
为了突破这个常理,人类发明了“道义”或者说“契约”的概念来约束自身。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士”阶层。“士为知己者死”。“士”既要执行管理权,也要保证委托者的受益权。不仅“贤”,而且“忠”。从这个角度说,现代的信托责任人、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等等,也都属于“士”。
可是光说没有用。周代的诸侯们可不相信什么道义,也不怎么愿意用“士”。但是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生死存亡的危机日益临近。管理权如果不加以改革,受益权同样保不住。这才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改变想法,认真考虑“君”与“士”契约合作的问题。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诸侯之中最肯打破陈规的,是当时比较弱小的秦国。秦国的国君秦穆公,以用“士”闻名。他曾经把楚国一个叫“百里奚”的奴隶买回来,委任为上大夫。这在讲究贵族血统的周代,可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当然后来“百里奚”也不负使命,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件事情的过程还有点曲折。秦穆公特地假装成很随便的样子,命人拿五张羊皮去把“百里奚”给换回来。赎金还不能多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多了,楚国就会发现这个人价值不一般,就不会放行,说不定还要抢先重用,或者干脆杀死他。
这个典故说明,当时的诸侯其实都已经明白,“士”的作用很大,相当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观念,相比于“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诸侯之中最能用“士”的,还是要数秦国。这是因为秦国建国最晚,发展最快,贵族势力的发育最不充分,所以才最有容纳新生力量的空间。
秦穆公的后代秦孝公,曾经发布过一道著名的《求贤令》,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就是典型的招股契约了。商鞅本来是卫国的“士”,就是被这个契约吸引到了秦国。后来商鞅设计出了军功爵制,把整个贵族政治的根基都连锅端了。任何人,只要有战功,就可以封爵。明码标价,不附加任何条件。这又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创举。
秦孝公的后代秦始皇,发现有人利用秦国的用“士”机制,安插间谍祸害秦国。于是他下了一道《逐客令》,要求别国的“士”退出秦国。这时楚国的“士”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令》上书劝谏。《谏逐客令》开篇第一句说的就是秦穆公招募贤才的事情,提醒秦始皇勿忘契约。秦始皇看完之后幡然醒悟,立即收回成命。这一桩故事,更成了“君”与“士”之间互动的佳话。
秦始皇席卷天下的背后,是“君士契约”的胜利,是管理权与受益权的充分分离,更是“士”阶层的崛起。从此以后,如何选“士”,如何用“士”,就成了中国政治中的头等大事。
二、汉武帝
秦始皇虽然雄才大略,隔绝血缘,以天下为郡县,然而社会政治演进的过程却拒绝“快进”。所以汉代初年做了一次退步,实施同姓分封。后来才有了汉武帝削藩之事。但是直到汉末三国时期,还有刘表、刘璋这样的“汉室宗亲”割据一方。可见有汉一代,政治制度受到分封制的影响始终很大。
汉代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组织结构上非常相似。中央有皇帝,地方有太守。中央有丞相,地方有州丞。中央有户、法、兵等曹,地方也有完全对应的各个部门。每一个地方政府,几乎都是一个缩小版本的中央政府。
汉代奉行“无为而治”,各个地方高度自治。从汉高祖到汉景帝之间的
60
多年,从皇帝下达到郡县一级的诏书,不过数十份而已。因此每一个郡,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们与先秦诸侯国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中央政府有权掌握州牧、太守和县令的任命。中央只管行政一把手。这些一把手则可以自行“组阁”搭班子,甚至有权决定附属官员的生杀予夺。这就是辟署制。
在这样一种高度分权的制度下,汉代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理的官员,不到全国官员总数的
10%
。绝大多数的官员,只知有太守,不知有中央,更不知有皇帝。反过来说,中央也不知道他们。政令大都出自地方,执行也在地方,效果好坏,水平高低,中央完全无法品评。
这样就造成一个大问题:官员的晋升机制被隔断了。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内部晋升都必须是最主要的人才来源。一方面,实际业绩的说服力是任何选拔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保持晋升通道畅通也是组织激励机制的核心内容。
为了给予官僚组织适当的流动性,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不断下诏要求各地举荐人才。到汉武帝时,察举制正式建立。各郡根据人口多少,每年固定向中央推荐
1
到
3
人不等。每年全国大约不到百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察举制的目的性很强,对人才的年龄和资历都有具体要求。如果符合要求则通常不会被拒绝。而且察举成功之后,授予的官职一般都是县令之类的地方实权。所以察举制对汉代政治还是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根据汉代的分权制度,皇帝与太守之间,太守与“士”之间,都是典型的“君士契约”关系。但是在皇帝与“士”之间,则完全不存在这种契约。如果有契约,那就好办,论功行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没有契约,皇帝也没有理由因为官员扶佐太守有功而奖励他。那么
在实行察举时,
选拔标准怎么设立?汉武帝规定,以通晓《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标准。
几乎与汉武帝同一时代,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曾经做过类似思考。他反对各种政治交易,也反对民主选举,认为这些措施都无法避免愚蠢。所以他在《理想国》中提出,应当以哲学家为王,管理众生。在“从贤”而不“从众”这一点上,柏氏与汉武帝略同,但是他没有提出哲学家的具体标准,而汉武帝提出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标准被提出来都免不了惹上千古褒贬。这里我们姑且存而不议。
在今天的西方政治中,各种契约和交易是所有事情的逻辑起点。在竞选的过程中,政客会对选民做出若干条具体承诺。在当选之前,竞选团队内部必须商量好当选之后的岗位分配。在当选之后,党派之间还要就席位和法案进行纵横捭阖。如此循环不息。
但是在汉代的中国,人民经过了春秋战国的千年战乱,对大统一政府的合法性是自动默认的。所以皇帝只需要根据“君士契约”,对开国功臣做一次性的权力分配。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新老更替出来的权力,都是自然归属于皇帝的,皇帝不需要为此奖赏任何人。换言之,这是中国特有的“统一”红利。
更深刻的区别在于,传统西方政治理论假设人对权力的欲望是无穷的。但是这个假设
显然
不适用于中国皇帝。中国皇帝的权力远远超过了欧洲的领主、国王以及教皇。边际上的权力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效用了,所以他们很愿意拿出一部分权力来追求纯粹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一种“凭读书写作来分配权力”的制度,会在中国实行
2000
年之久。
三、曹操
秦穆公任用百里奚,安排的是上等高官。秦孝公任用商鞅,更是直接给他当了丞相。汉武帝推行察举制,也是为了提拔县一级的行政长官。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在三国时代更是登峰造极。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可谓众所周知。虽然其中有许多小说杜撰的成份,但是诸葛亮承蒙知遇之恩,被迅速提拔,位极人臣,这倒也是事实。另一位英雄,曹操,则发布过一道震烁古今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在这道政令中,他竟然明确要求各地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用语坦白,毫无忌惮,堪称空前绝后。
曹操为什么要做此惊人之语?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本人性格豪放,有话直说。其次,此令发布于
217
年,当时赤壁之战已经过去
9
年。三分天下的格局大致确定。既仁且孝,还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基本上已经被瓜分完毕。但是战争压力仍在,所以德、才两条标准里必须放弃一条。那么他宁可放弃道德要求,也要强调实用主义。
如果再追究一层,那么就会发现“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其实是曹操的一贯风格。贾诩、许攸等文官,曹洪、于禁等武将,都在道德方面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仍然大胆委任,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因此,上述命令的说法,其实只是这种风格的自然流露罢了。
那么这道命令的效果如何呢?查阅史籍,似乎曹操无甚收获。三年之后,
220
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在当年就发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制度。在全国各地设置“中正”官,给人才评级,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称为“九品中正制”。
仅从形式上看,量化考评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人才数量太多,考评的范围如何划定?还是得由各地推荐出一个备选库来。所以九品中正制只能与察举制配合使用。更核心的问题是,考评的标准是什么?曹丕规定了两条,首先是家世,其次是行状。也就是说,家庭出身第一,个人品行第二。
前后三年,曹氏父子的两条政令,似乎完全背道而驰。其实也不尽然。曹操是才能第一,道德第二。曹丕是出身第一,道德第二。总之,道德都是第二位的。两者的异同,关键在于才能与出身的相关性上。
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是细究起来,他所用之人大多还是士族出身。荀彧、夏侯惇出身京城名门,郭嘉、曹仁来自地方豪族。真正农民、商贩出身的没有几个。换句话说,无论是文是武,都得读了书才有战斗力。而在当时,活字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读书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非士族豪门是不可能供养得起的。
三国时代的战争,早已不像春秋时代那样古朴。胜利不可能再像曹恺论战“一鼓作气”那样轻易。失败也不可能再像宋襄公“渡半而击”那样滑稽。当年孙武百战不殆,史称兵圣。他的知识哪里来的呢?
8
代军事世家积累下来的。随着《孙子兵法》流传于世,这些的知识便与天下士族共享了。反过来说,寒门子弟如果不能继承这些知识宝藏,全凭自己从头摸索,想要有所成就实在难于登天。
曹丕之所以实行“九品中正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拉拢名门望族,为自己篡位做准备。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社会的现实,治国用兵之术已经高度专业化,而且这些专业知识又被士族所垄断。那么这样的妥协又是可以理解的。曹氏父子二人的用人之术,差别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大。
当然,曹丕的内心对这样的妥协未必服气。假如给他一个汉武帝那样的大统一王朝作为平台,他是否还会允许这些士族做大呢?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从汉末到隋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将近
400
年的国家分裂,战乱连绵,人口损失超过
70%
。
不过曹丕的教训并没有被忘记。从隋唐开始,军事力量就被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唐有节度使,宋有枢密院,明有都督府,清有军机处。这些机构全都直属皇帝,不属宰相。“君士契约”的内容等于是做了一次大改。后世的权臣名相,即使如王安石、张居正,也不能染指军权。隋唐之后,像管仲、田单、诸葛亮、司马懿那样出将入相,军政大权一手抓的人物,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正是在这样文武分流的大背景下,行政官员的才能攀比愈发倾向于“诗书文章”。到了这个时候,科举制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四、唐太宗
两汉吏治,历代称美。它的好处在于委任。中央无为而治,地方灵活机动。但是要比逻辑清晰,结构严密,那还得数唐代制度。《汉书》中的汉代官制,只是记录官员的官职名称,机构本身并没有地位。比如光禄勋,这是一个官名,他管什么事我们知道。但是他所属机构叫什么,就不知道了。《唐书》则是先列出机构名称,比如某省某寺,然后才是官员官职。这意味着任何行政上的权力义务,都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机构法人。官员只是因为在机构中供职,所以代为行使而已。
如果考查唐代文物中的公文和抄件,很容易发现主办官员的头衔和署名,以及一连串的副署官员。而在汉代公文中,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唐代还有著名的三司制度,规定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联合审理。这在汉代更是不可能的。以上事实都说明,唐代官员必须首先服从于一套既定的规则,而不是仅仅是解决问题。事在制度,而不在人。换言之,唐代政治已经有了相当的“法治”成份。
唐代政治“法治化”的基础,是辟署制的萎缩。在汉代,地方长官可以自行任免下属官员。但是在唐代,九品之内所有官员的委任,都必须出自中央。这样一来,所有官员的工作,也都必须直接向中央负责。
全国官员的考评任免,全都归入吏部,这可是一桩难事。为此唐代的制度设计者们没少费功夫。但是有一个问题却怎么设计也无法回避。那就是唐代国土辽阔,机构庞大,层级自然很多,人才辗转晋级的速度就变得很慢。如果要为中央政府选拔年富力强的干将,就必须得在吏部体制之外,另辟一条快车道才行。
汉代的察举制,在隋代便已恢复。后来又逐渐淡化其它推荐理由,强化考试要求,把选拔标准统一到以“五经”为核心的考试上面。唐太宗时期,这一制度被正式确立为吏部官员选拔的补充措施,称为科举制。
唐代的科举,与其说是像高考,不如说是像
CPA
、
CFA
这样的资格考试。许多已经有相当品级的官员,也去参加科举。而且考完了明经科,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了古代经典。还要再考进士科,证明自己的诗赋文采。有了这些资格,再去参加吏部官员的选拔,就会被另眼相看,很容易飞黄腾达。唐代一半以上的宰相都是进士出身,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完全是平民,当然也可以参加科举。但是即使进士及第了,也只能得一个
8
品或者
9
品的小官,而且经常还是驻京无实权的。相比之下,汉代察举制任命一个县令,至少也相当于唐代的
7
品官员,还掌权。当然,即使只是
9
品,也足够吸引一大批学子趋之若鹜了。
唐代的科举,还保留着许多察举的特征。比如说行卷和通榜制度。所谓行卷,就是把自己的诗书文章送给达官贵人阅读,博得他们的推荐。所谓通榜,就是在评卷甚至考试之前,就开始讨论榜单名次,保证社会声誉卓著的人物直接入选。
从原理上说,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是有道理的。现代最发达的美国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而且文学作品的质量不易比较,一考定终身也确实不尽合理。但是唐代科举也有一些奇事。比如说诗圣杜甫,居然行卷多年都没有获得推荐。再比如写出《阿房宫赋》的杜牧,在通榜时竟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