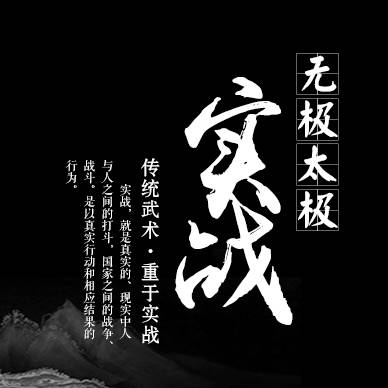那么怎么去理解生活得“更像人”呢?人是理性的动物,“更像人”就是更适合我们的“理性”和“物性”。“以人为本”是以适合人的理性与物性为基本原则,而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通过适合人理性与物性的聚居模式去提升空间上的接触机会,以满足人的理性与物性需求。
十三世纪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对自然之法的研究中指出:万物求存,万物都是按它的本质而存在;动物求存,求延续;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人当然也要求存、求延续,并且求共存。
人的理性是自然之法
,自然之法是不能改变的,顺天者兴,逆天者亡。就像因为地心引力的存在,如果一个人从12楼跳下去,很大概率会被摔死,这是自然定律,人的选择只在于跳还是不跳。
同理,
自存与共存的平衡也是自然之法
,这是不能改变的,面对自然之法,人的选择是遵循它来做事还是违背它。自存指的是按照自己的本质生存,共存则是指别人按照他的本质和我一起生存。人与人之间是有自存和共存平衡的。
举一个例子,一位爸爸和孩子,两个人自存又共存。爸爸是爸爸,不是孩子的仆人或朋友,他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个角色来与其共存,爱他不能与爱别人的孩子一样。相对而言,孩子作为孩子自存,他把爸爸作为爸爸来共存。因此,懂得与孩子共存的爸爸应该是把孩子需要的东西给他,而不是给孩子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假如爸爸不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孩子要什么他都买给他,这么一来,爸爸和孩子的关系就变成了主人和宠物的关系。当有一天,爸爸决定不再给孩子买东西了,孩子就会马上翻脸,因为父子自存与共存的平衡被破坏了。
那怎样才是最好的平衡呢?
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而自存则是共存的最佳标准。
因为如果大家共存的话,自存的空间和机会就大了。那么,应当如何与人共存呢?我觉得,你怎么样自存,就应该怎么样与人共存,简单来说,就是要懂得换位思考。
例如做城市规划,可以要求开发商在提方案时要提出:“假如你是周边的居民,你对噪音、尘埃、交通拥塞等的承受力是多少”,让别人知道你开发的底线。老百姓要是反对开发,也要提出: “你如果是土地开发者,你认为最小的开发强度是多少”。开发商可以说无限,反对者可以说0。但如果这样,他们的公信度自然就低了,博弈的力度就差了。
那么,
研究城市最好的指标应该怎样做呢?
比如,小学校区的半径为多大最合适。典型的调查是去问家长: “你认为孩子步行上学多远的距离是‘最理想’的?”也许多数家长会说,最好为0公里。同样,假如你问校方“理想”的校区半径是多少。它可能会说越大越好,因为半径越大,学生来源越大。他们的回答都是从自存的角度出发。
但如果你问家长:“如果考虑自己的孩子、其他家长的孩子也要上学,你认为‘合理’的距离是多远呢?”他们也许会说,四分之一到半公里。同样,问校方:“如果你考虑到校方的需要与家长和孩子的需要,你认为‘合理’的距离应该是多远?”他们也许会回答,半公里到四分之三公里。
这里的合理绝不是理想的值,半公里就是这两类答案中“合理”距离交叉的值,可以达到最大的共识,这比0公里和1公里的博弈更有意义。
由此可见,假如把门打开,人自然会考虑自存与共存的平衡。
人其实有一种天然的利他倾向。
假如你站在河边,河中间有个人在挣扎,眼看马上要淹死了,此时,你身边有个人跳下水游泳去救他,你会觉得对方很了不起。那为什么你会认为他奋不顾身地救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呢?因为在危难时刻,救人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共鸣。共鸣是因为心中的东西与看见的东西一致了。
所以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我们不仅仅是自私的动物,而是自存与共存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