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起,手指痒,胃口开,吃蟹来。
只怕现在没有哪一只螃蟹可以逃出
广东人
中国人的掌心。

你你你不要过来
入秋后的螃蟹膏黄肉壮,哪怕是饕餮附身的吃货,面对这只硬壳生物时,都会小心翼翼举止斯文:
轻轻打开微烫的蟹斗,将蟹身一折为二,左一口右一口,吮吸着金灿灿油汪汪的蟹黄,再细细剥出蟹肉,折下蟹腿,与带着姜丝的醋拌在一起,放入口中的是满嘴鲜香。
最后一杯温黄酒下肚,正如诗中所云:
“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

现在人人都知道螃蟹味美,平日也会买上几只蟹来解馋。
但螃蟹生来长相凶狠,性格霸道,连鲁迅都忍不住说:
“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
蔡澜更是大呼,
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颁发诺贝尔奖
,感谢他发现了天下如此美味的食物。
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大禹手下的
治水督工巴解
。
相传大禹来到江南治水时,遇到夹人虫的侵袭,巴解想出用沸水抵抗夹人虫,没想到烫死后的夹人虫散发出整整香气,巴解大胆咬了一口肉后发现,我去!
这也太好吃了吧!
于是可怕的夹人虫就变成了古人餐桌上的一道菜。
但这毕竟只是传说,最早记录螃蟹菜肴的典籍是
先秦古籍《周礼.天官.庖人》
:
“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
凡其死生鲜薨之物以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东汉郑玄作注:
“ 荐羞之物谓四时所膳食,若荆州之鱼,青州之蟹胥。
”
”蟹胥“就是蟹酱。
换句大白话:
先秦时期,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吃上蟹制品啦~

对对,就是我
也许有人不喜欢吃牛羊肉,却鲜有人不爱吃螃蟹。
应季肥美的螃蟹,煮熟后带着一股复杂的香味,蟹肉丝丝缕缕肥厚清甜,蟹腿中藏满了如同干贝一般紧实的肉,母蟹厚厚的蟹膏,公蟹糯糯的蟹黄。
这时候筷子已经变成了累赘,手才是吃蟹最好的工具。
待啃完一只蟹后,低头吮吸着手指,意犹未尽。


“蟹仙”李渔曾对螃蟹大肆赞美:
“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
”
,他不仅描写了自己对蟹的痴情,还总结出自己的
一套吃蟹理论
:
“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而食。
”
袁枚在《随园食单》也说:“
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
最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
蒸者味虽全,而失之太淡。
”


世界上的螃蟹无数,
划入天朝国民食谱的就有600多种
。
因生长地理位置不同,同是十只脚的生物被分为三六九等:
一等一的高手是湖蟹,如阳澄湖、洪泽湖,二等选手是江蟹,如九江、芜湖,三等是河蟹,之后便是溪蟹,沟蟹与海蟹。

但好吃的国人却并不完全遵守这条鄙视链,什么样的蟹好吃,从南到北各地人心里清楚得很:
北海的沙蟹汁
是广西人心里的老干妈;
黄油蟹
的油膏多,港粤一带最爱它的原汁原味;
肉质鲜顶角膏足的
芷寮蟹
让广东人百吃不厌;
潮汕赤蟹
逃得过生腌,却逃不过大排档里的煎炒焗蒸炸;
鱼羊鲜都无法企及
宁波咸呛蟹
的鲜美;
一到秋天江苏众湖泊里的
大闸蟹
,齐齐下锅,只只都是美味;
紫蟹火锅在天津人心里的地位堪比煎饼果子;
至于
梭子蟹
的做法,辽宁人可以写出一本菜谱来……
早有美食家说过,潮汕是中国美食界的孤岛。
这里一碗白粥都能配出百种咸菜,最好吃的蟹当然要从这里开始讲。

潮汕地区海岸线曲折绵长,多优良港湾,海产异常丰富,潮菜也以烹饪海鲜见长,其中生腌是最大程度保留食物鲜味的做法,
有“毒药”之美誉
,指吃过的人都会
爱上那个味道无法自拔,犹如中毒
。

就让我以身试毒吧
潮州生腌蟹
深得宋朝人的真传,宋人高似孙在所著《蟹略》中就有介绍宋朝名菜
“洗手蟹”
的做法:
“今人以蟹,沃之盐、酒,和以姜、橙,是“蟹生”,亦曰'洗手蟹'"。
意思是,
您洗个手就能吃……
王初寮吃过便诗曰:
“熟点醯姜洗手生,樽前此物正施行。
哺糟晚出尤无赖,尚有馋夫染指争。”
乾隆在《潮州府志》还diss这种吃法:
“所食大半取于海族,故蚝生、鱼生、虾生之类,辄为至味。
然烹鱼不去血,食蛙兼啖皮……尚承蛮徼遗俗。”
大猪蹄子你不懂了吧,这样才能吃到蟹本味!

你说什么?
潮汕人常用蒜头、辣椒、芫荽、白酒、酱油、香油、味精等佐料来腌渍,将食材本味发挥到极致,"毒药" 只需一口,
舌尖上鲜嫩软滑的蟹肉自动滑入喉咙,又咸又鲜的蟹膏刺激着味蕾
,
让你即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海风。
从此,除却巫山不是云,若是此时配上一碗香软的白饭,那即是人间至味。

但
这种吃法
只限于
海里生长的梭子蟹
。
对于那些生长于淡水或咸淡水之间的蟹类,比如瘪蟹
(拔蟹)
、蟛蜞、毛蟹和青蟹,因其生长环境难免污糟,倒也不敢放胆生吃。
从潮汕杀开一条生腌血路的膏蟹来到福建宁德后,荣幸地变成了当地的又一道的美味:
飘香红鲟饭
。

用来蒸糯米饭的红鲟一定要来自淡水与盐水交接处。
这里的红鲟肉质最为鲜美,颇为名贵,曾被列为贡品。
雌蟹体内挤满蟹卵,红膏顶角就是最好的,昔日产妇坐月子首选红鲟补身子。
在宁德当地最有名的就是秋天贵歧和漳湾产的红鲟,一般一斤二两左右,膏多肉肥,自是糯米饭的天然搭档。

营养这么丰富的蟹岂能随随便便怠慢呢?
当然要“好酒好肉”地伺候好它~
红鲟生性凶猛,
有经验的师傅在处理时会先用针管抽点红酒,
注入红鲟口中让其喝醉。
在等待时,将火腿,鸭肉,猪肚,鸭胗,虾米,香菇,竹笋,花生米用葱油爆炒,与糯米饭调和上锅预蒸,然后将喝醉的红鲟清洗干净,去掉鲟腮和鲟脐,切块后摆在糯米上,用荷叶包上葱头蒸制10分钟才能上桌。


经过大量煸炒的辅料带出红鲟的肉香,荷叶又吸附了多余的油脂,吃上去丝毫不腻,只觉得阵阵清香,满口鲜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
若消化不好,糯米则能被替换成粉丝,一样能鲜活你的胃。

来到了江南,湖蟹终于隆重登场。
九雌十雄,说的正是
阳澄湖大闸蟹
。
阳澄湖水质清淳,水浅底硬,水草丰茂,出产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十肢矫健,据说放在倾斜的玻璃上还能八足挺立,双螯腾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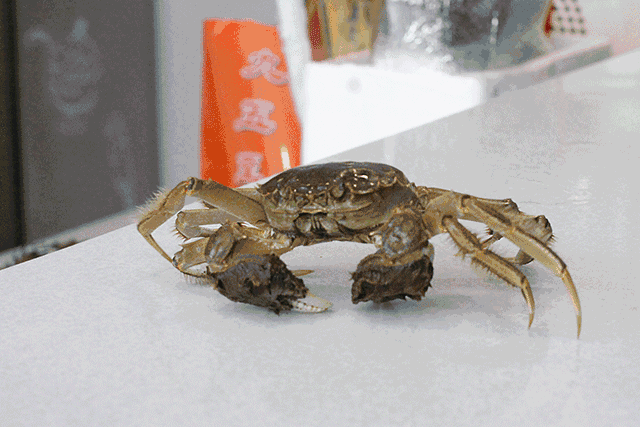
这么好体力的蟹,味道自然不差。
好的大闸蟹只需清蒸即可。
水里放两块姜,一勺料酒,十来分钟就能蒸熟。

金黄的蟹膏将蟹壳顶爆,轻轻一掰,膏体油润诱人,肉质雪白,紧实细腻,入口有微微甜味,香味浓郁。
这种浓郁的香味让蔡澜在日本时念念不忘,虽有体大味甜的日本蟹吃,但论起味道来,大闸蟹是一流。
甚至手上那股三天都洗不去的蟹腥味也是好吃的证明。

大闸蟹每年入冬时便拖着两只毛茸茸的钳子,游至长江口附近,在咸淡水交接的水域繁衍后代。
所产的蟹苗会被渔民们捕捞上岛,蟹农们将小蟹养到纽扣大时,再由全国各地的养殖户前来购买,带回去养大。

放放放……开我
包笑天的《大闸蟹史考》中就有关于“大闸蟹”名称的解释:
“闸字不错,凡捕蟹者,他们在港湾间,必设一闸,以竹编成。
夜来隔闸,置一灯火,蟹见火光,即爬上竹闸,即在闸上一一捕之,甚为便捷,之是闸蟹之名所由来了。”
竹闸就是竹簖,簖上捕捉到的蟹被称为闸蟹,个头大的就称为大闸蟹。
民国吃货团
里
最爱吃大闸蟹
的是
鲁迅
,秋风一起,他就琢磨着吃:
大的隔水清蒸,蘸点调料吃;
小的沾上面粉,做成面拖蟹或油酱蟹,安排得井井有条。
光自己吃还不够,还常常买“阳澄湖大闸蟹”送给他的日本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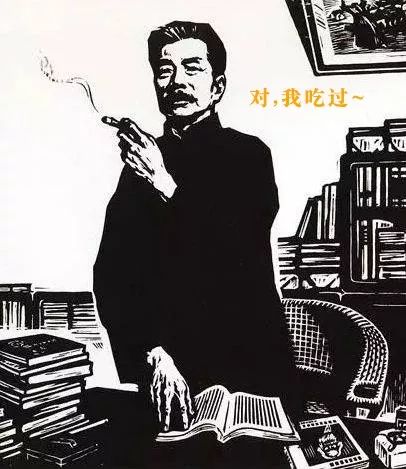
梁实秋
说起吃蟹就来劲,“七尖八团,七月里吃尖脐
(雄)
,八月里吃团脐
(雌)
,那是蟹正肥的季节……每逢到了这个季节,家里总要大吃几顿,每人两只,一尖一团。
照例通知长发送五斤花雕全家饮,有蟹无酒,那是大煞风景的事。
”

两只?怕不够您老人家吃的吧
林语堂
在《京华烟云》中描写“姚府蟹宴庆中秋”,吃的也是大闸蟹:
“全家人人都喜爱的一餐,没有胜过一桌螃蟹席的了……但是另有一种令人兴奋的理由就是吃螃蟹不同于吃别的饭那样由仆人伺候,由仆人端送,而是每个人都得自己忙,自己动……这种饭吃完,总是狼藉不堪,蟹壳儿蟹腿在桌子中间堆得高高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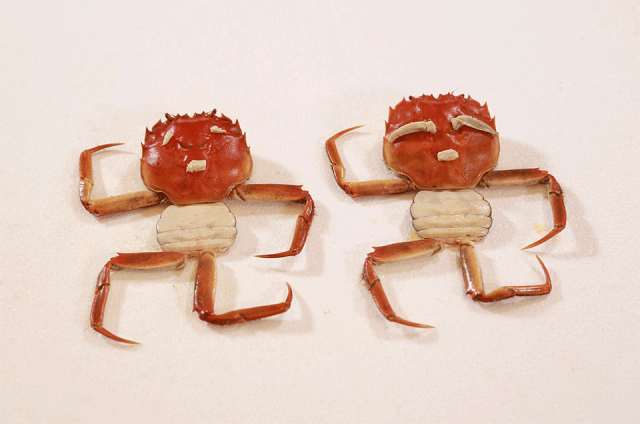
吃大闸蟹,谁的面前没一堆蟹壳呢
虽说江浙一带均有醉蟹,但论起年纪来江苏兴化的
中庄醉蟹
资格最老。

宁波咸呛蟹:我不服
明洪武二年
(1369)
,原本从事花木生意的童氏家族发现中堡庄前湖及周围河流出产的青壳大蟹十分肥美,于是开始做起了买卖鲜活螃蟹的生意。
为使卖剩的螃蟹延长保质期,就用
自制糯米浆酒制作醉螃蟹
,不小心变成了网红。
1915年,童氏家族的中庄醉蟹与贵州省的“茅台”酒一同拿到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食品类的金奖,名声大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