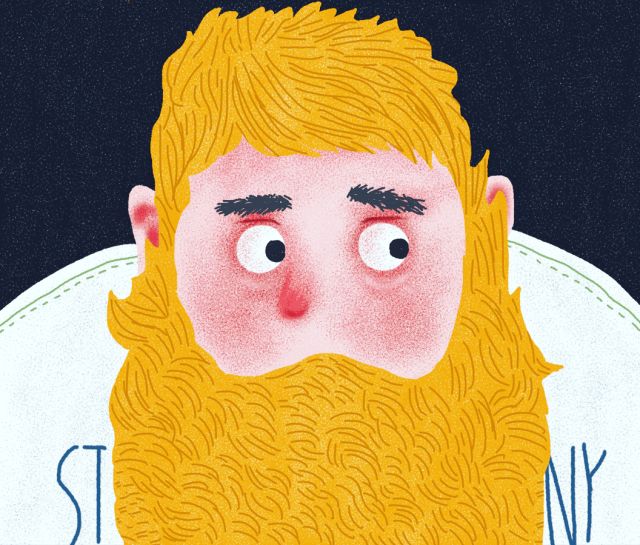编者按:
弗洛姆在他的《存在的艺术》里曾经提出过两个问题:“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放在《飘》里面就是
卫希礼的问题,“为什么而战?”。这是生活每个时代的人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拒绝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也会迷茫、孤独,甚至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但每个人终究需要走出自己的“乌托邦”,面对现实。因此
我们需要现实的品格,需要去思索属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光芒、典范和理想,因为我们只能走进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可能傲立于世界之外。
“为什么而战?……州权、棉花、黑奴和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去痛恨的北方佬。可我知道,这当中哪一个都不是我来打仗的原因。我反而好像看到了十二棵橡树,记起了月光是怎样斜照过白色的柱子的,还有在月光下怒放的木兰花那超凡脱俗的样子……我看到了妈妈在那做针线,还同我是个小男孩时一样。我还听到了黑人傍晚从田地里日落归来的声响。他们虽已筋疲力尽,却还唱着歌,准备吃晚饭。……我在为逝去的岁月而战,我太喜欢那逝去的岁月了,但是,我担心,不管死亡以何种方式关顾我,那种日子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无论赢还是输,我们同样地都已经输了。”
这是《飘》中我格外喜欢的一段话,所以不惜篇幅援引至此。是卫希礼写给媚兰的信,他质疑战争、怀念往昔安宁的日子。他用充满柔情的笔调描写了往昔在十二棵橡树的日子,月光下的木兰花、贤淑的母亲、日落归来的黑人的歌声……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段话,大抵也是由于这段话所描述的那种充满诗意、安详宁静的日子,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安宁、优雅。

(图源:pixabay)
然而这样诗意的日子终究一去不复返了。对卫希礼来说,无论战争输赢,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这样的日子就已经远去了。这是一种与农业文明、与美国南方传统相关的生活方式,从南北战争打响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将只是感伤地珍藏在那一代人的心中
。
“为什么而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有许多种别的问法,
诸如:“为什么而奋斗”“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什么要向前追逐”等等。人都是处在社会中,从小便被教育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好的。然而我们许多人决不像希礼那样,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于希礼而言参战并不是为了赢得州权、棉花的高价、黑奴或是一种爱国主义,这些都不是他所珍视的,他所无比珍视的是南方传统的那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那样的生活方式里有他所珍视的诗意、高雅、从容。我们更多人是去追逐我们被教育应该追逐的事物,做我们被教育应该做的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是在追逐着、奔跑着。然而,除却这种蒙昧,同样令人感伤的,是如卫希礼这样知道自己珍视什么但亦无能为力。
《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李美华 译
2000年9月版
(图源:豆瓣网)
这里影射出的是时代的变革,是两个世界交替时的分歧、沟壑。对于卫希礼们,美国南北战争打响,曾经安宁优雅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无论战争输赢,世界都将变成新的模样。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被赏识的是勤于经营、竞争、实用、精明利己,而希礼、媚兰所珍视的诗歌、音乐等文学艺术则是无用,他们所象征的那种从容优雅不会为他们赢得什么,除却从容、优雅本身。自从工业化的号角吹响、自从现代化的征程开启,那种从前慢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欣赏的不是从前那种诗意,这个世界需要更强、更快、更快。这个世界有不同于以往的野心和抱负。
其实,从前的日子未必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只是两个时代的确气质不同,欣赏的品格也已变化。往昔的日子在记忆中只留下了美好、诗意的印记,留下了属于那个世界、那个时代的文雅,而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新的时代,把更多现实的、甚至丑陋但真实的东西更多地也展示给人看,这个世界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格典范,这种典范会是怎样呢?

(图源:豆瓣网)
这种典范身上一定有明晰的现实品格。思嘉是这种典范的一个不完善的象征。
说她是这个时代的典范的象征,是因为在她身上深深烙下印记的果敢、勇气、魄力、精明,而这些都是为这个新的时代所赏识的,说她是不完善的象征,是因为典范意味着理想,而这个新的时代本身就还处于莽撞、探索之中,思嘉身上的现实品格是否值得肯定、哪些因素值得肯定、在什么情境下值得肯定也仍需要考量。无疑,希礼是属于曾经的世界的、是旧时代的人,而思嘉属于这个新的时代,她的莽撞、决绝、果敢、精明。当希礼向她提及往昔的日子,问道“你还记得吗”,在她的心里响起的声音是:“别往后看!别往后看!”
在思嘉身上有面对现实的果敢与决绝,这无疑是生活在这个飞速运转的新时代的人们所需要拥有的品格。当挨饿受冻、不得不亲自去田间地头找吃的时,思嘉发誓再也不要挨饿,再也不要让自己和家人挨饿,哪怕要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在根据小说改编的《乱世佳人》电影中,更是用了磅礴的乐曲来渲染思嘉的这种决心,思嘉高举拳头毅然站立在火红的暮色中,显得非常铿锵有力、振奋人心。显然,电影中对思嘉身上这种现实品格的肯定和赞扬要多过小说。
小说中有一个精彩的比喻论及现实、生存,那是方丹老太太对思嘉说:
“暴风雨到来的时候,它可以把成熟的麦子刮倒,因为麦子是干的,不能顺着风弯曲。可是,成熟的荞麦里面有汁液,可以弯曲。暴风雨一过,它又会挺起身来,几乎就像过去一样挺直,一样强健。……有麻烦的时候,我们连争也不争便向不可避免的事低头,而且继续干活,微笑着的等待时机。我们和较弱小的人合作,从他们那获得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而当我们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脚把那些我们踏着他们的肩部爬上来的人踢开。我的孩子,这就是生存的秘密。”
并不是从前的日子就没有这种竞争、压制、精明利己的一面,也许这原本就是人生存的法则,但这是自然的法则。而人给自己立法,立的是道德法则,是行为合乎道德律。这种精明利己在过去的日子里也存在,只是是作为暗地里、上不了台面的背后力量存在着,在一个飞速发展、注重现实目的的新时代呢?这种“生存的秘密”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了呢?生存是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问题,但人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在这个新的时代,人是不是可以丢掉一些东西却无损于道德、无损于人的尊严?
在思嘉不择手段地牟利的时候,她想着等到自己富有了再去做一个真正的贵夫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像她母亲艾伦那样,而现在她管不了这些。然而正如瑞德所道出的:
“你能做个正经人——可你也不会去做了。要救被扔掉的货物是很困难的,即时收回来了,通常也都被损害得无法复原了。我担心,当你有条件去捞回你从船上扔掉的荣誉、道德和善良时,你会发现它们都已经因泡在海里而变形了,恐怕已经不是什么贵重和稀奇的东西了……”
不可能先不择手段达成目的,达成目的之后再去追求荣誉、道德、文明,当人不择手段时,就已经抛弃了这些东西。在工业化之后、我们如今仍在生活的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注重实用性、讲求目的、效益的时代,现实品格无疑是重要的,我们不可能不考虑生存、不考虑现实,
我们不能空谈理想而忘了脚下当有现实的根基,但现实品格的“度”在哪里?如何把握好这个“度”?
媚兰不同于希礼,也不同于思嘉。她有着和希礼一样的关于文明的理想,但在她身上也有面对现实的力量和勇气。媚兰身上兼具席勒所说的那种秀美与尊严,她既有女性的柔情,又有面对现实的力量与尊严。这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完全理想化了的人物,这样的人在现实面前,其精神将屹立长存。然而一如媚兰身体虚弱、早逝所隐喻的,这样理想的人格在新的现实面前除却精神长存,有没有现实的生命活力呢?这种人格是不是只能是作为文明的典范、理想,但在粗糙的、原野的现实面前,却仍旧缺乏生机?当人格与肉体不能两全时,舍生取义为理想。但也许这样庄严的时刻并不多,在现实的生活中,更多的是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但需熬得过现实的消磨。在这样平凡的日子里,在这样平凡的现实面前,需要思考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能两全——如陈嘉映所言
“何为良好生活”——即如何能做得好且过得好,而非人格卓越但生活惨淡,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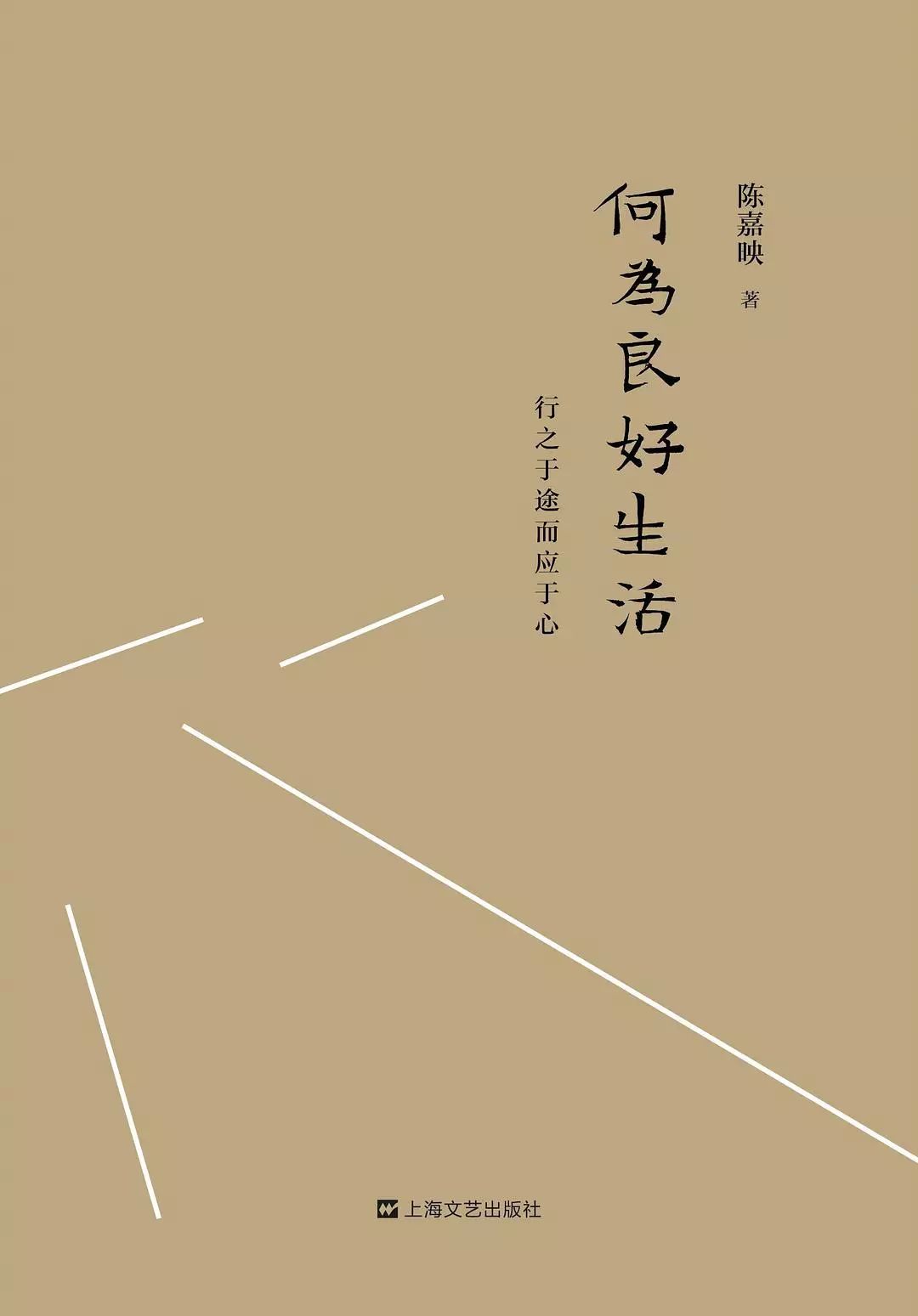
在一个我们只能接受而不可能拒绝的新的时代,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里,我们会有新的困惑、迷茫和孤独。思嘉处于旧时代与新时代交替的时期,她身上的现实品格与这个躁动、功利的新时代相契合,但思嘉又是为过去的时代所养育的,在她与过去之间,与曾经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还有一丝牵连,安宁的塔拉是她疲惫时的港湾和家园,
“她想到塔拉,就好像有只温柔、冰冷的手拂过她的心田一样……看到红土那自然的红色以及绵延的小山上那漂亮的暗黑色的松树林……她隐隐觉得得到了一些安慰,那画面使她坚强了一些,一些伤痛和狂乱的痛悔感从脑海的顶部被推到了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