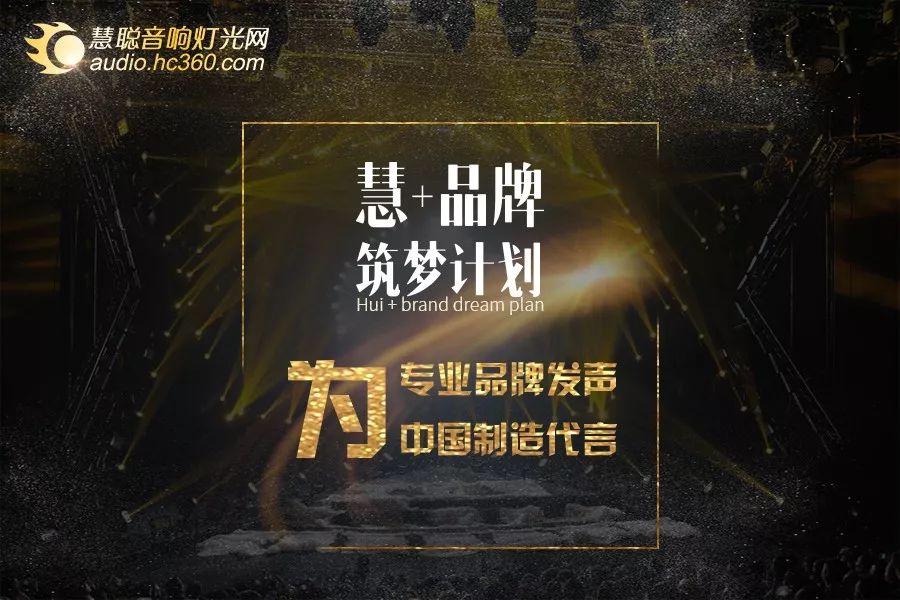如果以西方传统戏剧作为参照,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时空表现好像的确是“无限自由”。这具体表现在:相对现实世界而言,其舞台时间的流逝有时快、有时慢
(甚至中止)
,有时则与实际时间同步;其舞台空间有时被压缩
(也不断转换)
、有时是变大、有时则等值
(此时空间一般是固定的)
。但理解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时间的时快时慢或空间的转换,不应仅从戏剧叙事或表现人物着眼。不同于西方传统戏剧,中国传统戏剧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叙事艺术,在结构上它往往穿插、配置各种“戏点”
(或“卖点”)
。凡一般性叙事,时间往往压缩、空间不断转换,而每遇“戏点”,空间一般固定、时间流逝也变慢。故笼统地说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时空“无限自由”没有多少意义,其时、空的处理实受制于各种“戏点”。
关键词: 戏曲 舞台时空 自由时空 戏点
中图分类号: J 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 943X(2014)04 - 0084 - 07
如果以西方传统戏剧或话剧
(drama)
作为比较对象,我们或更易于看到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时空表现方面的特征。
西方传统戏剧可以说一直有着很深厚的写实传统,大都力求尽可能逼真地反映现实世界。从其舞台时、空的表现看,大都为确定的时、空,“三一律”作为一种戏剧理论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戏剧传统中产生的。所谓“三一律”即是规定:
戏剧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一本戏所写的故事只能是:发生在“一”个地点、“一”天以内的“一”个事件,故称为“三一律”。
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戏剧,其戏剧时、空是非常之确定的。虽然真正符合“三一律”的戏剧几乎没有,但“三一律”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传统戏剧对戏剧游戏规则的高度自觉地追求。
单从时、空的表现来看,中国传统戏剧似乎是一种完全没有游戏规则的戏剧。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者们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时、空是无限自由的。1956年著名导演阿甲在文化部戏曲演员讲习会报告中说:“
(戏曲舞台)
一个趟马百十里,驰骋沙场数十回合,在舞台上同场表演,都是常见的事。至于时间的处理,它是和处理舞台空间的特殊手法一致的。如果说,几十里的路程只要跑一个圆场,那么几十里路的跑路时间只要几秒就行了。”[1]

《穆柯寨》剧照
张庚先生在《戏曲艺术论》中也有专节讨论“戏曲舞台的时、空观念”。
在张庚先生看来,戏剧都是用有限的舞台时间与空间去反映无限的时间、空间,这样就存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但“在中国戏曲里面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了无视这个矛盾的办法”。
他以《穆柯寨》为例,说穆桂英住在山东的穆柯寨,杨延昭驻守在长城附近的三关,两地实际相距很远,但戏剧中的人物往来非常方便,可以转瞬即达。他以此说明戏曲的时空是无限自由的。[2]
范钧宏先生在谈到传统戏剧时空问题时,主要从戏曲结构方面着眼,他认为
戏曲结构的重要特点是“集中、精炼和夸张”,这一特点表现在时、空处理上主要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把不必要的情节精炼到最小限度,以便腾出手来,用夸张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描写那些最动人的场景。
譬如戏曲中的《梁祝》
(笔者按,应指越剧《梁祝》)
,梁山伯、祝英台同学三载的过程,可以一带而过,但对《十八相送》一场却尽情描绘,大做文章,通过一路不断变换的环境,刻划两个人依依惜别的情感和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再如《穆桂英挂帅》中的一场,有段唱词竟达一百余句之多,非常细致地剖析了穆桂英的精神面貌,写了历尽沧桑的今昔之感……从生活上讲,这只能是穆桂英登上帅台之前霎那间的内心活动,但在舞台上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加以夸张。”[3]
如果与西方传统戏剧的有限时、空对照,说中国传统戏剧是一种无限时、空,当然是可以的。但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时、空的“无限自由”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传统戏剧为何会采取这样一种时、空表现,其毫无游戏规则的背后是否仍有可以言说的规律?出于上述思考,笔者重新拈起这一旧题试加探讨。
需要交代说明的是,从总体而言,近百年,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演出受话剧影响甚大。现在一般读者能够看到的京剧及各种地方戏的音像资料,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戏曲电影
(绝大多数都有写实性背景)
以及80年代以来的反映舞台演出实况的影像
(如“中国京剧音配像”等)
,故这些影像作为材料使用时其史料的可靠性颇值得推敲,而昆曲折子戏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最具典型性,昆曲折子戏舞台演出受话剧的影响也最少
(主要是二道幕的使用)
,故本文以下在论证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时空时大多以昆剧、京剧折子戏为例,特此说明。西方传统戏剧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具体到每一幕而言,其每幕的空间场景是固定的
(多为室内)
,在每一幕的演出中,舞台上时间连续的流逝与台下观众的时间流逝是同步的,唯换幕之后,才可以有时间、空间的跳跃或转换。
中国传统戏剧的演出也可以分为若干场次或单元
(即传奇、杂剧的“出”或“折”)
①,对每一场戏而言,其舞台所表现的时间、空间仍是不确定的,但每一场也都对应着一段连续的时间段,只有场与场之间才出现时间的中断或跳跃,换场当然也带来空间的转换,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戏剧“场”的转换与西方戏剧“幕”的转换具有同样的意义,故我们现在讨论中国传统戏剧的时、空问题,不妨即具体到“场”,看每一场中时间与空间是如何表现的。
如果把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所表现的时间、空间与日常世界的时间、空间进行比较,从理论上说它们之间可有以下三种关系或类型:
一是相对实际日常世界的时、空而言,戏剧舞台上表现的时、空是变短或压缩的。
这一点最为普遍、显著,也易于理解。因为戏剧演出都不能不受限于演出时间和舞台空间,故表现时、空时一般加以缩简或压缩。俗语所谓“一个圆场万水千山,四个龙套千军万马”,可谓这种时、空压缩的最好注脚。最典型的如《浣纱记》“寄子”折的前半场,伍子胥预知吴国将亡,为存伍氏血脉将其子寄托其好友齐国大夫鲍牧,“寄子”折的前半场是父子去齐的旅途之上。吴、齐相距千余里,途经“万水千山”,按当时的旅行速度一般要一个月左右,昆台实际演出时间一般为一刻钟,空间、时间都可谓是高度压缩。《浣纱记》“寄子”折中空间、时间在压缩时存在一定的同步现象,但更多的情况是时间的压缩与空间的压缩不一定同步。如京剧《乌龙院》“坐楼杀惜”中有一段,表现宋江、阎惜姣在乌龙院房内一夜中各怀心事、不能安然入寐,舞台表现仅用了十几分钟,这一段表演从时间来看有很大压缩,但其空间却基本固定不变。
二是相对日常世界的时、空而言,戏剧舞台上表现的时、空是延长或扩大的。
这一现象相对前一点而言,虽然不够普遍,但也是客观存在的。如范钧宏先生在论述戏曲结构的“夸张”时所提到的京剧《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登帅台前的一段表演中,主人公将其霎那间的内心情绪用十几分钟的大段唱来表现,就属于对现实时间的极大延长。又如《白罗衫》“看状”一折前半段,徐继祖独在房内看状,从状词中猜知自己现在的养父徐能可能即是杀害其生父苏云的江洋大盗。从实际情况来说,徐继祖应当很快就看完状纸的,但昆曲舞台在表现时使用了大段的演唱及独白,以表现徐继祖内心惊疑、矛盾的情绪,故舞台的时间流逝与实际的时间流逝相比明显较慢。中国传统戏剧常常有人物登场后,有大段自我表白或抒情性歌唱,而这样的独白或歌唱可能根本起不到进一步推进剧情的作用,在这一刻,剧情完全停止了推进,舞台上的“表”几乎完全停止跳动。当现实世界的时间在舞台表现时被延长、甚至暂时停滞时,而这一时间对应的空间则一般是固定不变的。
现实世界的空间在舞台表现时被扩大,这种情况按道理上并无不可,但实际上并不多见,最典型者如《西游记》“借扇”一折,演孙悟空化作小飞虫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迫使其借扇。上海昆剧团的做法是演孙悟空的演员先一跃到桌上,然后做飞舞状(表示已变为小虫——当然这个小虫比实际上的小虫大千万倍)。此后孙悟空又一跃到地上,当扮铁扇公主的演员仰头“喝茶”时,一个筋斗从其头顶上翻过去落在她身后——这样就算“钻进肚子”了;然后在她身后,做出拳打脚踢的样子,扮铁扇公主的就在前面表演“肚子疼”,满台翻滚,然后孙悟空又在其前后左右翻腾、跳跃。铁扇公主的肚子本来并不大,但在孙悟空钻进去之后就变得有半个舞台大了。这是典型的空间扩大。又如《跃鲤记》“芦林”折,描述孝顺而迂腐的姜诗在芦林遇到被婆母驱逐的妻子庞氏,这真是“狭路”相逢,其妻因向其申诉实情,恳求姜诗带其回家。整折戏发生的地方都在芦林中的小道上,但两个演员在实际演出时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
(林中小道)
,也可以说是将芦林中的小道极大地扩大了。《白罗衫》等很多戏剧中都会用到官员的印信,实际生活中的印信较大者不过五六厘米见方,但舞台上所用印信大都二十多厘米见方,以表现官员的位高权重,这也是属于空间扩大的情况。当然这是舞台道具一类的扩大,如果把这种情况也考虑在内,空间扩大的情况当然也不算少。
三是相对实际日常世界的时、空而言,戏剧舞台上表现的时、空与之等长或等大。
这种情况应当说还是非常普遍的。如《牡丹亭》“寻梦”一折,写杜丽娘梦醒之后背着春香,独自去后花园寻梦。在这段表演中,其空间是随着演员的表演
(或念白、唱词的指示)
而不断变动的,其演出时间约为半小时,但这一时间长度与戏剧故事实际发生的时间长度应当说也是基本接近的。又如《朱买臣休妻》中《逼休》一折,演朱买臣为妻崔氏所迫写休书,这段表演从朱买臣回家、夫妻见面写到崔氏得到休书离家,昆台表演一般为三十分钟,这与故事本身的时间也基本相当。又如《跃鲤记》“芦林”折,舞台表演从夫妻芦林相遇到分别大概三四十分钟,这一时间长度与故事本身的内容长度也算是基本相近。
从舞台的空间表现看,很多传统戏其空间环境发生在室内
(或者说其中有相当多的故事片段是在室内发生的)
,而大多数室内戏其空间基本是固定的,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其舞台所表现的空间与实际日常世界的空间是同样大小的。
中国传统戏剧中实际上有很多室内戏或场景相对不变的戏,其舞台空间是固定的,舞台表演的时间与实际时间也基本相近。这也就是说,在时、空表现方面,这些室内戏或场景固定的戏与西方传统戏剧在“理论上”也可以完全相同。
我们为了便于说明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时、空的特点,将其与现实世界的时、空对比,分为以上三种情况,而实际上作为一种动态的戏剧演出,几乎任何一种传统戏剧其时、空表现都不会是纯粹的上述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上述三种情况往往是同时出现在一场戏中。
具体从时间方面而言,舞台时间可能有时流逝较快、有时较慢
(甚至中止)
,有时则与实际时间基本同步。

《浣纱记·寄子》剧照
如《浣纱记·寄子》,戏一开始表演伍氏父子在路上,时间被极大压缩,此时我们可以说舞台上的“表”跑得很快,但此后当伍子胥向其子说明远路赴齐的真正缘由时,其子面临生离死别,万分悲痛,伍子胥也非常伤感,这一段表演是外、作旦两门脚色轮唱两支非常有名的【胜如花】曲:“清秋路,黄叶飞……”,此时的时间流逝明显变慢,但此后又是在路途,时间流逝又开始加快,直到父子两人进入鲍牧家中,舞台时间又开始变慢。应当说《浣纱记·寄子》并非特例,而是一般情况的反映。
从空间方面而言,舞台空间有时被压缩
(也可以说此时空间是不断转换的)
,有时是变大,有时则等值
(此时空间一般是固定的)
。仍以《浣纱记·寄子》为例,戏一开始是在路途上,当时间飞速流逝时,其空间也是时刻在变动的;演唱两支【胜如花】曲时,舞台时间变慢,而舞台空间也相对固定
(在路途上的某一点)
;此后又表现路途之事时,舞台时间又变快,空间也不断随之转换;进入鲍牧家堂内,舞台时间又开始变慢,此时舞台空间基本又变为固定空间
(等值)
。中国传统戏剧舞台空间的产生,主要借助演员的言辞、行动以及桌、椅等简单道具以及观众想象的配合,也就是长期演出中自然形成的观、演默契,故其空间的转换同样依赖这种默契而实现。②
在谈到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空间可自由转换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述及两个空间的自由并置与合并。
现代剧场舞台灯光的使用,使得两个表演空间、甚至更多空间可出现在同一个舞台,这在西方传统戏剧中很少见。但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而言,在同一舞台并置两个空间,则非常普遍。
如中国传统戏剧有许多戏都有因室外之人与室内之人发生关系而推进剧情的,或因室内先已有人走到房外而与室外之人发生关系,或因室外之人进入室内而发生关系,此时观众往往会看到舞台上同时有两个空间存在。如《活捉三郎》这出戏,先是阎婆惜出场,表现其自荒郊野外来到张三郎家门前叩门,而后屋里的张三郎出场、伸懒腰、去开门。③ 此时观众同时看到屋里、屋外两个空间,当阎婆惜进入房内,张三郎做出表示关门的动作后,房外的空间消失,整个舞台都被默许为房内,原有的两个空间此时变为一个空间。《玉簪记·琴挑》的情况与《活捉三郎》有恰好相反处:潘必正、陈妙常本来同在室内这同一空间,因潘必正以言辞相挑,惹陈妙常羞恼,只得告辞,此后潘必正
(自家说出)
躲在花荫深处听陈妙常自言自语。此时原来的一个舞台空间转变为两个空间,观众同时看到两个空间里的人物在活动。又如《西厢记·游殿》,先是小和尚法聪带领张生闲游普救寺佛殿,而后红娘、崔莺莺也出场、游玩,观众此时可以看到两组人物同时在舞台行动。从演员在舞台上的实际距离来说,双方演员当然都处于对方实际上应可觉察的范围内,但在扮演张生的演员用动作表示看见莺莺之前,演者、观者达成一种默契:双方各自处于独立的空间,互不相扰。随着演员的提示,两个空间才在观众的想象配合中霎那间合并为一个空间。
基于上述相关时空的讨论,我们确实可以说,中国传统戏剧其时间、空间表现都是“无限自由”的。
但讨论至此,我们才开始触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传统戏剧为何会采取这种“无限自由”的时、空?在其表面的“无限自由”的背后有无规律的东西可以探求?在讨论传统戏剧舞台时、空问题时,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舞台时间的变短或延长是由于戏剧叙事或表现戏剧人物的需要。
④
与西方传统戏剧偏重叙事的情节线不同,中国传统戏剧往往偏重某一情节点的表现,即表现在整个叙事背景中戏剧人物在某种特殊情境下的思想情感,着力在这一点上淋漓尽致地描摹。所以中国传统戏剧往往不是靠人物的频繁上下场来推进叙事,而往往是借助简短的过场戏或者人物对事件的交代性叙述粗略地完成故事叙述,从而将更多笔墨用于特定情境中人物思想情感的描摹。昆曲舞台有很多独脚戏或者基本以一个演员为主的戏,如《烂柯山·痴梦》、《宝剑记·夜奔》、《牡丹亭·寻梦》、《牡丹亭·拾画·叫画》、《西楼记·玩笺》、《疗妒羹·题曲》、《长生殿·酒楼》、《思凡》等,这些戏都可以说是表现戏中人物在某种情境下的思想活动或情感,作为背景的情节叙事基本上都是在人物出场后非常简略地陈述。又如中国传统戏剧有很多场景都是描摹别离之情,如《琵琶记·南浦》、《西厢记·长亭分别》、《玉簪记·秋江》、《紫钗记·折柳·阳关》、《浣纱记·寄子》、《梁祝·十八相送》等,此前的相关人物、事件往往也是作为背景很简略地交代,唯独在写别离之情时着力发挥,极尽描摹之能事。当戏剧舞台在集中表现人物思想情感时,舞台时间往往变慢、甚至停滞,空间也基本固定。王骥德《曲律》论及传奇结构云:
勿太蔓,蔓则局懈,而优人多删削;勿太促,促则气迫,而节奏不畅达;……传中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如《浣纱》遗了越王尝胆及夫人采葛事,红拂私奔、如姬窃符,皆本传大头脑,如何草草放过?若无紧要处,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厌憎:皆不审轻重之故也。[4]
王骥德《曲律》所论大多在曲律,《曲律》能有此节论及戏剧结构殊为难得,王骥德能说出“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说明中国古人也已注意到判别轻重对戏剧叙事的意义。
但仅从戏剧叙事或表现剧中人物方面,去理解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时、空,似仍嫌不足。
在笔者看来,理解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时、空,其关键是把握中国传统戏剧的所表现。换言之,中国传统戏剧究竟试图展现给观众什么内容?是凭借哪些内容吸引观众的?

解玉峰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传统戏剧的“戏点”或“卖点”大致有四类:
一是“情志”,
即表现戏剧人物在某种“情境”之下的所思、所想、所感,择取情节“线”上的某一“点”做文章,如《宝剑记·夜奔》、《牡丹亭·寻梦》、《长生殿·酒楼》等独脚戏或基本以一门脚色表演为主的戏最有代表性。
二是“有戏”
,在观众预知当事人全部秘密的前提下,着力表现一方当事人“假”面目不断被戳穿、“真”面目最终显现的过程和趣味,如《十五贯·测字》、《玉簪记·琴挑》、《白罗衫·看状》、《梁祝·十八相送》、《白蛇传·断桥》等对子戏或“三脚撑”的戏皆属此类。

《西厢记·游殿》剧照
三为“谐趣”,
即以净、丑插科打诨为主的、极富谐趣的表演,如《西厢记·游殿》、《拜月亭·请医》、《绣襦记·教歌》、《红梨记·醉皂》等折子戏最有代表性。
四为“技艺”,
即以表演者唱、念、做、打等各种功夫的显示作为卖点吸引观众,《石迁盗甲》、《白蛇传·水斗》、《吕布试马》等各种武戏最具代表性。从“戏点”或“卖点”的角度来说,南戏、传奇在结构上一般是各种“戏点”或“卖点”的交相穿插、比配。
[5]
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戏剧中并非一种“纯粹”的叙事艺术,其所述故事虽然也可能富有传奇性,情节本身即引人入胜,但其吸引观众的并不止如此,也可以包括各种可取悦观者耳目的歌舞表演、滑稽表演、技艺性表演、甚至声色表演,而所有这样都可以打着
(演)
“戏”的旗帜,这与西方传统中作为较纯粹叙事艺术的“戏剧”,主要借助一对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紧紧抓住观众,可谓大相径庭。
带着这样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来看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时、空表现。我们可以注意到:
从时间方面来看,凡是舞台时间变慢、或甚至停止不前时,往往即是“戏点”之所在;从舞台空间方面来看,凡是舞台空间相对固定或舞台空间基本与实际空间等值、甚至是扩大时,往往即是“戏点”之所在。
而当舞台时间飞速流逝、舞台空间也迅速转换时,往往即不是“戏点”之所在。
以江苏省昆剧院演出的《白罗衫》为例。《白罗衫》的《看状》一场之前有一个简短的过场戏:徐继祖作为江南巡抚巡视江南,其生父苏云趁其升堂理事时递上状纸,状告其养父徐能十八年前谋财害命的罪状。这段过场戏整个演出仅十分钟,从总体时间来说可谓高度压缩,或者说舞台的“表”跑得非常快。
但是在这十分钟左右的表演中,也有几处的舞台时间是明显变慢的:
一是
两个皂吏表演出班房、验封、起封条、开锁、拔门闩、开大门等动作;
二是
徐继祖出场时,徐继祖在吹打乐中做抖袍、整冠、踱步、落座等一系列官生显示派头的程式动作;
三是
太平府知府上堂禀参,徐继祖作为八府巡按对其严加训斥,知府唯唯称是后告退;
四是
苏云被允上堂,递上状纸,徐继祖略沉吟后当堂答复说“三日后听审”;
五是
升堂理事毕后,两皂吏重新出来抬告牌、提门槛、关大门、上锁、上封条等。以上五处表演中,仅仅第四处直接与戏剧叙事直接相关,因为只有苏云递上状纸,后面才能有徐继祖看状一场,但这一段在十分钟的表演中仅占不足两分钟,更多的表演时间用在两个皂吏前后的两次表演上,以及用在徐继祖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出场、训斥太平府知府时显示八府巡按派头的表演上,而这些表演总体来说热闹有趣,考虑到传统戏的观众不乏喜欢“看热闹”的
(可能特别喜欢看八府巡按如何升堂理事)
,所以不惜在这些有“卖点”的地方作浓墨重彩的表演。
如果说《看状》前的这场过场戏“卖点”主要是热闹、有趣,而其后的《看状》一场则主要是细腻、传神地描摹徐继祖室内研读状纸时的思绪、情感——空间是固定不变的,时间流逝非常之缓慢!——因为描摹戏中人物之“情志”恰为此节之“戏点”。
又如《西厢记·游殿》,若从戏剧叙事方面来考虑,充其量是一过场戏,其
(叙事性)
作用是让张生与崔莺莺在佛殿偶然相遇,以便让崔、张一见钟情后,引起后面的偷情故事。但如果仅从叙事角度来考虑,《游殿》便显得不可思议:整个《游殿》演出五十多分钟,而相关崔、张相见、彼此生情的表演不足十分钟,《游殿》中表现小和尚法聪带张生四处闲游、一边讲一些笑话段子则占了四十多分钟,《游殿》这一折的主角实际上是扮演法聪的副净,这出戏的主要“卖点”恰是滑稽有趣!从这出戏的舞台时、空来看,凡是相关滑稽性表演时,舞台时间立刻变慢,空间也基本固定,凡是无关于滑稽性表演时,舞台时间往往被大大地压缩、空间也迅速转换。
再如折子戏《试马》。现在很多京剧院武生演员均能演出,浙江昆剧团武生演员林为林也以能演此戏出名。《试马》或称《吕布试马》,大意为三国名将吕布收得赤兔宝马,而赤兔马生性暴烈难驯,吕布以高超骑术降服赤兔马,得意回营。这场戏几乎谈不上有完整的戏剧叙事或人物性格塑造,可以嫁接到三国故事中任何与吕布相关的叙事中,甚至改为赵云“试马”或岳云“试马”
(可不提及赤兔马)
亦无不可。因为这出戏的“卖点”或“戏点”主要是表现武生演员的“技艺”,特别是身扎大靠而能跌、翻、滚、跳等诸多高难度“功夫”。当武生演员在展示其看家本领时,空间固定不变,时间几乎完全停止不前,任凭台上锣鼓喧阗!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曾写到当地目莲戏演出“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戏子献技台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6]这些目连戏表演吸引观者的显然是各种“技艺”。至于《三岔口》、《水斗》、《挡马》等戏均以“技艺”表现为主,而时间的展开也以此为目的。
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戏剧的各种“戏点”,若从首尾完整的全本戏来看,往往会各有偏重、交替出现,有些场次以表现
“情志”
为主,有些场次以表现
“有戏”
为主,有些场次以表现
“谐趣”
为主,有些场次以表现
“技艺”
为主,甚至在同一场中也可能是多种
“戏点”
交相映衬。从舞台时、空呈现来看,凡是一般性叙事,其时间往往被压缩,空间不断转换,而每有
“戏点”
,往往空间固定,时间变慢、甚至完全停止不前。当代中国的一些年轻观众,往往觉得中国传统戏“很慢”,其实中国传统戏剧情节推进也往往非常迅即,时空也可以迅速转换,经常是很“快”的,其经常性的“慢”往往是慢在一些“戏点”上,此时剧情几乎完全停止推进,而年轻观众因为文化背景的转换已不能像传统观众那样欣赏这些“戏点”
(特别是较长的抒情性唱段)
,所以自然会觉得“慢”!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浓淡、虚实的对比,书家更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说,学术界过去讨论到中国传统戏剧的时空转换问题时往往加以借用,并说中国传统戏剧的时、空表现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如果说中国传统戏剧在戏剧结构方面也可以说有浓淡、有虚实,或者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们或应更加明确为各种“戏点”的调配和穿插,其“实”处、“浓”处或者有“话”可说处往往即为“戏点”之所在,其“虚”处、“淡”处或无“话”可说处,往往是一般性叙事,其意义主要是为“戏点”提供依托的背景。
从舞台时、空方面来说,时间的快慢,空间的转换,也无不是围绕各种“戏点”而变化,是为表现“戏点”而服务的。
所以笼统地说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时、空“无限自由”没有多少意义,其对时、空的各种处理往往是受制于“戏点”的。虽然我们中国古人可能对何谓“戏点”或“卖点”,如何有效地利用舞台时、空为“戏点”或“卖点”服务,并没有清醒的理论上的自觉,但从现存的很多昆台折子戏来看,其对舞台时、空的处理确令人拍案叫绝,当然可以进一步推敲、加工的地方也仍有很多。
注释:
① 如果我们把“场”视为空间固定且时间连续的演出单元,那么这种“场”与传奇、杂剧所谓的一“出”或一“折”,不尽等同。传奇、杂剧的所谓的一“出”或一“折”虽可视为一个演出单元,但这一演出单元有时包含不止一个“场”,一“出”或一“折”在时间上一般具有连续性,但空间未必固定,有时空间、时间都有明显的跳越或中断。
② 关于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空间,学术界旧有“背景在演员身上”之说。窃以为不尽妥当。如果观众不能理解和领会演员对戏剧背景的提示,或者说离开了观众的想象和补充,仅靠演员的表演,舞台空间以及空间的转换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故从观者、演者达成的“默契”去理解舞台背景的创造或更妥当。
③ 传统的演法是在阎婆惜叩门前,戏班有人搬上桌、椅,现在通常是在阎婆惜叩门前拉上二道幕,负责道具的趁此空隙摆上桌、椅,在阎婆惜叩门后将二道幕再拉开,表示空间转换。
④ 参见阿甲《戏曲表演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24、125页;范钧宏《戏曲编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4、15页;沈尧《戏曲结构的美学特征》,收入《戏曲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14页等。
参考文献:
[1] 阿甲.戏曲表演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 张庚.戏曲艺术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3] 范钧宏. 戏曲编剧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 王骥德.曲律[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C].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J].文艺研究,2006(5).
[6] 张岱.陶庵梦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来源:戏剧艺术
(ID:Theatrearts )
作者:何萃
(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图片:网络
责编:卫荣

媒体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