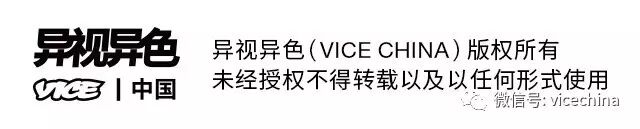怒罗权一开始并不是什么“黑帮”,只是一些出生于东北的日本残留孤儿二代,回到日本后成了不被社会接受的一群人。到了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按摩店在歌舞伎町的繁荣发展,他们开始把主要的盈利手段变成了向中国人收取保护费。大伟还有其他几个怒罗权的领军人物就是在这段时期登上的历史舞台。
混迹于歌舞伎町的中国黑帮
李小牧
谈起在日本的中国“黑帮”,永远都绕不开的一个组织就是怒罗权;而说到怒罗权,不得不提的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 东北虎,他在我的处女作《歌舞伎町案内人》中出现过,当时我没有用他的真名:大伟。
在日本,公民拥有结社自由的权利,所以像山口组这样 “著名” 的组织,我们并不完全可以称其为黑帮。目前,被日本警察厅认定的暴力组织有22个,皆由地地道道的日本人组成。

作者与住吉会原副会长阿形充规合影
日本版维基百科对大伟所在的怒罗权组织有很清楚的介绍:它是唯一一个被日本官方认可的由“原中国人”组成的暴力团体,但它仅仅是准暴力组织。而所谓 “准暴力组织”,就是指在规模和影响力等考量指标上,比 “暴力组织” 稍低一级。

这条街道曾经是中国流氓在东京的据点,如今衰落
怒罗权成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一开始他们并不是什么 “黑帮”,只是一些出生于东北的日本残留孤儿二代,回到日本后在不被社会接受、认可的情况下,自发团结在一起,对抗日本人,为自己打抱不平。所谓日本残留孤儿,就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日本人逃离东北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孤儿,他们大都被中国人养大。
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怒罗权的身影,从东京到横滨,再到福冈,广岛等等。早期时候,他们组织中的一些人买卖假电话卡、在弹子机房做手脚、或者做一些盗窃之类的事情。到了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按摩店在歌舞伎町的繁荣发展,他们开始把主要的盈利手段变成了向中国人收取保护费。大伟还有其他几个怒罗权的领军人物,就是在这段时期登上的历史舞台。
维基百科对大伟也有一段还算详细的介绍:他是怒罗权的重要发起者者之一,所带领的组有200多人,是怒罗权里最大的组。他和弟弟小伟是尔冬升导演、成龙主演的电影《新宿事件》主人公的最初原型。

电影《新宿事件》海报
1996年,我作为歌舞伎町的案内人,终于拥有了两条街作为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在这两条街上,我和我那个十几人的团队可以自由行动,把来往游客介绍给相应的店铺。突然有一天,大伟的队伍在歌舞伎町出现了,他的部下们先是在其他的街上跟我抢客人,然后开始在我的团队中挖墙脚,想要把我赶走,把我的团队和我的两条街据为己有。
这两条街是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拿下来的,我不可能拱手相让。

歌舞伎町夜景
有一天,大伟约我去咖啡厅谈判,跟我提了很多不平等要求,甚至直言让我把一切都拱手让给他,自己走人。他带了一群人跟着他,似乎是想用武力逼我屈服。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那天,看他们那阵势,似乎是如果我不答应就要我好看的意思。
还好当时我已经在日本待了七八年,无论是日本“黑道”还是警视厅都有了一些还算有点分量的朋友。在去见他们之前,我就已经通知了警视厅的一个朋友,他叫名高,也是多次在《歌舞伎町案内人》这本书中出现过的。我和名高都猜到了事情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他早早地带了几个警察前后包围了整个咖啡厅。但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只是谈判,没有打起来,所以警察们不能闯进去。

《歌舞伎町案内人》封面,角川出版社出版
正当我和大伟的对话已经火药味十足甚至到了一点就炸的地步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名高打来的。他让我像是接普通电话一样,往前门走去。我照做了,于是,在刚刚走到前门的时候,就被两三个警察前后夹击地 “逮捕” 了。这是名高救我的方式,也是他保护我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被别人知道我和警察也走得这么近的话,对我来说,是有危险的,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带我脱离险境。
后来,名高又通过别的警察给大伟等人打电话,劝他们不要再打扰我,因为我的存在对歌舞伎町来说是有益的。于是他们对我的态度收敛了很多,但我这个人比较能进能退,即使是竞争对手,我也不愿意结仇。出于给他们留面子的考虑,我还是决定每个月给他们交保护费 —— 既然他们想要钱,我就给他们钱好了。虽然当时给日本人交保护费也才两万三万或者顶多五万,但我还是答应每个月给他们交二十万日币。
就这样过了四个月,我慢慢发现,怒罗权不同于日本的组织,当我遇到麻烦需要“保护”的时候,叫他们几乎是没有用的。相反,因为他们的“保护”,我反倒得罪了一些日本人。这样一来,我还是决定不要他们的 “保护” 了。于是我通过日本的警察朋友,终结了向他们交保护费的日子。可是后来,他们秘密地把我团队里的一个小弟拖到角落里打了好几耳光,算是对我的威胁。我知道之后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只有打电话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这做,你挣你的钱,我挣我的钱,咱们互不干涉,你也别影响我们。”

关于怒罗权的报道
没想到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斡旋和交涉,我竟然和大伟交上了朋友。在他第一次被判刑前,我们有过一个不小的交集。大伟被逮捕之后,媒体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所以出新闻的时候就为难了。当时我出过的书里有我俩的合影,还有他单独的照片,TBS(东京广播电视台)想用照片,就打电话给我。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照片给东京台的。
后来 TBS 又通过我的出版社,也就是角川出版社,想拿到这张照片,但是出版社肯定也是要征求我的允许的,我仍旧拒绝了。然而,第二天,TBS 的新闻报道中还是出现了这张照片,我一气之下,当时就和 TBS 联系了。做这个报道的记者我认识,是个女孩子,可能是因为这个新闻实在太大,她没能抵挡住诱惑,最终不经授权使用了照片。
我带着朝日新闻的记者朋友去找她,她跟我赔礼道歉,说着说着都哭了。可是哭也没有用,这实在是件大事,我告诉她说要向大伟本人道歉才行,可是这件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后来等大伟假释出狱之后,我特地和朝日新闻的记者朋友跑去跟他解释了一次。因为他出狱只是暂时的,判刑之后还是要回到监狱去,所以我们让他写委托书,准备帮他起诉 TBS —— 这就是我在日本出版的第二本书《歌舞伎町案内人2》一开头的故事。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案子,就是千叶弹子机房门前抢劫运钞车、杀人案件。负责运钞车的人当场被枪杀,两名罪犯抢走了车里的数千万元日币现金,在日本晃了一圈之后逃到了中国,据警察说是去了东北。
当时警视厅的搜查一课(类似于国内的重案组)找到我,给我看了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被拍到的录像,本来是想问我有没有在歌舞伎町见过他们。但因为我不太清楚,加上他们又和东北有关,所以我就把这几个警察介绍给了大伟。
最后,他们确实在大伟的帮助下抓到了这两个在东北逃亡的犯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中国人在当地被判了死刑,日本人则被押解回国。因为得益于大伟找到了当地的公安机关,这件事情才得以快速被解决,所以在大伟后来因为毒品被抓面临判刑的时候,警视厅出了文件证明他曾经协警办案,在他申请减刑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点作用。
大伟出狱之后没多久,就离开了日本,回到国内做生意。他走之后,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2008年前后,我经常回国,每次回来他都会请我去非常高档的餐厅吃饭。我曾带着朝日新闻的记者采访过他一次,当时还上了头版。
因为他是日本国籍,所以也经常回日本,每次回来他都会找我,然后我就叫上一些警察朋友一起吃饭。但是,自从2013年怒罗权被警察厅认定为准暴力组织之后,日本警察跟他一起吃饭的机会就很少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