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当我在金融时报读到特朗普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怪中国,只能怪美国自己,我知道我在去年美国大选前的判断没错,特朗普当总统远远胜过希拉里。“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怪中国”,能说出这种话的美国总统,自1980年代以来,只有特朗普一人而已。也许从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而言,特朗普将迎来中美关系最好的时代。而时间倒退到美国白左偶像奥巴马当选后不久的2010年,中美关系的情形却远非现在这样,可以说是极度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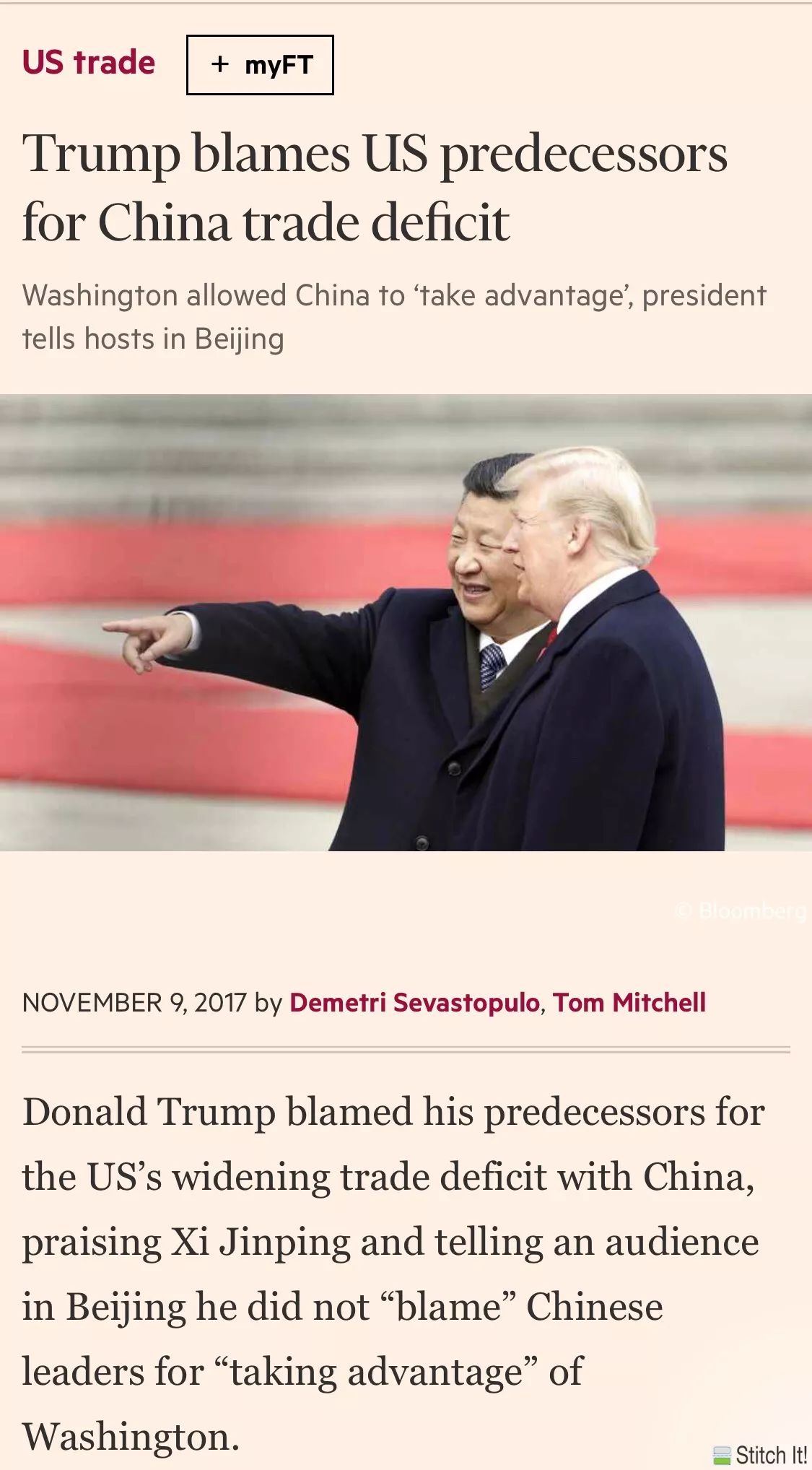
特朗普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不能怪中国,只能怪美国自己
2010年中美贸易争端无比尖锐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称中国的贸易顺差造成了其数百万就业机会的丧失以及巨额赤字,马丁伍尔夫在金融时报发表《How to fight the currency wars with stubborn China》,盖勒普的民调显示,在美国人的心中,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比伊朗还大(那些英文不好,不了解美国主流社会形态的人估计对此毫无所知),焦虑无比的笔者以英文在华尔街日报撰文《《The US will losea China Trade war》对他们严加驳斥,呼吁美国停止对中国贸易战的企图。那篇稿子我写了一个月之久,投稿给华尔街日报名不见经传的自己完全不抱被发表的希望,却成为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我的处女作。是的,美国是我处女作发表的地方,我的处女作是全英文的。

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学人,我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打不相识”地认识了许多美国经济学界、外交界、商界和财经媒体的朋友,不少机构请我访美做交流,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利用自己有限的影响力去捍卫中国人民的就业机会,去到美国的中心地带推动外交领域的微观探索,把中国公民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慈悲坚忍的信仰情怀带到大洋彼岸,去打破美国教育和主流媒体营造的关于中国人的极为负面僵化的形象样板(中国人和他们眼中文革红小兵真的不一样,也绝不是想灭掉美国的无产阶级战士。)。
这次赴美Citizen Diplomacy历时一个月,对于我这样一个月薪三千的教师来说颇有破产爱国的决绝,很多朋友都劝我放弃,因为大国相争,犯不着我这一介小民去螳臂当车。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美国是个公民意识极强的国家,而在中国,位卑不敢忘忧国也是士大夫传统,如果连我这样游学海外多年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有这种情怀,又何敢要求一般国人去如此忧国。
我在美国的第一站是波士顿和剑桥,应波士顿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Newman School校长Harry Lynch的邀请去他们学校讲国际经济学和Citizen Diplomacy。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僵化印象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美国的教育系统,意识形态的对立始于此。在和Newman教导主任Daniel Ohman的交谈中,我得知学生在经济学学习上,缺乏目的性和实际应用的能力,因此我提出可以把Citizen Diplomacy的平台引入经济学教学当中,让学生活用自己的所学,去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去帮助解决矛盾和对立,去建立互信与互助,关于这点我可以用亲身的经历作解说。如果效果好,可以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其他科目教学当中。Newman学校若能接受我的建议,那么其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就会更加人性化,更有可能产生友谊、同情和支持。这就好比“当你给一个人庆祝过生日,交换过笑话之后,即便是身处战场各为其主,你也很难对这个人开枪”。
Daniel对我的建议很感兴趣,不过他也有一些保留意见,因为美国的孩子生活在由ipad、facebook和其他消费主义享受主义的尤物组成的自我世界当中,对外部世界并不关心,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对中国,所以我那把Citizen Diplomacy注入教学的构想没有什么可行性。可是我不这样认为,我看到了另一个美国:虔诚强大的宗教信仰,感性大于理性的人文文化。美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票房奇迹《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都是一种基于悲剧情怀的自我救赎,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美国人民是极富同情心的。因此我用一个中国普通家庭在贸易争端中的悲剧开始了我的课程:
有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农民工兄弟,他在一个香港人开的玩具厂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不再给他们的厂子下单,香港老板就把玩具厂给关掉了。这位农民工兄弟除了做毛绒玩具之外没有别的技能,他的再就业前景是绝望的,女儿也只能休学了。每次他徒劳无功地找工回来,女儿都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什么时候可以吃红烧肉。他们已经半年没有吃过肉了。终于这位农民工兄弟放弃了再就业的希望,把所有的钱凑在一块买了猪肉,回家炖了一顿红烧肉给全家人吃个痛快,一家人特别开心,以为爸爸找到工作了。事实上他在这红烧肉里下了毒药,全家人在希望的喜悦当中死去了。这就是贸易争端所带来的小人物小家庭的悲剧,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不只是总统圆桌上的一纸文件。我在英国时也在饿死的边缘徘徊过,也曾有在接到母亲突然去世的电话后躲到打工餐馆的员工厕所痛哭失声的经历。这也就是我写信力劝奥巴马总统不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情感缘由。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很多人眼中都出现了泪水,甚至包括Daniel。Daniel说他一定会采用我的建议,因为这是公民意识的崛起,是人性的崛起,也是宗教的慈悲。其实能这么成功地把Citizen Diplomacy的理念植入美国人的心中,不是没有其背后的艰辛曲折的: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崇尚在“是非对错”的“理论输赢”上寸土不让的民族,在我游学国外的早期我就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常常和各个国家的人吵得不可开交,可是论“理”的输赢往往会伤害西方人的感情,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同情支持和帮助,嘴皮上快乐了,却解决不了实际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严重的孤立,验证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我们只有放下了意识形态的不同,放下了民族主义的对立,才能站到促进和谐世界的同一条跑道上。
很多美国人都为我这种情怀所感动,特别在他们知道我是大乘佛教修行者之后,他们明白我和他们很多人一样,有着非常强大坚定的信仰,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使得很多美国人愿意和我一起加入到促进中美公民阶层深刻了解的运动中来,我所受到的帮助和支持是我无法想象的。我到波士顿的第三天,前麻省理工大学划船项目主任Tom Tiffany先生就主动提出要把我引荐给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eter Diamond教授。
我在访美之前,就知道我将和一些学者精英会面,我知道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宗教慈悲情怀的,我必须用学术的观点和理念去打动他们,必须用学术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去吸引来自左中右的精英人群。因此我做足了功课,我为Citizen Diplomacy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双边关系赤字(两国在以货币为单位和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之间的不平衡)和代表赤字(政府系统的执政所为和构建政府权力基础的人群对政府执政期待之间的不平衡)。我指出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会带来过度的民族主义、对立冲突、军备竞赛甚至是战争,会在上层建筑中制造巨大的权力真空,加深社会动荡,威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茶党的兴起,中东的动乱,这一切都不是偶然。Citizen Diplomacy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两方面的严重赤字。
1月30日晚我和Peter Diamond教授在剑桥的一个精英俱乐部的年度峰会上见面了,我们探讨了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把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通过指数的形式加以量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决策层的政策结构调整提供依据。期间教授先生还和我讲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他在上海讲学的经历,说中国的发展是个值得全世界研究的奇迹。席间我获知教授有可能加入美联储理事会,所以我即兴告诉教授先生和夫人我飞了数万公里,历经23个小时旅程飞到美国,我希望代表来自遥远中国的经济学子给他们一个拥抱,并祝贺教授进入美联储的愿望能得到实现。最后还发生了一段幽默的小插曲,我顺手拿出《华尔街日报》给我的支票让教授先生给我签名,教授一惊说:“不会吧,我可不能签你的支票。”我告诉教授不用担心,这是《华尔街日报》给我的稿费,是已经兑现过的债务承诺,结果周围的人都大笑。

《华尔街日报》给我的稿费支票
与会期间我那关于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理论阐述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机构提出聘请我作研究员去从事相关研究,劝说我留在美国。我告诉他们我爱自己的国家,海外漂流多年的自己对我的祖国有未尽的使命。
我在出发的时候觉得Citizen Diplomacy是一艘助力缺乏的小船,来到波士顿后却得到了美国各个阶层人群的帮助,这是我没料到的。那时的我感觉Citizen Diplomacy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而是许许多多人分享的梦,是一艘迎风展帆志在万里的大船。我从波士顿剑桥开始向美国人民内心的腹地驶去,在洛杉矶给在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工作的人员,在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给投行家、大律师讲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在纽约的地铁里给普通美国老百姓讲Citizen Diplomacy。这次去美国深感中国是如何孤立,整个世界还不适应中国的强大崛起,感到抵触和不安,这对我们国家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继续稳定繁荣是极为不利的。既然我们从宏观层面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数十年的外交关系中仍没有改变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僵化模板性认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现在也许是时候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用Citizen Diplomacy去建立互信打破僵局。当年毛主席说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结果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让我们把全世界放进我们Citizen Diplomacy的海洋中,去收获一个和谐共赢的世界。

在波士顿的最后一个晚上,让我终生难忘。Tom Tiffany请我体会剑桥的酒吧文化,带我把他读哈佛时爱泡的酒吧都逛了个遍,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一夜的大风雪,雪花很粗很沉,风很猛很烈,让人丧失方向感。Tiffany带我去了一个肯尼迪家族经常光顾的酒吧,请我喝了一种那个酒吧最好的酒,那个酒是按杯买的,我们各自喝了两杯。Tiffany说这个酒喝下去口感很好,像是非酒精的可口饮料,但是后劲很足,今晚一定会有神奇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结果第二天凌晨四点来钟,我在一个酒店的大堂沙发上醒来,居然不是我住的酒店,而且我完全记不清我是怎么来到那家酒店的。长这么大,这种失忆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那个酒真的不一般,因为我喝的酒真心不算太多,以前喝过比这多得多得酒,但喝到失忆那还是至今唯一一回。
不一样的洛杉矶和好莱坞
2月1日是我离开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日子。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对这次Citizen Diplomacy能取得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信心。美国人民有着悲天悯人的善良,人文的关怀和宗教的慈悲。一旦他们在你的理念中得到共鸣,(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警觉性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频频有人问我是不是北京特训前来美国做国际公关的特使,为什么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后紧接着来美国?因为像我这样能有效地把准确的信息传达给美国受众,并得到左中右美国人共鸣的中国人,他们见得很少,他们不相信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背后一定是一个团队的行为。),他们会坚定的支持你帮助你,去为你的理念扩大影响,去为你的目标贡献时间和才华,去为你站台募捐。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文化和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他们渴望被代表,他们渴望能与他们共鸣,知道他们的情感赤字和诉求缺失的民意领导者的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美国人劝我在美国留下来的原因,去run for the office,或者作一个活动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认识peter diamond教授及其他许多美国社会精英的原因。我对接下来的Citizen Diplomacy之旅充满了信心。
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我认识了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高级顾问和德意志银行副总裁的James Dix先生,我们谈了关于中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互动的许多话题,还有代表赤字和双边关系赤字,最后话题自然引发到Citizen Diplomacy。期间我们谈到Peter Diamond教授可能进入美联储,James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Frederic Mishkin教授曾是美联储纽约的执行副主席。James对我关于Citizen Diplomacy的理论阐述很感兴趣,让我把相关资料email给他。我们约好在纽约共进晚餐继续我们未尽的话题。

美国西海岸的许多说唱乐巨星最初都是在Compton作皮条客,毒贩子起家的,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r Dre和Snoop Dogg, 2Pac也常在这里寻找暴力灵感
洛杉矶是个和波士顿和剑桥很不同的城市,有种很工业化的大都会感觉,波士顿和剑桥很像古朴隽永的英国城市。我在洛杉矶的主要联系人是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协调员Candace Burnham,所以我住在离她比较近的地方---Compton。Candace知道我是第一次到美国,所以她建议我住在离好莱坞比较近的地方,但是我告诉她:“我最想见的风景还是像她这样的美国人的内心世界。”熟悉hip hop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西海岸的许多说唱乐巨星最初都是在Compton作皮条客,毒贩子起家的,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r Dre和Snoop Dogg, 2Pac也常在这里寻找暴力灵感。不过来到这里感觉街区还是比较平静的,没有那种电视上看到的帮派云集的感觉。还有一个比较震撼的地方就是,波士顿和剑桥正笼罩在冰雪风暴之中,而洛杉矶却完全是一派夏日感觉,阳光温暖慷慨地洒满大街小巷,洛城人穿得非常清凉,非常时尚,非常有风格,与我在英国时听到的美国人不善穿着,身形走样的形象完全不同。洛城人很张扬,很性感。我把这点感受放在了我在公共外交中心演讲的开头,全场人大笑,大家都非常为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加州而骄傲。然后我告诉大家洛城是美丽的,但陈腐旧见(stereotype)是危险的和富于欺骗性的。中国和美国在2010年有超过3000亿美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而在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上我们还是停留在陈腐旧见(stereotype)和冷战思维上,两国在以货币为单位的交流上和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我管这种不平衡叫做双边关系赤字),这就决定了我们两国以后的关系将在互信缺乏的基调下继续在贸易,货币等各个领域的利己博弈和冲突的态势,就像两个人维持着一个表面握手,背后藏刀的姿态,也即是博弈论中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现象。我的听众中有一个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人员,他说五角大楼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充满了不确定的焦虑,所以建议白宫进一步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付这种挑战,这对奥巴马政府以经济为中心,致力消减财政赤字的执政承诺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和负担(两年以后,奥巴马政府果然启动了遏制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我又指出这种双边关系赤字还会为两国过度的民族主义提供滋生土壤。贸易保护主义和茶党兴起都不是偶然。一旦这种过度的民族主义的运动对政策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后果将不堪设想。贸易战,货币战,军备竞赛甚至是战争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在官方沟通渠道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公民应该尝试去弥补这种双边关系赤字,而不是坐等危机发生,因为危机中会有无数中下层家庭的生机受到牵连,作为有知识有能力的公民,我们应该去在微观层面上做些努力。这时候有人问我:“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去中国工作,学习和旅游,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来美国做同样的事,这算不算是一种Citizen Diplomacy?”我说:“教育和旅游都是一种服务产品。我们不但应该鼓励两国人民消费彼此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更应该鼓励他们消费彼此的情感,文化,思想和观点。这种在经济上无限紧密,在情感上十分遥远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经济联系其实是脆弱的,容易破碎的。”又有人问我:“中国缺乏freedom of speech,这对Citizen Diplomacy开展是否不利。”我说:"自由是相对的,比如说你的邻居天天晚上派对到天明,吵得你睡不着觉,你睡觉的自由和他派对的自由之间有矛盾,最后是不是要在不同的受众群体的自由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了这种平衡你可能会投诉,叫来警察。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方式和美国不同,不代表中国就不自由。我Citizen Diplomacy的活动受到了国内许多最大媒体的报道和提倡,这没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化和社交网络的今天,公民意识的崛起是连政府都必须认真审视,引导,鼓励和利用的现象。林肯总统在148年前号召我们建立一个"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政府,今天我们必须用我们公民的意识和行动去实现它。“至此我的演讲在一片掌声中结束,我知道林肯总统对美国精神的巨大感召作用,用他的话更能和美国民众产生共鸣。
演讲之后Candace给我引见了公共外交中心的副主任Naomi Leight女士。她告诉我美国民众对Citizen Diplomacy参与度很低,他们没有这种紧迫感,也没有这种使命感。公共外交缺乏清晰的理论框架和诉求结构。于是我就把自己对于Citizen Diplomacy的理论认识对Naomi作了阐述: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如果能把它们量化,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政策调整依据,也能成为向公众宣传的共识平台,提高公众的危机感和参与感。Naomi对此提法很感兴趣,提出我可以来他们中心做研究学者。但我不想Citizen Diplomacy只成为象牙塔里的一个东西,一个精英层的东西,我想使它成为一个来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公民运动。于是我问Naomi公共外交中心能否帮助中国展开Citizen Diplomacy运动,Naomi说他们中心是一个智囊机构和研究实体。Citizen Diplomacy的实际开展由美国Citizen Diplomacy中心主管,他们能给我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我请求Naomi介绍我认识一些Citizen Diplomacy中心的管理层,结果我认识了位于华盛顿的Citizen Diplomacy中心联络主任Diane Rasmussen,我们将在以后商讨帮助中国展开Citizen Diplomacy的可能。
在洛城的五天我没有去看一次风景,没有去看好莱坞,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日程排得满满,我想来一次美国不容易,得尽力为Citizen Diplomacy和保护中下层人民就业免于贸易争端威胁做一些事。
就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研究问题,我应Naomi的引荐拜访了南加州大学研究公共外交的Jay (Jian) Wang副教授。他是公共外交和国家品牌(Nation Branding)的研究专家。在见Jay之前,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历,发现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孔子学院和软实力。我们从中国在时代广场的国家品牌广告谈起。从胡锦涛主席访美前的1月19日到2月14日,这段广告在时代广场最显著的位置,每天播放300次,总共播放8400次。我问美国人对这段广告的感受是什么。Jay说这段广告打破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很多陈腐旧见,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有内涵有深度,有才华和强大自信的一面。但是花费颇巨,性价比还有待观察。特别是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强大的一面,但是他们不知道强大的中国将会为亚太和平,人权改善,和贸易平衡承担什么养的责任,因此会引起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因为美国人强大惯了,中国的崛起和出手阔绰让他们很不习惯。我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所以不必太考虑性价比的问题,只是国家形象毕竟不是可乐和耐克鞋,中美两国人民的互信和友谊是很难通过新闻发布会和电视屏幕产生的。在全球化,facebook,手机普及和国际旅行越来越便宜的今天,我们应该鼓励各国人民直接互动,一起面对挑战和冲突,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友谊和互信才是真实的,牢而难破的。Citizen Diplomacy可以使外交人性化,可以弥补官方渠道无法弥补的互信缺失。最后我们一起探讨了量化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可能性。Jay说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和代表赤字很难量化,参照系也不好找。南加州大学的交流学院对这种研究会非常有兴趣,我可以申请来做专项研究。
见了Jay之后,我还拜访了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的院长Clay Dube先生,向他介绍了一下我所做的Citizen Diplomacy活动,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的理论构想。Clay认为我关于Citizen Diplomacy的理论阐述很新颖,值得进一步研究,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月5日,我离开洛城飞往纽约。洛城之行见到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学者权威,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相应工作人员,并与他们讨论了我那关于Citizen Diplomacy的理论构想:双边关系赤字和代表赤字。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在美国决策层的推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纽约后,我给国务卿希拉里写了一封提倡Citizen Diplomacy以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并在Hostel附近的邮局寄给了她,是的,我没有疯)。白宫的政策制定非常仰仗于各个领域里的学者权威,南加州大学的交流学院里许多教授都曾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顾问咨询,所以Citizen Diplomacy要影响决策层,就必须有相应的理论建设。
不是《欲望都市》里的纽约
2月5日,我告别阳光明媚的洛杉矶,飞到纽约的寒冬里。

我住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纽约国际青年旅馆,离中央公园只需走10几分钟,也就是著名的upper east side---美剧里热播的那帮"gossip girl"还有“Sex and the City”里的那四个时髦女郎出没的地方。这里有很多高档饭馆,私立学校和著名的博物馆。这里号称是纽约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也是全世界富人最集中的地方,人均收入接近十万美元。不过我住的这个青年旅馆却很便宜,和八个人住一个小屋,每天只要42美元。
在纽约我主要想拜访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的朋友。我们都是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因为加入了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论战而认识。和西方人辩论可以讲道理,但是道理在他们眼里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好的口才固然可以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但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在那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数据沟通,特别是用他们自己官方的数据,这样他们一般会通情达理的接受你的意见,要不就是歇斯底里的抓狂,原形毕露。所以在谈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我从美中商会,商务部,财政部,国会预算委员会,劳工部等美政府部门网站获取以下几方面数据:美元汇率变化和美国贸易逆差的关系,美国联邦债务的偿付结构,美国的国内需求与美元汇率的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结构,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美国出口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上的竞争性,中国占美国出口的份额,美国财富创造和就业创造之间的对称比较,美国就业创造的主要引擎。然后以数据为基础和他们对人民币汇率与美国财政赤字,与美国贸易赤字,与美国失业问题的关系展开讨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发现说服工作容易很多,数字是中性的,非意识形态的,不会伤和气。而且西方人很钦佩能从枯燥数据里讲出深刻含义的人。
我先拜访了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主编助理David.Feith先生。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就是他负责编辑的。我们谈论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很敏感的谈到了人民币会不会跌破1美元6块人民币的关口,我告诉他这取决于中国政府现有政策对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控制成效。我还具体给他介绍了一下中国经济泡沫的情况。他问我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看法,我说美元不能持续这样弱化下去,美国天文数字的债务问题除了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再融资偿还外暂无他途。他又问我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值货币的可能性,我说这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全球产能过剩,仍是买方市场,中国转型为(贸易顺差相对较小,甚至趋零趋负)消费大国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值货币的必要条件,而且中国黄金储备量不足,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和南海争端诸国关系紧张,这一切都阻止了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值货币。世界首席储值货币之争中,虎视美元王座的是欧元,远远不是人民币。我最后谈了想成为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的愿望,他告诉我目前比较现实的还是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以后或许有机会。华尔街日报的销量主要来自于北美版,所以我一直渴望成为其北美版的一个专栏作家,专门研究中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互动。如果有可能那将为中国争得相当的国际话语权。在西方,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对执政的影响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一提到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手执“上打天子,下打权臣的亢龙锏”的媒体充满了骄傲的原因。东西方的媒体直接互动太少,大家还在隔墙说话,有专业知识及英文能力的人应该多去这样的媒体投稿。纽约时报曾刊文说中国的学术文章尽是抄袭,言辞中充满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鄙视,所以我们有责任去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去打破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样板认识,这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一步。
我的下一个拜访目标是金融时报首席商业评论员John Gapper。我们讨论了一下中东局势,我说中东之乱是由代表赤字造成的。中东民众对执政的诉求结构和政府的实际所为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向权贵的集中;振兴经济乏力,通胀失业猖獗,民生维艰;国际政策缺乏在美国以色列中东霸权下的独立性,没有保护好穆斯林利益;凡此种种代表赤字缺乏适当的民主言论渠和道加以宣泄疏通。这种个人的代表赤字在全球化,手机普遍,社交网络深入人心的今天很容易整合成一个全民的运动。以前由代表赤字形成革命需要十年甚至是几十年,现在却可以在几个月内发生。这种加速度前所未有,所以代表赤字从过去的一个执政过程中的小噪音变成了今天的轰天巨雷。我们所熟知的民主政体和权力集中的公共管理体制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像一个庞大的恐龙一样不知在这种执政环境巨变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场由代表赤字引发的Revolution。Street Revolution只是这种代表赤字的一个极端例子,更普遍的是像茶党这样的民意代表运动的兴起,(我关于代表赤字的这些观点发表在了美国最大的财经新媒体Business Insider上,7年后特朗普横空天降当选美国总统,正是这种代表赤字的体现。那篇文章可以说是预测到了美国传统政治板块在代表赤字下的土崩瓦解)分散政府的执政权,严重的话会造成政府职能的反应迟缓和局部瘫痪(事实上后来奥巴马政府就陷入了停摆僵局)。John同意我对代表赤字的阐述,但他问我中国是否存在严重代表赤字的问题,中东的风浪会不会波及中国。我说任何国家都存在代表赤字,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巨大,所以代表赤字问题远不如中东严重,而且中东各国同教同宗,诉求结构极为相似,所以代表赤字才极易在彼此间传导,而中国的诉求结构与中东有本质差别,所以不可同日而语。从John的问题当中我还是能看出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John这个问题其实是老布什提出的"和平演变“策略的延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去争锋相对的争论,因为这会踩进他们的“样板化陷阱stereotype trap”中“:一提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进入渐失常态的争论状态,咄咄逼人”。我们可以姑且赞成他们的一些普适理念,不给他们预期中的argument,然后把话题引向期待成果的区域。虚晃一枪,直奔主题:所以我们又谈到了双边关系赤字的问题----美国和中国,美国和中东在以货币为单位的交流(贸易等等)和以思想为单位的交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大家忙着互取利益,却难得有闲暇加深彼此情感,文化和民族性差异的交流,每每用冷战思维和样板模式看待彼此。这种双边关系赤字也就是中东局势死结难解,中美暗战冲突频频的一个重要原因。外交在宏观上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微观上作出努力,大力发展Citizen Diplomacy,使各国人民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隔阂,做深度交流,共同面对挑战,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建立互信和友谊。只有这样才会避免重蹈后危机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覆辙,维持和扩大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成果。而且在交通便利,手机普遍,社交网络触手可及的今天,Citizen Diplomacy也是一个成本有效性很高的解决方案。”John对我的代表赤字和双边关系赤字的提法很是赞同,鼓励我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西方精英交流的时候,以学术理论为平台探寻解决方案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因为他们很尊重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Misako Hida对我的的人物专访
之后我又接受了我的好友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Misako Hida的人物专访,这是Citizen Diplomacy的一个极大成就,在西方最权威的核心媒体上宣传Citizen Diplomacy。其间我遇到的了两个最棘手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问我对钓鱼岛争端的看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明我所宣传的Citizen Diplomacy和中国政府的说客有什么区别。关于历史遗留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们是否应该争锋相对,踩进他们的“样板化陷阱stereotype trap”,这种对峙是否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如果不能,我们可以在不出让主权的前提下,搁置争议,寻找合作而不是对峙的可能。因为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对峙解决不了历史遗留问题,而武力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峙不是首选,会孤立自己和扩大恐华市场。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日之间的争端很多都是基于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几届政府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去解决。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在缺乏互信和彼此仇恨的前提下顾步不前,我们应该鼓励中日两国人民更多的直接互动,加深对话,去在政府不能的地方建立互信打造桥梁,培育互信和鼓励合作。要不然两国的民族主义对立会愈演愈烈,威胁两国的长治久安和贸易繁荣。”至于我这样的人才应是政府说客一说,我觉得有必要让她知道中国有“士人虽穷困潦倒仍忧国事”的传统。我问她知不知道中国有蚁族。我自己就是个蚁族,连买房娶媳妇都实现不了,我所代表的正是这个没有金钱也没有实力去负担说客这种奢侈品的中下阶层。这是个在两国相争中最易受到伤害最脆弱的人群,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我和Misako讲起了那个因为贸易争端失业而毒死全家的农民工兄弟的故事。她知道了在东西方硝烟弥漫的贸易争端的背后是无数个破碎家庭的不幸,她手中鼓吹贸易战的笔也可以杀人。
Misako很同情我的处境,她告诉我在西方媒体一般她不能写太美化中国的文章,管理层不喜欢这种东西。可见西方媒体是对中国样板化思维的最顽固的堡垒。关于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因为”恐华论“和”丑华论“有利于卖报纸。Misako告诉我她和虎妈蔡美儿(Amy Chua)聊过,其实华尔街日报那篇让她名扬天下的专访中有很多是曲解其意,刻意制造的效果。我通过主动地去和西方的媒体人接触,发现他们也会像朋友一样和你开诚布公的交流,也会给予你同情理解和帮助。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传媒人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传媒人意识形态的堡垒过于森严,互动太少,缺乏交流。我们应该大胆的把手伸过去,去和他们做朋友,去通过直接接触了解对方,而不是道听途说。
我交了很多西方媒体的朋友,很多人说我应该当心,不要被他们利用,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给予我的都是理解支持和帮助。我用普适的价值观,严谨的学术思想,悲天悯人的人文理想,对意识形态对立的化解,对合作互助的善意和渴望去拥抱他们的不同,承认自己的不足,展望我们能共同取得的进步。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热诚也是一个很能感染西方媒体人的思想。和西方媒体人打交道确实不容易,因为对中国之不信任以他们为最甚,但是为了逐渐消除东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培养稀缺的互信,特别是争取国际话语权,我们必须努力去和他们沟通,交流,合作,建立起工作的友谊甚至是私人的友谊。做以来很难,但长期坚持必有收获,这也是Citizen Diplomacy最能发挥威力的一个领域,需要艺高人胆大的国人踊跃的加人。
纽约并不是美国
纽约的地铁非常发达,每走一两分钟就有一个地铁站,而且纽约的所有地方一般都是以大道(avenue)和街(Street)的名字命名,大道(avenue)和街(Street)一般又以数字命名,就像横坐标纵坐标一样精确,所以在纽约问路和交通都十分简单和方便。
有一次我在地铁上听到有两个纽约的职业女性在谈论他们孩子学校里的一个人,他是中东的阿拉伯人,但是很多关于阿拉伯人的格式化描述放在他身上并不相符,所以有些时候要小心别让自己和孩子跌入陈腐旧见(stereotype)的陷阱。我意识到陈腐旧见(stereotype)是阐述双边关系赤字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是一个很好的和他们谈Citizen Diplomacy的机会。于是我插入到了他们的谈话中。“你们所说的陈腐旧见(stereotype)问题很有意思,也是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他们以为我是纽约的一个大学生,遂问我在哪个大学读什么专业。我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是大学生,我是来美国做Citizen Diplomacy的一个中国经济学教师。
“美国每年要向阿拉伯世界购买上千亿美元的石油,这种以货币为单位的交流是巨大的,可遗憾的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思想交流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就叫双边关系赤字。这是恐怖主义横行和美国中东政策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双边关系赤字的弥补,官方外交这种宏观方式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最有效的,所以公民应该去做一些微观的努力,也就是Citizen Diplomacy,鼓励两边的人民除了消费彼此的物质财富之外,也去消费彼此的情感,文化,思想和观点。”
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一个朋友每年都在加沙地带组织一个夏令营,有以色列学生,巴勒斯坦学生,美国穆斯林学生,基督教学生和犹太学生参加,大家一起面对挑战,一起解决问题。“这就是Citizen Diplomacy。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有时候面对的生存问题,诉求问题和选择问题是共同的,我们在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上所遇的障碍和认知缺失上也有共同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共性中共同面对和突破我们的困境,这样一个面对面手牵手的过程将有助于消除我们彼此间的偏见,加深彼此的理解和互信。这样的民相亲的效果是上层建筑中的官方外交所无法浸润的微观角落。”我告诉他们我很赞赏他们的朋友的勇气和做法,觉得她是个很了不起的Citizen Diplomacy家,很有远见。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过中国,中国的人民很友好热情,中国有很多很美的地方。我告诉他们在享受中国的美食和旅游快乐的同时可以去认识一两个中国朋友,带着 stereotype去和他们交往,然后检验一下这些stereotype的真实性,去了解他们的宗教观,自由观,和牵动他们喜怒哀乐的东西。他们会看到一个长城山川和江海美景之外的中国,这个中国的美会更深刻更鲜活更饱满。而我在美国也会做同样的东西,不但在美国做一个称职的旅行者,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买东买西贡献我的消费力,而且会用心消费美国人民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这里我们都会心的笑起来,他们知道我是在拿困扰他们经济复苏的疲软无力的国内消费打趣。
纽约确实是一座世界之城,纽约人对新理念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而且人口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有海外体验,对一个像我这样充满理想主义的中国activist能很热情的接受,对充满公民意识和世界主义色彩的Citizen Diplomacy理论也很乐于理解,可是纽约是纽约,纽约只代表纽约。你甚至可以把美国分成纽约和非纽约,通过纽约去了解整个美国是危险的,就像通过巴黎去了解整个法国一样。比如我在和一个费城人交谈的时候,他居然问我为什么我选在胡锦涛主席刚刚结束赴美国事访问的时候访美,我能从他心领神会般的笑容中读到他的意思:我是北京国家品牌战略的一个部分,肩负着秘而不宣的使命。可惜的是我无法成为他诡异的洞察力无比准确的证明,我之所以选择2月18号访美是因为那是我学校寒假的第一天,仅此而已。美国虽然是影响力覆盖全球的超级大国,可与之严重不对称的是美国民众匮乏的世界主义认知。我在美国呆得不久,所以无法深刻理解造成这个现象的深刻原因,但肯定和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关:过于围绕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缺少对其他文明和价值观的思考。这样一种教育会造成美国人对外认知的许多盲点,我们一直期待华盛顿来改变这种现状,可是等待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所以与其坐等其成,不如一对一的去和他们的交流,也就是展开充分的Citizen Diplomacy。
这就是我从地铁外交中获得的一些体会。
纽约不光是世界之城,也是几乎所有北美最大的华人媒体所在地。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Citizen Diplomacy之旅影响颇大的几个人。《星岛日报》的总经理何力和记者荣筱箐,凤凰卫视的庞哲女士,《世界日报》的谢涛先生和美国中文电视的边令晶小姐。何先生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要对Citizen Diplomacy进行报道的人,之后由荣小姐对我进行采访。在和何先生的对话中他得知我要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就和我分享了一些和西方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小心说错话被断章取义,越描越黑。这个善意的提醒对我后来帮助很大。我和荣小姐在时代广场的一家星巴克见了面。我们喝着咖啡像老朋友一样的聊着,我和荣小姐聊起了我在英国的艰难时光:出国第二年,母亲脑溢血突发过世,娇生惯养的我因此患了抑郁症,同时陷入经济绝境,像机器人一样的打工,看不到人生的希望,曾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国后父亲又患上脑赌塞重疾,生命垂危,自己如何流泪下跪的去为父亲寻医问诊。工资微薄,咬着牙在零下十几度的黑夜里跑兼职挣钱。说着说着我忍不住的流下了泪。荣小姐告诉我她母亲来纽约后得癌症的事,自己是怎么看着自己最亲的人被钻心的庝痛夺去了生命。“不管生活有多艰难,多不可能,都不要放弃,一点点按希望走下去,总会走到光亮越来越多的地方,去把自己的人生照亮,把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的人生照亮,这种因赋予别人光亮而赋予自己光亮的人是不会在黑暗中走失的."这就是我从这些人生的苦难中学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做Citizen Diplomacy的一个重要原因。
星岛采访之后我见到了凤凰卫视的庞哲女士。庞女士是一个经历传奇的新闻工作者,911恐怖袭击时,全球华文媒体中冒死在世贸附近报导实况的第一人。我们在Avenue of the Americas的凤凰卫视纽约演播中心见面了,见面直接就进了演播室。这是我第一次做电视采访,有些紧张,但我被庞女士专业的状态感染了,自己也很快调整了心态进入了状态。我们谈的主要是我给奥巴马总统写信和给华尔街日报撰稿劝阻中美贸易战的事。能够在凤凰卫视宣传Citizen Diplomacy理论是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庞女士对我的帮助还远不止这些,在她的介绍下,我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证券频道的采访。之后她又介绍我在纽约最著名的一家私人会所Down Town Association里参加了大成律师事务所纽约分所成立的庆祝活动,席间见到了大成律师事务所主席肖金泉先生和许多华尔街的大投行家和律师。肖先生很赞赏我的行为,邀请我即兴发表一个关于Citizen Diplomacy的英文演讲。我已经在公共外交中心,纽约地铁等很多地方讲了关于Citizen Diplomacy的理论,所以这次演讲我驾轻就熟,热情澎湃。我首先给他们讲了我被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经济学家的笑话,我告诉他们中国的资本主义者要远远多于共产主义者,如果一个国家光凭资本主义者的绝对数量就能主导世界的话,那么今天的超级大国就是中国和印度了。所以stereotype里面看人就像哈哈镜里看人一样,笑笑可以是不能当真的。就这样我把话题轻松地引到了双边关系赤字,代表赤字和Citizen Diplomacy。最后指出没有充分思想交流为基础的双边经济交流的繁荣就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越繁荣强大越有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充分加深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思想交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话下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演讲完毕,掌声雷动。又有在场的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侨报》和美国中文电视要采访我关于Citizen Diplomacy的活动。这里要感谢《世界日报》的谢涛先生和美国中文电视边令晶小姐非常辛苦的专程到我下榻的Hostel采访报导Citizen Diplomacy的活动。通过他们Citizen Diplomacy在海外华人社区取得了很大的反响:不管在哪,祖国的困境都会成为自己的困境,想回避逃避是回避逃避不了,护照可以换,但族群的归属是换不了的。国家昌盛,国民自尊,国家孤立,国民自卑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海外华人也能加入到中美Citizen Diplomacy的行列中来。
至此我在美国的Citizen Diplomacy之旅在美国的土地上播下了许多希望的种子。没有争论长短,只是留下了人文的和平的开放的自由的祈愿,人种不同,主义不同,地位不同,但对美好世界的普世祈愿总是相通的。
特朗普已经走了,他的外孙女唱中国民歌的歌声还在回响,而中国真正突破stereotype壁垒走向世界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也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给笔耕不缀,做量化分析苦力的笔者打赏,好让笔者专心做学问,不为半斗米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