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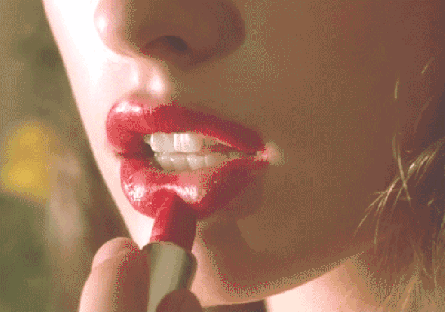
本期背景音乐来自王贰浪的《往后余生》
我认识柳桥时,才十八岁,我们都刚高考完。
我妈开麻将馆,兼供宵夜,她妈是帮工,在后厨煮面、炒面、包饺子、下馄饨,她在县里读书,暑假来省城看她妈,就在店里混,我妈不让我总去店里,那里烟雾缭绕,男人女人光着脚丫,盘腿骂娘,氛围低俗。
柳桥十分适应这种低俗氛围。
她穿背心、短裤,胸脯胀鼓鼓的,十八岁的姑娘,一道深沟,而打情骂俏仿佛天赋技能,男客人都喜欢她,进门就叫:“热死啦桥桥,凉茶伺候。”她白天翻台、拖地、收银,晚上泡茶、倒水、搞服务,我妈花一份钱雇两个人,和颜悦色,偶尔赏她一根雪糕,她跷脚坐在空调下面,细心的啜,边吃边哼流行歌,雪糕沾到手指上,用粉粉的舌尖舔干净,旁若无人……而
爱情,恰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偶遇,我第一次见她,她就在啜指头,表情慵懒,姿势浪荡,令我情窦初开。
我愣愣看着她:你谁啊?
她却像认识了我很久似的,笑了,把吃了一半的雪糕伸过来:“还剩了点儿,你要吗?”
我说:“你认识我啊?”
她笑:“认识啊,老板娘的儿子,周齐嘛。”

高中时我不缺女孩喜欢,但她们都很矫情,春心荡漾、故作矜持,天天守在去厕所的必经之路上说“Hi真巧”,侮辱彼此智商。
我只和班长一起去看过一次电影,她身高快一米七,亭亭玉立,正好到我耳垂,头发清汤挂面,黑得发亮,遮着两边面颊,显得清高而端庄,是很多男生的女神。看电影时,端庄如她,老用胳膊肘碰我,我以为是种暗示,就轻轻握住她的手,结果她跟触电似的抽回去,搞得我很没面子,只好作罢,专心看戏。不一会儿她又用胳膊肘蹭我,我没反应,她蹭得更频繁了,直到电影散场。回去路上,她故技重施,若有似无的碰我,再不干点什么我还是男的吗?
我一把推她到墙上,偶像剧一般低头凝视她的脸,说实话,她长得还行,特标准那种行,眼大大的,睫毛像扇子,樱桃小嘴微微颤动,惊慌的问:“你干吗呀?”我说:“我现在要亲你了,点头yes,摇头no。”她既不点头也不摇头,一双手捂住脸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头也不回的走了,从此再没理过她。
我第一次见柳桥,就觉得她和我们学校的女生都不一样,
她的眼睛像一汪深潭,清,却不见底。她做什么事都是懒洋洋的,好像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包括做爱。
我把她轻轻往床上抱,她用两条细长的手臂圈着我笑,我说,笑什么呀?她说,你劲儿真大,我可不瘦。我说:“你是不瘦,光两个胸都有五斤了吧。”她笑得更厉害了。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对我笑和对别人笑不一样,像个少女,天真无邪,好像把内心的快乐全都留给了我。我亲她,我说,我想要你,行吗?她轻声说:“随便。”
她的身体非常凉,而我的每一寸肌肤都很烫,仿佛进行一场宿命的能量交换,虽然都是第一次,但拥有与生俱来的默契,好像生来就注定要吞噬对方,她的自然卷发湿漉漉散在肩上,在额前贴成好看的弧度,眼神迷离,小麦色皮肤,那会儿正是夕阳时分,余照将她的脸镀上一层金光,脖子上纤细的绒毛和血管清晰可见,连汗珠都璀璨动人……我们没有压马路、没看电影、没有废话,没有铺垫,快速为彼此办了成人礼。
我们一起洗澡,我说,柳桥,我将来娶你,怎么样?她说,还早呢,再说吧。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她眨了眨清不见底的眼,用莲蓬头冲我的脸,咯咯咯笑。
她说:“那你有钱吗?我要嫁有钱人。”

我一直没什么钱,我妈非常抠,大学时我的生活费很感人,柳桥更穷,她爸睡在县城医院里,也许随时会醒,也许永远醒不了。她跟我说这件事时,坐在她们学校操场的双杠上,两条腿晃晃悠悠,显得非常轻松,懒洋洋的,好像在说别人的爸。
我说:“你别难过。”
她说:“不难过啊。”
我们的大学相隔较远,周末她在店里帮忙,没空理我,我经常坐在一边看她,我妈也不让我久待,晚上她和她妈住在店铺后面的隔间里,我深夜从家里溜出来,在窗外学狗叫,叫了好一会儿,嗓子都快冒烟了她才跑出来,捂着嘴、靠着墙,笑弯了腰,说,谁家的狗叫这么响?是不是饿了?我说,你可有点过分了啊。她拉着我,一路狂跑,跑到巷口,四寂无人,抱着就吻,她的吻有绵绵清香,她问:“你想我了吗?”我说:“无时无刻。”
夏天,宿舍的哥们儿,喜欢齐刷刷聚集在主楼下面看妞,她们喜欢在那儿玩轮滑,白花花的大腿,英语系的“方芳”是个尤物,生物系的“小酒窝”笑起来甜死人,他们抽着烟讨论女人,但不谈性,毕竟还没到油腻的年纪。
“他们抽烟的姿势很帅。”我对柳桥说。
她将店里记账的废纸卷起来,递给我,说:“来,装个样子我看看。”
我风骚的眯起眼睛,做作表演,逗得她笑不停,趁我妈不注意,她狠狠亲了我一大口。
我们同时学会了抽烟。那一阵她爸褥疮大面积感染,放弃了治疗,办完后事回来,她妈头发白了一半,神情恍惚,哭得非常凄惨,我妈跟着一块儿哭,麻将馆停了三天业。柳桥说:“哭什么?现在不好吗?我们都知道迟早有这一天啊……”话没说完狠挨了一巴掌,她妈歇斯底里:“我早知道你是只白眼狼,只顾自己,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老了你一样这么对我!”
我们买了一包蘇烟,在无人的夜灯下一人点了一根,她说,你先。我吸了一口,呛出了眼泪,柳桥说,笨,看我的吧,吸了一大口,再慢慢从嘴里吐出来,竟然没有咳嗽,原来吸烟也像别的事情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抱着她,吻她,我说:“你别难过。”她说:“不难过啊。”可是眼泪扑簌簌掉下来许多,打湿了我的肩,过了很久很久,她说:“我爸活着的时候,我们每天可高兴了……这不就够了吗?他怎么会愿意天天看到我哭?”
我们窘迫的谈着恋爱,在路边摊憧憬人生,在钟点房分秒必争,我总是有种错觉,那几年,每一次都那么投入,像是要把毕生的爱做完。
性感是一种基因,均衡的分布在眼神、喘息及事后的微笑里,悸动,不靠低俗的下流话,而是爱意流淌的撩拨。
“你爱我吗?”我问柳桥。
“爱吧。”
“永远吗?”
柳桥笑了,脑袋扎到我怀里,挠我胳肢窝,说,哎呀,你怎么会问这么傻的问题?

“你爱我吗?”
“永远吗?”
我成年后,很怕女人这样问我,她们其实知道答案。爱情里一提“永远”,就叫人喘不过气。
我的第二个女人,是研究生院的院花,留漆黑的马尾,因为束得高,所以眼尾上吊,很媚,她是个超理性的姑娘,学习生活一丝不苟,整个人活在钟表上,六点半起床跑步,七点吃早餐,七点半早读,然后上课,分秒不差。上床更是有条不紊,先握着手一会儿,然后从脸亲起,到鼻尖,到嘴唇,到脖子……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她追了我半年,非常冷静的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那你还非要和我在一起?”
她:“因为我喜欢你。”
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平淡无奇的话,在特殊时刻可感人肺腑,那会儿我研究生快毕业了,即将工作,心灰意冷。每天在篮球场野蛮训练,缓解失恋的暴击,狰狞的张开每个毛孔,企图用流汗代替流泪。
我的柳桥,大学毕业就去了外企,学会了喝咖啡,学会了泡吧,纸醉金迷,穿露到极致的吊带裙,这样的她,我早该熟悉。她从十八岁开始就精通裸露,能给人看的每一寸肌肤都大大方方给人看,因为清瘦,性感而不色情,小麦色的仙鹤腿,光滑的像穿了一层丝袜,闪着微光,锁骨因为太深,分外尖锐,黑暗里咄咄逼人。她开始在做爱时仰着脑袋,从喉咙深处挤出令人心悸的叫唤,分不清是难受还是舒服,令我无所适从,而她给我的笑,跟别人都一样,在应该笑的时候笑一下,在应该叫的时候叫一下。有次,情到深处,我感到难过,我在她耳边问:“到底欠了你什么连做ai都让我难过?”
我们同居,她租了非常奢华的一居室,租金花掉一大半工资,阳台上养名贵的盆栽,却从不记得浇水,我在台历上做了记号,按时浇水,独自等待花季。茶几上三三两两摆放着最新的时尚杂志,它们教会柳桥种睫毛,化咬唇妆,把脸瘦成锥子,穿尖跟凉鞋,将脚指甲涂成艳红……
我有时候在学校住,周五回家,煲一锅排骨,可她要减肥,不喝。我开始做家务,把衣服扔进洗衣机,等至夜深,有时是凌晨。有一次,接到电话去1912椿树右酒吧接她,她的同事个个跟她一挂的,戴浮夸的耳环,项链满钻,她醉醺醺说:“这是我的同事宝歌莉,这是我同事卡缇雅……”说完哈哈哈哈放肆的笑,我跟傻逼一样说:“哦,你们好啊,我叫周齐。”她同事也跟着放肆的笑,说:“你哥好帅哦,又可爱,给我做男朋友行不行?”——嗯,我在她手机里名字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哥”。
她伸手拍拍我的脸,问:“你肯不肯呀?”牙齿整得比麻将还齐,炫白耀眼,可以为牙膏代言了,笑容璀璨,然而陌生,像是另一个人。
回家激烈争吵,她拎着甩干水的外衫咆哮:
“周齐,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洗涤方式叫干洗吗?”
“你知道我这件衣服什么牌子吗?”
“你知道多少钱一件吗?”
“你知道我们之间现在一大堆问题吗?”
“你真的爱我吗?”
“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吗?”
……
我:“知道。”
她:“你知道什么呀?!”
我顿了一下说:“知道你爱钱远超过爱我。”
她站在那儿,捂住了胸口,像被我一刀扎穿了心,然后眼泪扑簌而落,继她父亲死后在我面前第二次哭,跟第一次一样伤心。
我:“为什么哭呢?”
她:“对不起。”
我:“分手吗?”
她沉默,我们之间谁也不会轻易提这两个字,提了就都懂了。柳桥和别的女人不同,虽然那会儿我还没跟别的女人好过,但我知道她不一样,她很坦率,一点也不作。她不闹,不会拿“分手”试探谁的爱,她不用试探,她知道我爱她,入骨。
我不等她回答,摔门而去,夜里冲冷水澡,发了两天的烧,凌乱的梦,支离破碎,浓情时的场景无序组合,像一部用力过猛的烂电影。第三天,我清醒了,追我的院花发微信来,两句拙劣的诗:
“若能乔迁你心,我必入乡随俗。”
我突然觉得好笑,一个人笑了半天,回了她两句——
“把爱用尽又何必,此心早已是空城。”
我约柳桥在1912椿树右酒吧见面,她惯常宿醉的地方。她姗姗来迟,妆容精致,拎了一款新包。
她:“为什么约这里?”
我:“有点仪式感。”
她:“有必要吗?”
我静静看着她,她已经换掉了我攒钱送她的细颈链,精致的钻坠吊在锁骨间,像一句带引号的诗,不得不说,的确跟她更衬。
她:“你想好了?”
我:“嗯,你呢?”
她:“我随便。”
我艰难的忍住眼泪,想起第一次说要她,她也说“随便”,那时的她,像刚刚开放的百合花。
那时的随便意味深长,现在的随便就只是随便而已。
我:“行,就让我们随便开始,随便结束吧。”
她松了口气似的:“回头你把盆栽拿走吧,你花了那么多心思,留个纪念,反正我也不在乎它开不开花。”
我笑笑:“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永远都在。”
柳桥也笑了:“永远那么远,我不会去想的,我只要现在。”

我叫周齐。
在我工作第四年的时候,我爱的人嫁给了别人。我参加了婚礼,她穿着一流设计师定制的奢华嫁衣,如牡丹层层叠叠开满花坛,婚纱也别具一格,裙尾由四对可爱的花童牵着,踏着近十米宽的T型水晶台走向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