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宗城
导演
艺术和商业的平衡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得了他,什么都不行。”这是制片人格雷泽(Brian Grazer)对《异形》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评价。他对自己的作品有高度自信,作为一位“作者”,斯科特不满足于生产一部部好莱坞的流水线型科幻电影,他不排斥技术,可技术不可喧宾夺主。

《异形》系列并非斯科特一个人的杰作。《异形2》(Aliens)有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异形3》(Alien³)是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而第四部则交接到编导了《天使爱美丽》(Amelie)的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Jean-Pierre Jeunet)手上。直到《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开启的《异形前传三部曲》,指挥棒才重回开山祖师之手。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剧本,一直以来就只有一个十页纸的概念。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制片人。不过现在,这个项目不会继续了,福斯公司彻底决定不再跟进这个项目了。”
当斯科特冷静地宣布《异形5》陷入停摆时,一切是可以预见的。他不希望狗尾续貂,而是从前传入手,另起一章探讨起异形和太空骑士的起源问题,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也暗合了斯科特的哲学思考,那个经典的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与大卫·芬奇的文艺到底不同,斯科特更愿意做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与其全场只靠一群人类的叽叽咕咕,他宁愿与伙伴开发出异形的新形态,也许它会更残暴;也许它会更有重金属乐的质感;也许......它的脑袋再光滑透亮些,甚至它出生时可以被安全套包裹(在《普罗米修斯》拍摄时,道具师先把异形卷成肉团,塞进安全套,并灌进去很多液体)。事实上斯科特也的确在这样做,《异形:契约》的尺度足够让大陆剪刀手们多剪去十分钟,外太空的殖民,到头来是一场杀戮游戏。
在接受DGA专访时,斯科特回忆起往事说:
“大概3个月之后,有人请我拍《异形》。我接受了。因为我一直对《重金属》上的那些欧洲漫画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怎么拍好,所以我接受了。”
人与异形结合
受争议的“繁殖”和“性”主题
《异形》第一部的定位是惊悚片而非有怪物的Cult电影,为了营造惊悚的氛围,创作团队设计出不少奇妙的设定,比如异形的哥特式重口味模样、形似章鱼与蜘蛛合体的抱脸虫、异形的胚胎植入一个船员并最后破胸而出的情节等。

这个情节是编剧罗纳德·舒塞特(Ronald Shusett)的主意,当时编剧班农(Dan O'Bannon)正苦恼于如何让异形通过某种有趣的方式登上飞船。一天半夜,醒来的舒塞特告诉班农:“我想到一个好主意:让异形钻进某个船员的身体里,它跳上他的脸然后植入自己的种子”。
班农兴奋极了:“我的上帝,就是这个了,我们整个电影就算拿下了。"
在这部倾注班农心血的电影中,繁殖和性是明显存在的主题。异形如何而来、如何发育、如何繁衍下一代?人类在荒原一般的太空中又如何自处?异形对人类的反噬,既是凭借自己超强的体格,也由于它们近似于寄生虫般的繁殖手段。而人类似乎掌控异形的过程,同样离不开对异形繁殖的研究和改造。
在第四部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人与异形的结合体,其实异形本身就充满了性暗示,维罗妮卡(Veronica Cartwright)洞见地指出:“(对异形的设计具有)明显的性暗示,就像巨大的男女生殖器,好像进入了一个子宫里面,那很像内脏。”

《异形》前传电影《普罗米修斯》(2012)中受争议的性暗示。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电影使用了一个聪明的机制来使异形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新鲜感,那就是不断的进化自己使自己的特性和外观都产生变化。所以我们永远不 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具备什么能力…… 当它破胸而出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清楚的他的外形。那绝对是一种强烈的男性生殖器的样子。”当观众看到从人类体内探出头来的小异形时,他们很难不联想起男人的阳具。
《异形》中的太空骑士同样指引观众思考这一主题。斯科特说:
“他可能是一艘太空船的驾驶员,而这艘载有武器的飞船的作用可能是将异形的卵播散在某个星球,然后异形可以利用周围的生物作为寄主来繁殖。在早期的剧本里,巨卵都是被放置在分离的金字塔形的建筑物里。而且,这个建筑物后来被 Nostromo 的船员们发现了,那上面还有雕塑和象形文来描述异形的繁殖过程及他们和人类还有太空骑士种族的不同文化。”

尽管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后世被不断挑战,但性对于人类精神和行为的作用早已不言自明。《异形》系列是探讨人类未来可能的实验场,也是探讨甚至玩弄人类的性本能的典范。破胸者异形对女性身体的穿破刺激起女性对怀孕繁衍的恐惧,尽管班农否认一些影评人的揣摩,但他也直言不讳道:
“人们总是对这个很敏感......这正是我打动观众的手段。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触动他们。我对女性观众并不感兴趣,我的目标人群是男性。我要尽我所能令画面让男性观众加紧双腿。比如同性的侵犯、分娩、在喉咙里下蛋等等所有。”
女性最后都成为幸存者
是女性主义立场,
还是对社会既定权力架构的反讽?
但如果仅仅利用符号呈现性的暗示,你未免小看了斯科特和班农。纵观《异形》系列,女性最后都会成为幸存者,在第四部,抗拒生殖的雷普利(Ellen Ripley),又阴差阳错成为了白色异形的母亲,却也亲手毁灭了白色异形。
而在《普罗米修斯》的结尾,也正是女主角决定寻找异形和太空骑士源流。有观众指出:“(第一部)飞船上的电脑叫作“mother”,而它执行的正是公司,其实也就是“father”的意志。”这到底是创作者的女性主义立场,还是对社会既定权力架构的反讽?
作为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异形同样有自己的分工,而分工衍生出权力的分配。异形女皇(Empress)、卵异形(Xenomorph)、抱脸者异形(Facehugger)、破胸者异形(Chestburster)、工蜂异形(Drone)、信使异形(Runner)、禁卫异形(Praetorian)、新异形(Newborn)等,它们各司其职,维持着异形族群的内部秩序。有意思的是,它们内部偶尔也会有僭越的行为,混杂了人类的基因、由女王异形的子宫直接生产出的新异形就杀死了自己的这位异形母亲。在它眼里,雷普利似乎才是真正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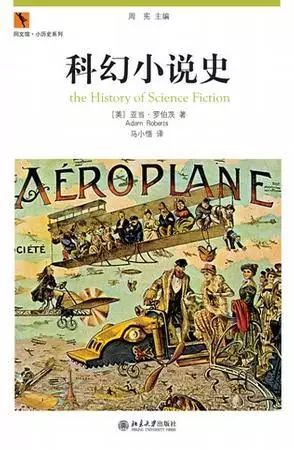
《科幻小说史》
作者: [英]亚当·罗伯茨
译者: 马小悟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
科幻小说起源和发展的批判史:在古希腊的先驱,在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再度横空出世,在18、19世纪的风格流变,以及在20世纪如何登上文化巅峰——以小说、电影、电视到漫画等各种风貌呈现全盛之势。
继承与僭越
被创造者终将要反抗和僭越造物主
继承与僭越正是《异形》系列的又一个暗示。在《异形4》(Alien: Resurrection)的结尾,人与异形的结合蕾普莉和机器人二代科尔(Annalee Call)重返地球——她们第一次见到的星球。她们看到的是一片新奇,而在同一艘飞船的人看来,地球已经是落后陈腐的象征。

人与异形的结合蕾普莉,《异形4》(1997)。
彼时,他们已经能够在银河系自由穿梭,在其它行星建立殖民地、劳改监狱,他们去寻找神,他们能培养异形,他们创造克隆人和机器人,而后者终于有了自己的意识并学会自我思考和创造。蕾普莉和科尔可以说是不同形态的“新人类”,无论是形体还是智慧,还有关键的生存力,她们都超越人类。但人类基于自己创造者的心态仍有高高在上的优秀感,却又因为内心深深的惧怕而抵挡甚至要毁灭她们。
这种矛盾贯穿《异形》系列,也在《普罗米修斯》中体现。“我可以创造你,就可以毁灭你。”但无论是《普罗米修斯》的主人公和人造人还是《异形》中的异形皇后、蕾普莉之子(新异形),乃至蕾普莉和科尔,都被传递这种暗示——被创造者终将要反抗和僭越造物主,在毁灭造物主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超越。
它内在的逻辑是:造物主必然不容许自己的产物与自己平起平坐,而拥有意识的后者也终究不会甘于被支配的命运。波尔·安德森(Poul William Anderson)的《叫我乔》(Call me Joe)也曾探讨这种矛盾,《异形》系列则深入分析了这层矛盾。在这场斗争中,人类终归会被“新人类”取代,即便蕾普莉因恻隐之心或其它原因选择自我毁灭,终究会有新的新的蕾普莉出现,在那里人类旧有的伦理法则都将成为破铜烂铁,弑父弑母、无限交配、机器与新人类欢愉等都会成为无需惊奇的常态。而最初,也就是人类的创造者要面对这一切,“新人类”与最初的创造者必将碰面。
在《异形》系列中,人类大胆开拓宇宙的进程,像一个寻根的过程。人类好奇自己从何而来,好奇茫茫宇宙是否存在所谓的造物主,人类那些大胆的星际冒险和殖民,最终回归到那个古老而经典的主题——认识你自己。生之为人,并非一出世就掌握自己的全部信息,不但不知自己存在的本质,也不了解自己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好奇心和竞争欲让人类不满足于困顿蓝色地球,也让他们在面对解惑的蛛丝马迹时激动不已。于是,在《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中,女主角毅然踏上寻找“主”的孤独之旅。

《异形:契约》(2017)。
营造颤栗
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的焦虑和恐慌
《异形》系列也反映出人类对于特定生存状态的焦虑和恐慌。如今的观众也许很难理解第一部《异形》上映时的情境,那是在一九七九年,一段夹在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的日子,人类世界刚刚告别席卷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即将迎来冷战的最后岁月。
美国人酝酿着星球大战计划,冷战的气氛深深嵌入进那一代人的血肉中。当 Nostromo 在黑暗的太空中孤独地航行;当宇航员们在异形停留的洞穴里惶惶不安;当未知的声音在狭长空旷的船舱游荡,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抓住了观众,令观众想起了自己现实的生活处境。《异形》的氛围,恰恰是冷战的氛围,《异形》所营造的颤栗,正是人们对高压生活的焦虑和恐慌的投射。
事实上,在《异形》的世界里,最体现“恶”的不是异形。如果我们暂时放下站在人类一方的先行立场,异形的举动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它们而言,人类是侵入者,所以要打击。比异形更像“恶”的载体的是具有军政府烙印的角色。像第一部中代表军方的船员艾什(Ash),他负责贯彻军方的意志,利用自己的同胞作诱饵来捕捉异形。当影片揭示出航行的真正目的,你会深深地倒吸一口凉气,原来一切的一切本来都可避免,只是利益熏心的军方和企业渴望获得强大的生化武器,于是开启“作死”之旅。
库布里克导演作品
《
奇爱博士》
(1964)。
对冷战氛围的暴露是当时一些电影的自觉行为。比如电影大师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他所导演的《奇爱博士》就源自导演本人对于冷战中核威胁的担忧。而《发条橙》则是一部揭露出强权与个人意志的典型作品,它本质上是对古拉格式悲剧的决绝冲击。
到如今,当冷战的铁幕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回收站,《异形》系列的这层意味也就渐渐淡去。大量同题材影片的承袭,以及投资方的压力,使《异形》系列需要兼顾更多的商业元素,在创新上反而难以企及第一部的高度。所以当我们看这一部《异形:契约》,它就没有了当初的震撼感,观众只是把它但做一部有情怀的怪物电影罢了。
“在太空中,没有人能听到你的尖叫。”可以说,《异形》系列是一部呈现人类对自我身份的焦虑的佳作,也是一个暗合时代氛围的科幻注解。人类看似是地球食物链的顶层,可当人类回顾地球的历史,人类又何尝不会担忧自己的结局。谁将颠覆人类?是更高等的外星生命?还是人类自己?这是一个只有时间能解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