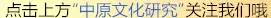
作者:胡承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研究员
摘自:《浙江学刊》
2008
年第
5
期,原题为“封建主义还是
‘
官治主义
’
?——中国古代
‘
官治
’
社会基本特征及对现时代的影响”
官治社会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方式之所以是采取官僚统治的样式,除了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自然条件这一因素之外,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小农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早在春秋末期,以“井田制”为主要形式的大地产制度便已开始解体,私田得以产生,在其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伴随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的技术发展和贵族的逐渐没落,逐步形成中国农业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首要特点是,生产生活条件类同和相互隔离。整个国家的小农,因利益的同一性而无法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和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能形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他人如封建领主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同时,小农的政治影响而产生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局面,因小农的文化意识而不断地得到增强。一方面,小农生产方式的单一性、封闭性诱使农民将意识局限在狭小的血缘、地缘范围,在内部熟人社会里,“差等之爱”构成行为和社会关系准则,而对外部世界则抱陌生、冷漠、恐惧、甚至敌对的态度;另一方面,长期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又造成对外部世界的循从和迷信。当这两个方面的文化意识结成一体面对庞大的国家权力机器时,小农的心理意识是十分复杂的,既有祈盼、又有敬畏、迷信、服从、冷漠、恐惧、仇恨。
官治社会的社会结构
首先,官治社会本质上必然地是扁平化的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治人的官僚统治阶层和治于人的小民百姓阶层,“官——民”二元结构是官治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中国古代的这一社会结构特征是很难直接套用“经济关系——阶级划分”的分析方法来说明的,因为,最大的财主在衙门、官员面前,他也是民,也是小的;反之,官员在财主面前,他总归是治人者。这种关系,从奖褒方面讲,
是父母官与子民的关系,往贬斥方面讲,就是牧与被牧的关系
在民面前,他就是“放牧者”。官治民、民从官是中国古代社会全部社会关系中最为核心和本质的社会关系。
其次,与封建贵族等级制相比较,中国的官治社会的巨大进步在于它超越了直接的人对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而,在社会个体层面上并不存在严格的种姓等级制与贵族等级制,但存在实际的身份等级制。这种身份等级制与职业分类、职层分类紧密相联,士农工商被分别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标识和权利、义务,官员则按职务予以不同的等级品位,享有等级待遇,得轻易更改。
第三,古代中国社会,是政治权力独大的社会,政治权力对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个人私权具有绝对的至上性和操控性,节制甚至规定着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个人私生活领域的活动内容和权力运作方式。比如,重农抑商与盐铁官营;比如独尊儒术与文字狱;比如,“七出”之律与贞节牌坊;等等。
“官治”社会的运转机理
首先,由“官——民”二元结构的扁平化等级结构所决定,官治社会的全部制度安排是按官僚集团的利益要求构筑起来的,官僚集团垄断和控制整个国家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具体分配。进而官僚集团的利益驱动成为“官治”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凡是有利于官僚集团利益的举措都将得到强有力的推行,反之,要么不会被予推行,要么即便推行了亦终将难以真正得以贯彻到底。在“官治”社会里,民众的利益始终是被动的、被赋予的,是以是否有利于统治者官僚集团的利益为转移的。
其次,由于农业社会剩余产品有限性的约束,官僚集团的统治还必须将被统治对象划分为若干等级,并将其中的一些阶层作为统治活动的过渡环节。在思想统治方面,士大夫阶层直接构成这一过渡环节。士大夫们一方面直接宣传传播官僚统治集团的思想意识以俘获人们的头脑,征服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断地依据时代的变化改进、修正既有的思想意识体系以适应统治集团的实际需要。士大夫阶层本身并不直接地属于官僚统治集团,但由于他们生产精神产品的实际作用而成为官僚统治活动的中间过渡环节,同时还成为官僚集团的补充来源,
是官僚统治集团的外围阶层。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官治社会具有局部的社会开放性,并成为具备社会统治集团“亲选”与“贤选”双重选拔机制的社会类型。在社会事务治理方面,则由乡绅、社会贤达构成官僚集团统治活动的中间过渡环节。在中国古代二千多年的官治社会历史阶段,农村、农民一直是官僚集团统治活动的主要对象。“官治”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城市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进行着城市对农村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居住分散,交通不畅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城市里的官僚集团如果要对全国农民直接实行全部的政治、经济统治活动,其统治成本将会变得十分巨大,选择乡绅和社会贤达作为统治活动的中间过渡环节,不仅经济而且更富效率。进而扁平化的“官——民”社会等级结构又具体化为“官——士——民”、“官——绅——民”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三,尽管官僚集团相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是一个利益整体,是在共同治理这个社会。但是由于官位和出身等方面的差异,
这个官僚集团内部充满矛盾,
其中皇帝与官僚、官僚个体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始终左右着“官治”社会的统治活动。首先,在皇帝方面,因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且他又处于最高领导的位子上,通常主观上非常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即把个人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与整个国家利益的增长相等同,在追求巩固统治地位的同时谋求整个社会的利益,
并将整个官僚机构和官僚集团看作是自己实现政治与经济统治的物质器具。反之,
官僚机构及其官员们在巩固统治地位方面虽然与皇帝有着极大一致性,但他们的“工具性”地位却会促使其产生机会主义投机,极易将自身的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整个统治集团的整个利益之上,甚至为了局部利益、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进而形成最高统治者与某些官僚及其团伙之间的斗争,且这种斗争影响甚至决定整个统治方略尤其是改革时期政策的实施和成败(如王安石变法)。
第四,“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动员。君权神授、政权神授是传统社会统治集团为自身而作的本体论辩护。“天下为公”的王道仁政学说,一方面赋予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的统治让人目眩的道德光环,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满足了小农对统治者的政治幻想,以天然地成为历代统治者竭力加以宣染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天下为公”有二个核心涵义:一是说天子富有四海、皇帝统治是最大的公道;二是说皇帝统治是为了公众百姓的利益。显然,这套“官治”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辩护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它从根本上遮蔽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本质特征。
第五,法度的原则性与官员的自由裁定权。二千多年的帝国社会是一个有法制的社会。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地域广阔而又复杂,政令和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社会事务及其复杂性,故此必须赋予官员处理政务、事务实际上的自由裁定权。这就形成通常所说的“经”(包括儒学经典、当朝政令法律)与“权”(权变、变通、通融)的矛盾关系。在“经”与“权”的矛盾关系中,相对说来,在王朝初期“经”的严肃性能够较好地得到保障和贯彻,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自由裁定的沿袭和累积,“经”的严肃性越来越削弱,而官员的主观意识却愈来愈在政务、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得到反映,到最后,所谓纲纪颓废便成了集中写照。在“经”
与“权”的矛盾双方地位转变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要害问题在于:官员主观意志的加强是与官僚集团和个体特殊利益的不断加强结合在一起的,进而为官僚集团和官员掠取特殊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并因此而造成吏治败坏。
“官治”社会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