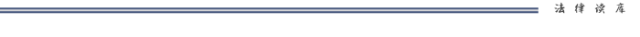近日,由腾讯新闻出品的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第二季上线,第一期许知远采访了马东,在网上引发热议。何以一个视频访谈节目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诸多讨论呢?正是因为许知远和马东的所谓“尬聊”,刺痛了观众,从侧面印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
跟许知远老师谈谈粗鄙
来源:押沙龙yashl
马东和许知远的对话这两天在网上很火,许知远因为这个视频在网上被骂的鼻青脸肿的,“许知远你离采访马东还差十个朱军!”弄得我都起了好奇心,特意找来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想看看那十个朱军往那儿塞。
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在审美上,其实我是能理解许知远老师的。老实说,《奇葩说》我也看不下去。它里头那些红头发绿脑袋的造型我就受不了,而且里面的人说起话来都很激动的样子,也不符合我的审美观。我的心情跟许知远老师是一样的,不光跟许知远老师的心情一样,跟中老年人看见穿着麻袋服、留个鸡冠子头的年轻人的心情也思一样的:这都什么呀?太粗鄙了!
但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偏见。我能理解许知远的焦虑,甚至我认为这种焦虑里有一些真实的力量,但是我依旧认为他的逻辑理路是不清楚的。我不想加入骂他的队伍,因为队伍实在太拥挤了。我只想对事不对人的谈几个道理。
过去的时代有多精致?
觉得过去的文化非常精致,我觉得这是个误解。我们看过去的文化,其实只看到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比如唐诗。可是唐朝认字的人是很少的,会写诗的人更少。唐朝有六千多万人口,能够阅读诗歌的人最多只有三四百万,能够写诗歌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万,悲观估计可能只有几万。我们都说唐诗如何如何,其实能够背出三十首以上唐诗的人,在唐朝的比例肯定比现在还低。
那消失的六千多万人哪里去了?他们的文化在哪里?
他们是无声的。他们的文化像尘沙一样在历史上消失了。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无声的中国》。其实古代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就是无声的。他们好像哑巴一样无声无息,没有人知道他们想过什么,没有人关心他们喜欢什么。
在历史上,文化的雅致就是以大多数人的沉默的代价的。如果让大多数人发声,文化一定是喧嚣的,一定是不够精致的。如果唐朝老百姓都有机会发声,都有机会选择文化节目,许知远老师认为他们会选择什么?他们会看杜甫的《登高》诗朗诵,还是看魔术杂技郭德纲?
全民高雅的时代从来不存在。
如果让看《奇葩说》和《康熙来了》的观众统统沉默,只留下许知远这样的知识分子站在文化舞台上,这个舞台当然会看着雅致很多。许知远老师家肯定一屋子书,肯定还知道柏拉图和哈贝马斯,头发还那么艺术的蓬蓬着,当然是很精致了。
可是,凭什么?
缺乏精致,是粗鄙的错儿么?
许知远老师说起梅兰芳,马东说梅兰芳就是现在的周杰伦,许知远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其实梅兰芳在他那个时代,真的是那么难以企及的高雅和精致么?事实上当时的文化人很多相当鄙视梅兰芳的。鲁迅就嘲笑说梅兰芳眼睛那么凸、嘴唇那么厚,还腆着脸演什么林黛玉?沈从文也觉得梅兰芳演《贵妃醉酒》,“在一丈内看他作种种媚态,”穿的衣服也不伦不类,毫无唐朝空气,看着恶心。而这样的贵妃醉酒还是改良版的,以前的《贵妃醉酒》穿着紧身衣服抚摩自己,是有名的“粉戏”,难道不粗鄙么?
许知远老师还提到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当然是绝世天才,但他的戏剧里头粗鄙的地方还少吗?他的剧本里到处都有猥亵之处,就像《哈姆雷特》,伟大的悲剧啊!哈姆雷特跟奥菲利亚对话的时候,朱生豪翻译的是“我可以把我的头枕在您的膝上吗”,其实这就是双关语。你以为是什么头?就是指小弟弟啊。就是哈姆雷特说我的小弟弟能不能往你那里插的意思啊!就是这么黄。没办法,观众爱看,莎士比亚也爱写。
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就是喜欢黄段子,喜欢暴力场面,俗气程度比现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莎士比亚有个剧本《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里头杀人的,砍手的,到处是暴力场面,简直是不堪入目。那又怎么样?莎士比亚还是一个精才绝艳的大师啊!
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夜,那可是诞生了乔伊斯、伍尔夫和奥威尔的时代啊。可奥威尔本人是怎么说的?奥威尔在一个书店当过店员,根据他的观察,被租出去的书基本都是伊索尔.戴尔、瓦维克•迪平、杰弗里•法诺尔的廉价小说,那些破玩意儿跟现在的玄幻小说没啥太大区别。奥威尔说有位读者“每年读过的垃圾书能铺满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用许知远先生的标准,这些普通人的口味也是很粗鄙啊。可这并没有妨碍乔伊斯他们的诞生啊。
可是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产生足够精致的文化,那也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精英太过无能,而不是因为大众太过粗鄙。
就像许知远先生觉得现在没有精致的东西,那他应该做的事情是自己开始创作精致的东西,而不是抱怨《奇葩说》太粗鄙。没有人拦着你去做啊。如果许知远老师真有莎士比亚的能力,写出一部《仲夏夜之梦》或者《暴风雨》那样足够牛逼的东西来,一定是有观众看的。那么,《奇葩说》那样的节目再粗鄙,又何碍于他的创作呢?
许知远老师到底在担心什么?
假定世界上确实存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分(事实上这种区分是含糊和变动的),那么许知远老师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呢?
他担心的是大众文化太过粗鄙,会影响到精英文化的精致?可是就像马东说的那样小群体始终存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有一批关心形而上事物的人,始终有一批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胜过盗墓笔记的人,他们始终没有消失,始终等待着你去触动他们、吸引他们。
或者他觉得大众文化本身就不该这么粗鄙?那么就像我在上面说的,无论是唐朝的中国人,还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他们都不会像许知远先生想的那么精致。现代的中国人也许粗鄙,但我不相信他们比那些古代的普通人更粗鄙。但是莎士比亚不就是从那个粗鄙时代里诞生的么?
那么他担心的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原来那些人是无声的,现在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他们的声音又被许知远先生听到了。而在美好的过去,他可以装作这些人不存在。
就像在听交响乐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隔壁的大厅里,居然有人在看二人转,这多让人恶心啊!
什么是粗鄙?
事实上,真正留心一下文化史就会发现,经典东西往往是产生在混乱喧嚣的时代,产生在泥沙俱下的时代,产生在创造力旺盛,粗鄙和精致混杂的时代。就像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就像马克吐温所处的镀金时代,就像兰陵笑笑生所处的话本小说时代。处处强调精致、鄙视粗鄙,往往是文化贫血衰弱的征兆。
而且让我们再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粗鄙?《奇葩说》粗鄙么?我没仔细看过,无法做评价。但是仅仅因为看不惯它的风格,就说它粗鄙,很可能是错的。它可能是俗文化,但不一定是粗鄙文化。它的文化范式是俗的,但是它如果争取在这个范式里面做的足够用心、足够精细,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精致的俗文化。而我们看到的许多经典艺术,都是从这种俗文化里长出来的。许知远老师现在觉得京剧多精致,但他如果生活在京剧刚出现的年代,多半会觉得这是粗鄙的。如果他生活在话本小说刚出现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粗鄙的。
没有什么东西一出来就是精致的。
我们这个时代会留下什么吗?
许知远先生似乎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留不下什么,马东说他这话说得太早了。确实说的太早了。
我并不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我深深的相信,《红楼梦》的价值高于《鬼吹灯》,巴赫的价值高于凤凰传奇,我相信每个时代都应该留下一些美好的经典,留给未来的人类。其实马东也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他说现代人看《奇葩说》,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看莎士比亚,是一样的。这是指观众欣赏这个举动本身,而不是说《奇葩说》和莎士比亚是一样的。但是许知远先生说我们这个时代粗鄙到留不下经典,我就不能确定。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绝对。稍微对历史熟悉一点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我不知道周杰伦会不会在一百年后被视为经典,我不知道三体会不会成为未来的经典,我不知道刘震云会不会成为未来的经典,我也不知道某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艺术家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大师。
许知远先生可能会对这种乐观看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在伊丽莎白时代,大家就觉得莎士比亚是个讨人喜欢的剧作家和演员,如果有人对看客说,莎士比亚会成为荷马一样流传永久的诗人,看客肯定会觉得你脑子有病;在西班牙黄金时代,大家觉得《堂吉诃德》就是一本逗乐的滑稽书,如果有人告诉读者,塞万提斯会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作者,大家肯定觉得这人是傻逼。
有活力文化往往是“粗鄙”的,就像大海的浪潮一样浑浊杂乱,而他“精致”是浪潮过后留下的贝壳。没有这种混乱的浪潮,就不会冲来海底的贝壳。精美的文化总是混乱浪潮沉淀的结果。我们往往会高估过去的时代,因为我们回首过去时代,喧嚣已经消失,混乱已经消失,只留下了一些精美的贝壳,而对这些贝壳的评价,又已经有了定评。
我们这个时代会留下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自己就处在这个浪潮之中,只看到周围的泡沫和海水。这个东西要未来的人们来判断。就我个人来说,我相信这个时代很可能在创造着未来的经典,只是我们身处局中,分辨不出而已。
当然我的判断可能是错的,有可能我们这个时代依旧是一个模仿和追赶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创造的时代。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像许知远先生那样,如此轻易地否定这个喧嚣而混乱的时代,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产生于喧嚣与混乱之中。
是许知远落伍了,还是我们真的粗鄙?
文 | 蒂芗 来源:欧洲文艺评论
许知远和马东的事儿过去好几天了,批评许知远的热潮也有所降温,过去一周冒出那么多批评、指责许知远的文章,有的甚至把他骂得一无是处,读完之后,说实话,内心替许知远感到悲凉(声明:个人不是许的粉丝,也不是马东先生和《奇葩说》的粉丝)。从视频内容来看,许和马的对谈和争论并不过分,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很奇怪会引起这么大争议。
从很多文章来看,对许的批评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是针对许的采访形式和主持风格,他们认为许的采访有过多自我预设,他是带着自己的成见和偏见在对话,而且自说自话,散漫,“自我循环,喃喃自语,像一个拧巴的中年人”。
许这期采访的是《奇葩说》的主持人,而《奇葩说》是一个有较强娱乐性且粉丝众多的节目。有些批评文章,比如阅读量很高的《许知远为什么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 》,其实是不自觉地以《奇葩说》的节目形式和思维来评判许知远和《十三邀》的风格,换言之,表面上看,这是许知远和马东的争锋,实际上在有些评论者的解读中,这是《十三邀》和《奇葩说》的一次交锋。当许知远表现出他与马东在主持方式、思维方式和对时代的认知上的很多差异时,他的对立面站着的不只是马东一个人,而是《奇葩说》的众多拥趸。其他一些文章也基本是以我们之前习惯的访谈类节目去评判许的《十三邀》。
不可否认,从主持专业的角度看,“自我预设”和自带成见是许知远的问题,他的散漫和随性也与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主持人风格不相符,但,他的身份不只是一名主持人,而且他也不是以主持人的事业来做《十三邀》,《十三邀》是访谈类节目,是一问一答的节目,是聊天式的节目,是注重思想对撞的节目,许知远不是一个机器人式的主持,他是一个思想型主持,而且,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有着浓厚公共关怀和问题意识、并对这个时代有着成熟思考的文化人在与访谈对象对话,这是《十三邀》的风格,所谓他带着自我预设去对话,又有何不可?《十三邀》不是《奇葩说》或辩论赛,许知远不是马东和辩手,他不需要每分钟都滔滔不绝,他不需要每分钟都要尽力制造娱乐性或思辨性;《十三邀》也不是《面对面》,许知远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不需要将自己隐身,只做一个所谓客观中立的主持人去引导别人思考和陈述。这种文化对谈的节目,他保留自己的底色,岂不是能更好地映照出对方的色彩么?对于观众来说,为何要纠结于他的形式,只要能从他的内容中有所收获,岂不是就是他的价值。
关于饱受非议的“尬聊”,文人、学者、知识分子之间聊天,不是打辩论赛,也不是上主席台发表演说,有沉默,有沉思,有无言的对视,有笑而不语的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个人曾跟国内某一位老派学者聊天,他可以在沉默中抽三分钟的烟,然后嘟哝一句休谟,再沉思一分钟,给他一串精彩的评价。那时还没有“尬聊”这个相当无趣的说法,跟这种文人学者聊天,两分钟的沉默就是为了那一分钟的精彩,而那两分钟的沉默既是他们审慎思考、准备严谨的逻辑和措辞、组织语言的过程,也能让我们感受文人学者们的言说风格和真实气质(可见《十三邀》采访陈嘉映老师那期为例)。许作为制作方,他完全可以减掉那些尴尬的时段,他完全可以减掉他彷徨、喃喃自语、自说自话、无聊的一面,但恰恰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作为时代思考者和困惑者的知识分子的真实一面,那些尴尬和沉默正是他想要引导大家思考的问题所需要的语境。就像有篇文章里说的,“许知远“入世”的方式,就是去跟那些和他“道不同”的人聊天,把他的焦灼、困惑、不安和异议直愣愣地抛给对方,他知道对方会反驳,会否认,甚至反唇相讥;但他不在乎,他也不会在最后的节目里剪去这些尴尬的场景,因为这些尴尬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尴尬,他从来没打算回避它们。”(骆轶航《许知远、马东和罗振宇,一场中年危机的三个镜像》)
批评许知远的另一方面要更复杂,很多人说他知识结构落伍了、老套了,批评他精英化的立场,指责他总是对时代不满,讽刺他悲天悯人装高贵。
难道这不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么?难道要所有知识分子都去歌颂太平盛世?难道要所有人都说我很喜欢这个时代?难道这个社会还不应该有悲天悯人?
而且,就对批判性立场和所谓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言,想想那些远离喧嚣的学者和思想家,许知远才算哪儿跟哪儿啊。
许知远和马东的这期节目能炒到这么热,不能证明我们对文化的认识有多么深刻,不能证明我们对娱乐形式的品味有多么高级和时尚,不能证明我们多么有现代媒体精神,它证明的恰恰是我们的文化是多么荒芜,是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和认知是多么单一和狭隘。更可悲的是,今天批评许知远的一些文章,还弥漫着一种文革大字报式的语言风格,比如某文章里对许的评语:“猥琐的文化直男”、“极度自恋”、“撒娇和撒泼”、“民科式的中年危机”、“凝固的高傲”、“自慰式的煽情”、“自说自话的前现代僵尸”等,这些戾气十足的词汇,听了有没有后背发凉?如果许知远真是如此,那么这篇文章比许知远更许知远。它甚至比许知远更可怕。
最后,有文章说许知远失败了,他的节目“一直很失败”,个人反倒觉得,许知远是成功的,他采访马东的这期节目也是成功的,这个成功不是指他的节目提供了多么迎合大众、娱乐民心的答案,而是指它们提供了问题,引起了文化困惑,揭开了这个时代的一些伤痕。许知远的这次遭遇也让很多人看到,在言论空间越来越小的今天,狭隘的文化态度是多么普遍,一个习惯了娱乐化的新生代网络社会对注重思想性和批判性的文化节目的接受度是多么有限,多元文化思维在这片土壤上的成长是多么艰难。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