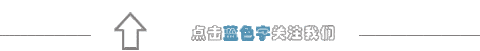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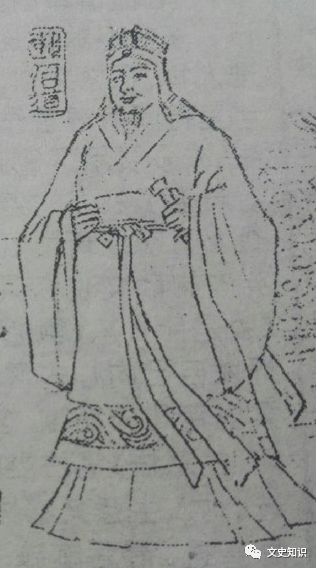
《世说新语·德行》第二八条讲了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
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
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
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
在“永嘉之乱”中为逃难而放弃亲子的邓攸,过江之后,为求子纳妾,却误纳甥女,遂哀恨终身,不复蓄妾。
就篇幅论,“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只是故事主体的背景说明。
故事中他所谓的“德行”,显然侧重他得知自己误纳甥女时,尚属“闻过能改”。
要细说起来,邓攸保存侄子、抛弃亲子,着实异乎常人之情。
原本作为背景的中道弃子故事,却备受关注,甚至衍生出添油加醋的版本:
“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
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
”(《晋中兴书》)当人们侧重对邓攸弃子存侄这一特殊事例的讨论时,也很容易遮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其时其地,邓攸何以非要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
邓攸是平阳襄陵人,和西晋权后贾南风的娘家平阳贾氏是同一个县的小同乡;
贾后之父、西晋佐命贾充,当其领衔伐吴时,担任幕僚长的就是邓攸的祖父:
两家既有乡谊,又有府主——故吏这层时人很看重的关系。
邓攸年幼时父母与祖母便接连去世,与其弟相依为命,以孝友博得声誉,进入贵族社交圈。
虽然彼时已完成“清和平简,贞正寡欲”的个人形象设定,但他的“贞正寡欲”重点是不贪财利,而不包括淡看虚名。
借着拜见贾后亲叔贾混的机会,他就有意展现过自己“具有名士风度的举止”:
尝诣镇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之,以女妻焉。(《晋书·良吏传·邓攸》)
贾混让邓攸判断公案,是想测试邓攸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能力。
邓攸的回应则在姿态上超越了问题本身,避开在具体细节上露怯的风险,这契合大部分西晋贵族不经世务的追求,是一种比较取巧的回答。
贾混“笃厚自守,无殊才能”(《晋书·贾混传》),但喜欢他的回答,于是邓攸娶了贾后堂姊妹,颇历清显。
贾氏集团倒台,他又依靠人设,很快转为新当权者司马越的幕僚。
或许妻子在他眼中渐渐失去价值,因为到了西晋政权崩塌,邓攸选择南奔的时候,在“弃子存侄”之后,还一度抛弃了其妻贾氏:
至新郑,投李矩。三年,将去,而矩不听。荀组以为陈郡、汝南太守,愍帝征为尚书左丞、长水校尉,皆不果就。后密舍矩去,投荀组于许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属还攸。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晋书·良吏传·邓攸》)
李矩也是平阳人,为当时新郑一带的坞壁主,组织对抗刘、石的活动,一度保持较高胜率。
邓攸先投奔他,当然是想依靠有力量的同乡。
李矩也想留他与自己继续共同作战,却导致邓攸无法成功获任愍帝政权的官职。
愍帝政权虽自建立初就风雨飘摇,内讧不断,听起来总算还是个朝廷。
李矩强留,邓攸便抛弃家属,孤身投奔了愍帝阵营的荀组。
这次抛弃的家属,最起码有他的妻室,应该还包括他放弃亲子保下来的侄子。
若是乱世英雄、枭雄,做这样的决策,倒还不足为奇。
但邓攸既非此等人物,发迹又依靠贾氏一族,有难临头如此这般,未免有失厚道。
贾氏在娘家如日中天时成为邓攸的妻子,没有对不起他的记录,到了娘家彻底翻身无望时,先是亲生骨肉被丢在半路,继而自己也横遭遗弃——这个故事,和邓攸误纳甥女为妾,最终哀恸改正相比,又如何呢?
那个时代中原板荡,公主、王妃都可能被掠卖为奴、下落不明甚至死于荒郊。
若非李矩个人修养尚可,始终坚持不劫夺、强占妇女(《晋书·李矩传》),邓妻贾氏的处境,几乎不能细想。
大约在邓攸潜意识里,非但孩子可以再生,妻子也可以再娶。
李矩最终将邓攸家属送还,厚道之心毕竟未泯;
在邓攸,则是一种幸运:
《世说新语》和刘孝标注,不约而同隐去了邓攸妻的身世;
编者、注家,对邓攸也还是厚道的。
若加上这笔,他们的读者,恐怕未必还认为邓攸宜入“德行”一科。
不过《世说新语》之外,东晋初王隐《晋书》、东晋中后期邓粲《晋纪》、南朝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以及唐修《晋书》,则对邓攸在另一串事件上的德行,展开多样化描写,可以说构成了立体声式的反讽。
它们也与邓攸为何弃子有一点点关系,因为这一串事件正是:
为叙事方便起见,我们按照唐修《晋书》的故事时间线,来比对一下相关异文。
邓攸作为西晋河东太守,被羯人武装领袖石勒擒获。
接下来:
邓粲《晋纪》说石勒和他一见如故,还请他吃了顿饭,于是他就留在了石勒军中;
唐修《晋书》则说,西晋二千石以上高官,大都是石勒一贯讨厌的对象,所以邓攸一开始差点被杀,因石勒部下中有与他相熟的亲随,他才得以和石勒一见。
邓粲《晋纪》没有细说石勒对邓攸后来如何,而唐修《晋书》说,石勒谋主张宾曾和邓攸邻居,对他从前的名声印象很好,帮助他得到石勒另眼相待,甚至得到任用,留在石勒军队的车营中。
邓粲《晋纪》说,某次,与邓攸比邻而居的胡人造成失火,并诬赖邓攸,邓攸觉得争不过他,就认了下来,并推说是自己“为老姥作粥”(“老姥”,老妇,或系对他人谦称妻子)而失火;
唐修《晋书》中增加了“勒夜禁火,犯之者死”的细节,矛盾得到强化,邓攸面对诬告则“度不可与争,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
邓粲《晋纪》说石勒采信邓攸的说辞,就放他走了,唐修《晋书》则说,石勒相信并赦免了邓攸,邓攸也继续跟着他,又过了一阵,才脱离石勒部队。
邓粲《晋纪》里因邓攸“不争”,胡人出于感激,送他驴马,还护送他逃离;
唐修《晋书》的故事,没有胡人护送邓攸逃离的情节,但被感动的胡人到石勒面前坦陈了事实,而后唐修《晋书》采用王隐《晋书》的说法,邓攸是自行逃亡。
而且,这个故事里,没提到邓攸那位“弟妇”(也就是他侄子的寡母)下落如何,只是在与王隐《晋书》大致相同的情节(“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
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
度不能两全”,遂弃子存侄)之后,又采用了出自何法盛《晋中兴书》的“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
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
《晋中兴书》说邓攸逃离石勒军队之后“遂渡江”,而唐修《晋书》指出,邓攸在坞壁主李矩军中,被强留至少三年,终于投奔荀组,几番周折才南渡建邺。
 出行依仗图(王陵大墓,甘肃嘉峪关新城出土魏晋墓壁画画像砖)
出行依仗图(王陵大墓,甘肃嘉峪关新城出土魏晋墓壁画画像砖)
可以看出,邓粲《晋纪》塑造的邓攸,至少对东晋政权一以贯之,而唐修《晋书》则显示出,邓攸的南渡过程,是一个不断比对各种政治势力强弱、挑选依靠对象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避难”。
唐修《晋书》的故事里,多出了一个弟媳;
而这个弟媳的出现与消失,对邓攸形象的影响又颇微妙:
她或许因为邓攸拿她顶包而被杀,或许因为邓攸出奔而被抛弃,独自去面对石勒的追究和不可知的未来;
邓攸一家逃亡途中,也无异于放弃了得到弟媳助力的可能性,落得不得不舍弃亲子的下场。
唐修《晋书》中的邓攸,因此形象尴尬:
他原本因为兄弟友悌得到赞誉,但关键时刻却出卖(或抛弃)了弟弟的寡妇,甚至后来还企图放弃孤儿。
虽然故事中他放弃己子的明面理由是为了亡弟、保存侄儿,但这一连串选择也暴露了内心:
他对弟、侄的爱和尊重,其实也深不到哪里。
邓粲《晋纪》中连最初无理生事的胡人,后来都被邓攸感化。
而唐修《晋书》的故事里,并不是没人帮助过邓攸,只不过陆续都被一心追求个人名位的他抛弃而已。
邓粲《晋纪》希望塑造一个得道多助的名士,而唐修《晋书》中的邓攸,必然因其失道而走向寡助的结局。
唐修《晋书》的撰著者们,对邓攸显然已完全不打算继续保持“厚道”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邓攸渡江之后的政治抉择,恰恰向读者证明:
唐修《晋书》中比邓粲《晋纪》多出来的那些不堪,“完全有可能发生”。
邓攸离开李矩,又放弃了他之前心心念念的荀组、愍帝阵营,投奔江东的元帝。
他和东晋高官刁协、周顗有旧交情,得到重用,出守吴郡,入为侍中、吏部尚书,努力重建相对良好的风评。
“蔬食弊衣,周急振乏。
性谦和,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而颇敬媚权贵”(《晋书·良吏传·邓攸》),此时他敬媚的对象是刘隗、刁协等得势的元帝心腹。
王敦起兵战胜元帝,刁协、周顗等被杀之后,他的敬媚对象就成了王敦。
“永昌中,代周顗为护军将军”,“王敦伐都之后,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
过于迅速,姿态也过于难看。
明帝支持者们非常恼火。
即便邓攸后来又想转投明帝,他们也千方百计加以破坏。
在拉锯中,邓攸挨到明帝英年早逝,但在成帝刚刚即位的咸和元年(326),他便死去了,因此不必再接受“苏峻之乱”的考验。
他的侄子为他服了三年丧,随后消失在史册中。
一个以主题词“抛弃”贯穿始终的故事就此结束。
绝大多数被抛弃对象,也像邓攸的亲生儿子一样,不再可能追上来找他。
乱世里从不缺少分道扬镳的故事:
或许因为观念不合,或许因为利益冲突,最终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志在惩戒失德者的裂裾割席,尤其容易得到舆论理解。
邓攸故事的特点,则在主角总是不断抛弃那些信任他、依赖他,甚至愿意帮助他于危难中的人。
后来讲起邓攸故事,一部分人(包括《世说新语》编撰者),或许把这些“抛弃”也混同于闻过能改,遂使邓攸“素有”了某些他自身不具备的德行。
《世说新语·赏誉》第一四〇条: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
‘天道无知,使伯道无儿。
’”邓攸活动时期与谢安正大致相当,名望则远不如。
东晋后期到齐梁,邓攸故事的讲述方式逐步定型,似乎也掩藏了某种默契:
但,认真分析,实际并不困难。
邓攸行事一贯之处,主要是经营人设,追求名声,以名求利。
为此他可以谦和对下,也可以“敬媚权贵”,在西晋摆出务虚蹈空的姿态,东晋初则努力展示政绩和能为——两朝评价人的标准有变化,当轴权贵也取舍不同。
但他内心实质说不上有原则,眼光不够长,既没有与人共担风险的能力和毅力,也无法自行组织队伍,就很容易表现出:
总在各个势力集团接近发展顶点时投奔,又在他们转向下坡时迅速脱离。
承平时,这类人经营声望,大多确实能收获随之而来的一些利益,很难暴露本相;
碰到乱世,他们还能凭借伎俩活下来,甚至暗暗得意自己的“生存技能”。
历朝历代,这类人物都往往比纯良君子多。
相较被弃而丧亡的无辜者,这是很令后人唏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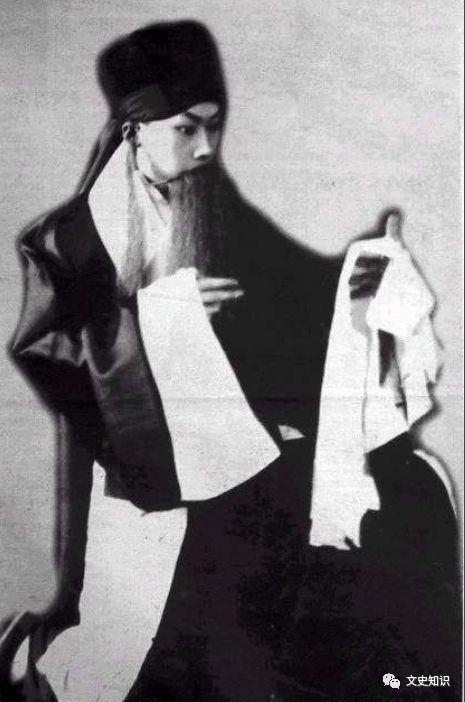
南渡衣冠至少可分三类:
元帝永嘉时期草创班底的成员(旧臣)、流民帅(强将)、其他。
邓攸所属的“其他”群体,渡江有先后,内部层次丰富,种类繁多,个人品质各异,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对汉魏以来的观念新变,则有不同接受和理解,在东晋南朝文化发展史上,构成大量驳杂、斑斓的图景。
东晋权门如庾、桓、谢等,多属“其他”群体,客观上也使认同邓攸价值观的人,得以从旁趁势发声,甚至裹挟一部分文化人物的意见。
邓攸的“德行”,正在此阶段获得避重就轻的树立。
作为个案,邓攸在西晋便依附强者,南渡之后更加如此。
真实的个人欲望、无力自主的个人困境,产生巨大的戏剧张力。
他这类人,在南渡者中并非罕见。
不过,即便他和同类们始终努力经营“清名”,但在《晋书》的编撰者们看来,除了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邓攸实在再没什么可多加赞誉的。
同处两晋之际,论家中情理,邓攸不如他的前任尚书左仆射荀崧:
遭遇乱兵身受重伤,还能保护幼女周全,甚至把女儿教育成文武兼能的小英雄;
论地方政绩,他比不了年纪轻轻就力拔郡国守相考绩头筹的诸葛恢。
他出守吴郡,刻意模仿地方上前贤陆绩的清廉表现,痕迹却过于明显。
论大节、论原则,他更远不如《晋书·良吏传》中的其他许多人。
史臣论给他的标签止步所谓“清廉”:
《晋书》并不认为他能像同样被史臣点名的西晋洛阳令曹摅一般贤明。
总而言之,邓攸的遭遇,有他自身和外在环境的多重因素,“伯道无儿”更是一连串进退失据综合结果的象征。
遥想过江之初,他出守吴郡,还能试图兢兢业业为当地解决问题,甚至在灾荒中顶着政治风险开仓放粮。
或许他还在试图博取声名,或许他的良心当时并没有完全沉睡,能提醒他,有一些东西比个人利益更重要。
但,谁知道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19年第10期“人物春秋”栏目
感谢您对本刊的厚爱,2019《文史知识》继续贴心陪伴您,忙碌中别忘了订阅哦:
一、去往邮局征订,邮发代号2-271。
二、咨询伯鸿书店购买,联系电话:010-63458912、010-63265380。
三、北京的读者可以去往三联韬奋书店、万圣书园、伯鸿书店购买(伯鸿书店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中华书局一层)。
四、需要网上购买的读者,请登陆“杂志铺”网站(www.zazhipu.com),京东商城中华书局官方旗舰店(http://mall.jd.com/index-84097.html)然后在搜索栏搜索“文史知识”,即可看到《文史知识》的订阅信息,按照网站购物流程购买即可。
五、集体订购电话:010-63458229。
六、您也可以添加《文史知识》的微信公众号“wszs1981”及时获取《文史知识》的更多信息!征订在即,请千万别错过。
七、敬告读者:自2018年7月1日起,《文史知识》编辑部不再接受任何购买咨询,如欲购买《文史知识》新刊、过刊、历年合订本等销售问题,敬请致电中华书局伯鸿书店(010-63458912、010-63265380),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文史知识》(月刊)邮发代号2-271,每月1日出版,定价15.00元,全国邮局均可订阅,国内统一刊号 CN11-3153/K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2-9869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文史知识》编辑部收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458229
(邮购 每册15元,挂号每次另加3元)
微信号:wszs1981
QQ群:363031535(迁移中) 713071938(新群)
新浪微博:@文史知识杂志
官方网站:中华书局/文史知识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电话:010-63397473
010-63458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