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道要用半生沉默,才能换你一句真心?」
截至去年8月份,从富士康的大楼上,已经陨落了30个生命。
其中有一位年轻人,他叫许立志。
家境贫寒的他,自高中毕业后就辗转外地打工。2011年,许立志进入了富士康工作。
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诗人。
在他的诗里,生活是这样的: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2010年的第一跳,让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生活。
每日每夜,他们活在人为筑起的“牢笼”里,每日每夜,他们都要咽下那一枚“铁做的月亮”。
然而这一切,那些身在大山里的母亲并不知道。她们与子女日常的联系,就是每年一度的春节。
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爬上富士康附近的一座大楼,脚底下的一条条流水线,仿佛掘开了青春的墓地。他纵身一跃,再也咽不下了……那一年,他才24岁。
到最后,家里的老母亲才从别人口中得知:儿子死了,他曾过着怎样挣扎的生活。
如果许立志心中的那块顽石有人与他分担,那么结局会不会变得不一样?

父母与子女之间,似乎藏着许多不可说。
累了,不可说;病了,不可说;甚至出事了,我们也常常选择缄口不语。
这一点,每一位离家打工的年轻人大抵都懂。
小事怕父母唠叨,大事怕父母担心。我们和父母之间,隔着巨大的信息断层。他们从电话里已知的信息,只有我们吃饱穿暖,工作不错。
可是,每当从他人口中听到那些难以挽回的伤痛时,总令我不禁怀疑:这样的隐瞒,对吗?

还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过:“怀胎十月,你从我肚里出来,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每一次心情不好时打电话回家,母亲总能敏感地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当时,我仅仅只喊了一声“妈”,她便接着问我“闺女,怎么啦?是不是遇上啥困难了?”
当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时说不出话。原本不觉得委屈的委屈,就在听到他们声音的那一刻,溃然决堤。
工作多年,我早已独立,可以独自面对挫折和打击。尽管一度困难,但从未害怕,因为我知道,
这世上最爱我的父母就站在身后,一回头,就能够望见他们,一开口,他们便会向我奔来。他们随时都准备着为我们倾听,只差我们自己说出口。

我们用尽一生,都在朝着远离父母的地方走去,未曾认真诉说过自己,也未曾仔细推敲过他们的过去。
自孩提时代起,
邬霞的
父母就离开她去了深圳打工,她成了中国的第一代留守儿童。
邬霞的父母,也是一对十足的“骗子”。
他们会到深圳的照相馆里,挑选高楼大厦的海报为背景,拍下照片,寄给老家里的邬霞。
在小邬霞的眼中,深圳一直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父母一直过着美满富足的生活,总有一天,他们会接她过去。
直到14岁时,父母带着她走出大山,远赴深圳打工。此时,她才看清了生活的全貌。
她卖过头饰,学过美容,做过库管,干过最多的,还是制衣厂的流水线。30多名工人,一天要做出1000多件成衣来,忙到晚上12点才下班。
工作的忙碌,一度令她痛恨。然而,在她的诗歌中,写下的却是篇篇温暖。
为什么?
因为父母从小时候起“
撒过的谎
”,落在了她的梦里,她的笔下,为她在残酷的生活中筑起了温暖绮丽的城墙。

邬霞在诗里,对陌生的姑娘说道:“我爱你。”
还记得去年众筹观影时,有一位读者在看完电影
《我的诗篇》
之后,也说出了她的故事。
她的父亲,是一名矿工。和片中的老井一样,在外地打工,每天要下到600多米的地底下挖煤。
父亲下岗的前一年,矿井中发生瓦斯爆炸,他幸运地活了下来,抬着工友的尸体走出了井外。
这一切,他从未告诉这位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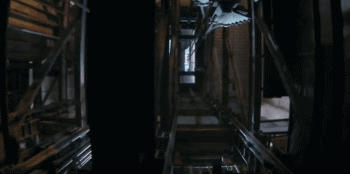
矿工老井,每日都要下地600多米
从小到大,父亲在女儿的眼里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丢下家人跑去外面,不知道自己女儿期末考了多少分,也不知道自己女儿被老师夸还是骂,更不知道女儿有多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