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在空中。”
在小说《遗忘通论》中,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José Eduardo Agualusa)笔下的秘密警察发出这一声低吟,对面是一名“收集失踪的人”的记者。阿瓜卢萨给这个章节起了整本书最长的小标题:“本章会阐明一件失踪事件(接近两件),或是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2024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阿瓜卢萨从非洲远道而来,他在复兴公园望见一座马克思雕像,兴致勃勃地过去合影。独立后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都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阿瓜卢萨目前居住的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还有条“毛泽东路”,原美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就在这条路上。“美国人去找过莫桑比克政府,想让这条路改名,但莫桑比克人表示,名字我们可不会改,要不你们搬去新地方吧。”
阿瓜卢萨1960 年生于安哥拉中部内陆高原万博,父母是来自巴西和葡萄牙的移民。他出生时,国家还没独立,万博一度被葡萄牙殖民者唤作“新里斯本”,多元的成长背景让他意识到非洲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也激发了他的创作。
“35年前,我开始写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国家——安哥拉,以及在这个国家、在当时经历的动荡岁月中我的位置。”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发言时,阿瓜卢萨介绍自己的国家“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漫长、最残酷的内战”。
1975年,安哥拉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同年,安哥拉内战爆发,直至2002年才实现全面和平。长达27年的内战造成了安哥拉动荡不安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现实,这些记忆和经历都成了阿瓜卢萨的素材。“我常常在想,是否因为虚假的记忆,我们的现实也是不真实的?我们到底是谁,身份的不确定性总让我感到不安。”上海书展期间,阿瓜卢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小说《贩卖过去的人》中,主人公是个为雇主构造记忆的专家。安哥拉民族独立后,随着经济发展,一批新富阶层应运而生——“企业主、各部部长、农场主、钻石走私商和军官”,他们有钱有势,唯独缺少体面的出身。主人公通过信件、照片和墓志铭等,为这些人造出一个高贵族谱,满足他们对身份的虚荣渴望。凭借这部作品,阿瓜卢萨2007年荣获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他是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战争是一种非常例外的状况,在这种颠覆性极强的状况里,人很容易暴露自身的某种天性:他可能成为英雄,也可能变作怪物,我一直想做的就是探索人的这种天性。”
《遗忘通论》讲述了战争期间一个遭受过性侵的女人将自己关在家中整整28年的故事;在叙述主线之外还牵出多条辅线:一名葡萄牙雇佣兵被秘密警察审讯,经历九死一生逃至少数民族聚居区;法律系的青年学生在国家经济转型后暴富成了企业家;流落街头的孤儿被迫沦为小偷……所有人的命运在一张记忆的蛛网中交织,阿瓜卢萨将沉重的故事讲述得轻盈如梦。随着《遗忘通论》入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并荣获2017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阿瓜卢萨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他被视作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

▲1976年安哥拉内战期间,一名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士兵护送女孩和婴儿离开战地 图/视觉中国
“世界终结之后,会在岛上开始。”在近作《生者与余众》中,阿瓜卢萨描绘了一个具有非洲特色的后末世故事,这是“一部关于人们被困在时间胶囊之中、来到现实难以触及之地的小说”,主人公来到一座小岛参加文学节,小岛与外界的沟通突然中断,岛上的作家们在七天时间内,以写作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岛屿与大陆、当下与过去、真实与虚拟,种种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我写作是为了反抗界限。”正如阿瓜卢萨在上海书展演讲时强调的,“仇恨的第一步是制造他者”,而写作则朝着相反方向努力,“难的是倾听敌人的声音。更难的是套上敌人的皮肤,感受他的心脏在我们胸中跳动,并流下他的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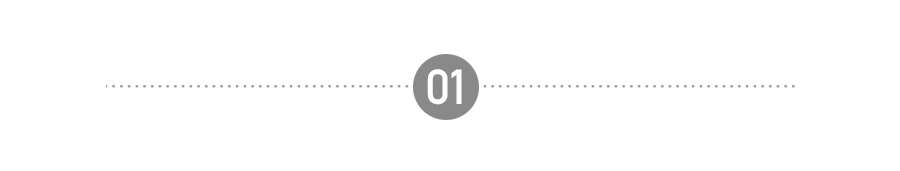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中国存在感很强,
《天上的生活》里有“上海”飞行器
南方人物周刊: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此前对中国有何印象?来上海这几天有何感触?
阿瓜卢萨: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其实有很多华人。此前我对中国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如今在全球的存在感和地位都很高、国力也很强盛。中国的高度存在感不仅出现在文学中,也进入了流行文化,例如2022年的安哥拉电影《中国商店的圣母像》就以安哥拉一个中国商店里的故事展开。中国并不是依靠战争或暴力冲突等达到这样高的存在感,而是通过商贸,这与巴西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印象相似,巴西也是体量、影响力大的国家,但它也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文化和商贸产生影响,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点。
上海是座巨大的城市,让我想到巴西的圣保罗,有些地方让我感到惊奇,上海比我想象中更井井有条。此外,这里有很多公共绿地,我非常喜欢。虽是个大都会,但有时我不觉得它很大,整座城市比较宁静,尤其晚上我们在苏州河畔散步,没我想象中大都会不夜城的喧嚣。

▲《中国商店的圣母像》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2013年的小说《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中,掌握权势的人建造了名为上海、东京、圣保罗、纽约的巨大飞行器,16岁的主角卡洛斯则住在罗安达这样的村庄。这部小说还未翻译过来,可否给我们介绍下“上海”这个飞行器的样貌?为何选择这几座大都市来命名飞行器?
阿瓜卢萨:《天上的生活》是我写给自己孩子的一本书,它描绘的是一个类似“启示录”中的景象:全球灾害频发,一场巨大的洪水淹没了世界……为了生存,富人建造了飞行器,空中有这4座,其实总的更多;穷人运用想象,创造热气球才能飞到上面去。我想传递的信息是:非洲与其他更发达、现代的地方比存在着落差,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这种落差和不平等。
至于“上海”这个飞行器,我只是提了一下,我具体描写的是“巴黎”飞行器,那座飞行器非常漂亮、壮观,内置一个大花园,还有个巨大的游泳池,非常典型的富人生活的配置。基于《天上的生活》这本书,巴西可能会做个动画电影。我计划给孩子们写三本书,这是第一本,另外两本还没写,说不定这次来上海后回去就有思路了。

▲2023年9月23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市郊的凯兰巴新城夜景,这是中企在当地承建的最大民生工程。凯兰巴新城建成后,被安哥拉政府称为安哥拉战后重建的典范、安哥拉乃至非洲大陆上的“明珠” 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主论坛上,你提到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阴谋》,那是怎样一个“阴谋”?你表示,写这部小说是为了了解过去、理解现在,创作完成后,你对过去和当下的认知有何发现?
阿瓜卢萨:《阴谋》是一部历史小说,我虚构了一个历史事件,故事是19世纪末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一次起义,因为同期巴西也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所以我在书中虚构了这样一次践行尝试。
从这本小说开始,到如今我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书中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不久的将来,都在帮助我不断理解过去和当下,甚至是理解自己。完成每部作品时,我都会感受到极大的愉悦,快写到结尾时,我开始意识到所写文字之间的各种关联,这简直就是个魔术,连我自己都没法解释。至今,我都是在这种巨大的愉悦中写作。我太太有时会抱怨:你创造了一个世界,然后就住在里面了,都没法跟你真正沟通。(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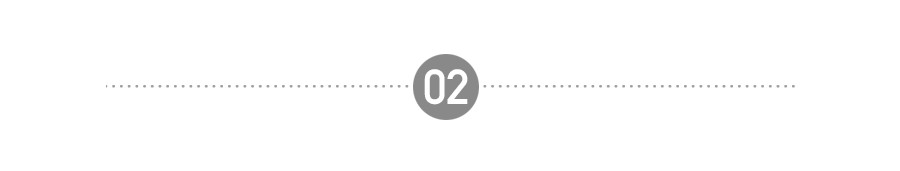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失明”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遗忘通论》中有个小标题“失明(以及心的眼睛)”,《生者与余众》中有只名叫“命运”的盲鹅,你似乎经常会写到“失明”的状态?这也让我想起葡萄牙文豪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阿瓜卢萨:说实话,之前我还没想过与萨拉马戈的这种联系。我非常喜欢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现在我开始想你这个问题,通过我的读者、他人的解读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书,让我感到快乐。要知道,这些书是我和我的读者们共同建造的。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新鲜,我需要时间好好思考下,我现在能马上想到的是,你提到那只盲鹅“命运”,因为我觉得失明跟命运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此前受访,我常被问到: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到底是不是直接可触的?或说现实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失明”本身就是这个现实中的一部分。
我们观看世界,其实也是观看他人或通过他人去认知这个世界,对作家来说,最有趣的一点是你居于另一个人的身体中。例如,想象一个盲人的生活是怎样的,这本身也构成作家应该去描写的现实之一。在我另一本书《热带巴洛克》中,主角某种意义上就是我的另一个自我,他在一夜之间因遭受重击而一只眼睛失明了,现在我一边回答你的问题,一边尝试再把失明、心的眼睛以及残酷的现实等等联系起来,能想到的是绝望,失明跟那种令人绝望的现实有很强烈的联系。
南方人物周刊:有评论指出,《遗忘通论》中在地图上消失的小部落“新希望”是安哥拉动荡社会的缩影。在漫长的战乱年代,政权频繁交替,很多人不再相信国家能走上正轨。你自出生起先后经历了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的独立战争和之后长达27年的内战,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关于战争最深的记忆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力量能帮助人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阿瓜卢萨:内战时我在老家南部小城万博,当地经历了近50天的炸弹轰炸。那段日子,许多人不是四处流散就是闭门不出,因为怕被炸死。当时万博有个花园,花园里有个园丁每天还会从家里出来,去花园侍弄花草。当时我还是记者,就很想认识这个人。我问他,为什么形势这么严峻你还每天去花园工作?那人就说,因为这些花草需要人照顾。直到今天,这个人的故事、这段记忆,对我来说都是人生重要的一堂课,哪怕在暴力或极端境况下,人群当中总还有这么些人,会坚持去做日常的一些工作。
我最新出版的《一部安哥拉传记》,写的就是安哥拉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正如你刚才所说,他经历了从反殖民到内战等好几场战争。为写这本书,我采访了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是,采访这些人时,哪怕他们在那段历史时期持不同政见,但回顾过去,也不会显示出丝毫的厌恶或极端的仇恨。这也是安哥拉人最让我感动的点:人们拥有一种非常包容的原谅的力量。在我看来,安哥拉街头碰到的任何一个人对我讲述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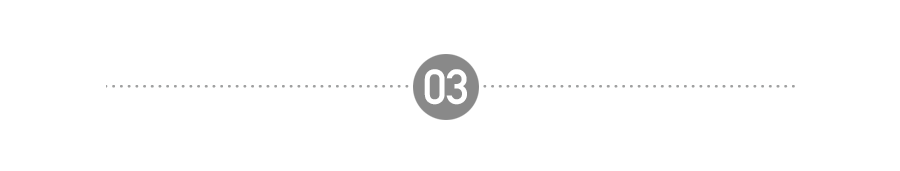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花朵“发烧”了,我想成为一棵猴面包树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在葡萄牙学习农学和林学,回望过去,这两个专业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启发和帮助?
阿瓜卢萨:对我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是这两个科目中最诗意的部分,举个例子,例如植物在破土前有个专业名词,直译出来是“花朵的高热”,或者说,花朵“发烧”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一天也许我会用这个词写本书。
南方人物周刊:这个表述的确富有诗意,我发现在《遗忘通论》的“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坦白”一章中你引用了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整本书中也经常穿插着卢多写下的优美诗句,诗歌对你的生活和小说创作有何影响?
阿瓜卢萨:我非常喜欢佩索阿,身边常带着他的《不安之书》。我热爱诗歌,可以说,我对诗歌的兴趣比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兴趣都更浓,我家里其实有些中国古代诗歌的文集,我也读过一些中国古诗。我觉得,诗歌会带来一种惊奇感,通常我写小说前要先读下诗歌作品,我的小说是被诗歌照亮的,也有诗行贯穿其间。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将自己比作一种植物,你觉得比较像哪种植物?为什么?
阿瓜卢萨:在莫桑比克岛上,我们不久前买下一个17世纪的大房子,我们也有一片园子,在园内也种了棕榈树,那里还有很多天然的猴面包树,我也非常喜欢猴面包树,它们现在大概有5米高,但还只是一棵小树。
如果可以选择,我想成为一棵猴面包树,因为猴面包树非常长寿、能活很多年,这点很重要,因为我想体验时间的另一种维度,树所感受和生长的这种时间跟我们人类不同,就像蜉蝣感受到的时间长度跟人也不一样,树会生活在一种更加宽松、拉长的时间里,我很想体验这种时间感。此外,猴面包树往往长在水边,它会收集雨水,我很喜欢收集雨水的这种感觉,这也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名字,以前海员出海时,若发现海面很平静、透明,他们描述这个水的状态就叫“阿瓜卢萨”,阿瓜(Agua)是水,卢萨(Lusa)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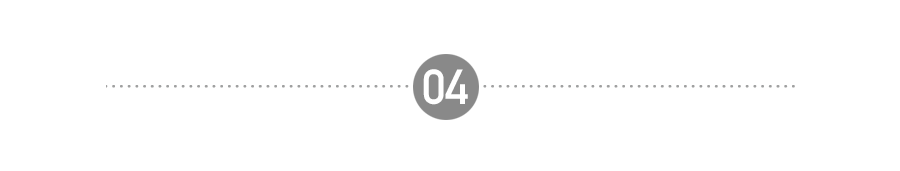
“你小心点!这条路上到处埋了地雷”
南方人物周刊:《遗忘通论》中有个记者丹尼尔·本希莫尔,他与你本人的记者经历有关?战争时期,你有没有经历过危险状况?
阿瓜卢萨:我在安哥拉做记者时主要供职于葡萄牙媒体,那时基本什么领域都做一点,政治的、社会的,但我主要还是文化记者。
当时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猛烈或直接的危险,但有些事就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会让你察觉到那种危险的气息。记得那时我正好经过拜伦多,安哥拉有个中央高原在那块地方,我跟着一队人经过某片区域,我准备下车解手,下车没走多远,就听到有个士兵在吼:你小心点!这条路上到处埋了地雷。这件事会让我不断去想,普通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一辈子要怎么活下去?你随便走的一条道上都埋了地雷,我尤其会想到女性,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生存下去。

▲1997年1月5日,戴安娜王妃访问安哥拉万博,她身穿防弹衣,头戴面罩,走过一片清理过的雷区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听说《遗忘通论》中女主人公“卢多”的故事来源于你读到的一则新闻?
阿瓜卢萨:恐怕那是误传,整本书就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开启这本书的写作与我个人经历有关,那时我还是记者,整个安哥拉社会非常动荡,我住进了罗安达一个奢华的公寓,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战争爆发,底层阶级侵占了这栋奢华高楼,书中这一切也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我住进去时,整栋楼就是处于这种贫富交加的动荡过渡期,时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冲突或暴力。住在里面时,我也会感到挣扎,要怎么活下去?也是在那个时候,“卢多”这个女人就从我的体内生长出来,实际上是我感受到的这一切——如此动荡的环境下如何生存以及外出面对他者的恐惧。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男性作家,你选择刻画一名女性来传递某种心声。
阿瓜卢萨:作为作家,最有趣的事往往是创造一个跟你距离很远的他者。我认为,在那样一个时代、环境中,女性比男性更脆弱,生理上的原因,可能会招致更多麻烦,此外年迈的女性还会面临更多困境,所以我创造了这个更加远离我自身的女性角色。
南方人物周刊:提及女性,安哥拉历史上有位著名的恩津加(Njinga)女王,她一生都在与葡萄牙殖民者抗争,你在《遗忘通论》中也提到了她。欧洲人笔下的恩津加极富传奇色彩,我很好奇,安哥拉人民眼中的她是怎样的?
阿瓜卢萨:写安哥拉的历史不可能跳过恩津加女王,为了写她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我想从内部视角——例如宫廷里更接近她的某个人——出发去写这个女王的故事。因为那是个遥远的时代,所以我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找到叙事的声音,最后我选择由一位巴西神父来叙事,他既有安哥拉血统、又有巴西的原住民血统,当我找到这个声音,写得就特别快,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在我心里形成了。
恩津加女王不仅对安哥拉产生历史影响,在全球,无论是17世纪她的故事发生时还是如今,包括在流行文化里,都是非常重要的现象。恩津加女王是个僭越性极强的人物,她依靠自己建立各种规则,并建立了她的世界。有趣的一点是,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时,有一部分被剪掉了,尤其是在安哥拉放映时——那个部分讲述了女王在宫廷里有五十多位男宠,这五十多个男人都穿着女性的服饰,而女王本身则穿着男性服饰,安哥拉那些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不能接受这部分,所以剪掉了,但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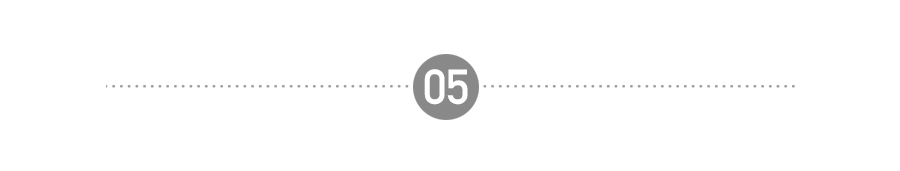
时间是圆的,
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在空中
南方人物周刊:《遗忘通论》中有这样的句子:“时间没有方向地延展”,《生者与余众》里的时间也是非线性的,分享下你本人对时间的理解?
阿瓜卢萨: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时间其实是一种意识、文化上的构建。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地区,总有些关于时间的不同解读,例如有些地方,未来指向并不是向前,而是在背后,因为它看不见。再说非线性的时间观,就像时间是圆的,或者说不存在我们失去时间,其实时间一直在延续,并没有失去的概念。
南方人物周刊:时间的概念与记忆关系密切,《遗忘通论》这个标题本身就跟记忆有关,你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记忆与时间的关系?
阿瓜卢萨:其实我所有的写作都在反思时间的性质,而记忆这个主题对我而言与身份密切相关。一直以来,让我最担忧和不安的是记忆的整体,比如《贩卖过去的人》中,记忆的整体中存在虚假的记忆,是否因为这种虚假的记忆,我们的身份也并不是真实的呢?从这点出发,当我们说我们是谁,背后这个东西到底是虚假还是真实的?它跟我们经历的过去密切相关。这种不安推动着我的写作,因为我的作品经常聚焦记忆、时间与身份的关系,我最终想传达的,也许是没什么东西是永远坚固的,一切都是流动的。

南方人物周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原乡也是非洲,你们有交集吗?
阿瓜卢萨:我认识古尔纳,我很欣赏他,他是一个非常亲和、温柔的人,我们是在肯尼亚的文学节上认识的,他赠了我三四本书,我读过那本《天堂》,他笔下的桑给巴尔与莫桑比克岛关系紧密,正因如此,我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
南方人物周刊:你常去欧美旅行,你认为西方人眼中的非洲形象是怎样的?与你青年时期相比,他们对非洲的印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阿瓜卢萨:说实话,我年轻时并不存在“西方人怎么看待”的问题,也并不存在真正的视角,存在的只是“无知”和“看不见”。今天当然改变了很多,正因如此,像古尔纳这样的非裔作家可以获得认可。我觉得真正变化的不是他们的观点和视角,而是他们终于愿意多投一些眼光。但我觉得,美国还是相当傲慢自大的,当它真的想要了解谁时,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军事或其他方面的冲突,而这种了解播种的还是一种无知,这点跟像英、法、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很不一样,那些国家殖民过非洲,今天在它们自己的社会里存在大量非洲后裔,它们自身与过去的非洲有某种联系,因此古尔纳在英国的写作会获得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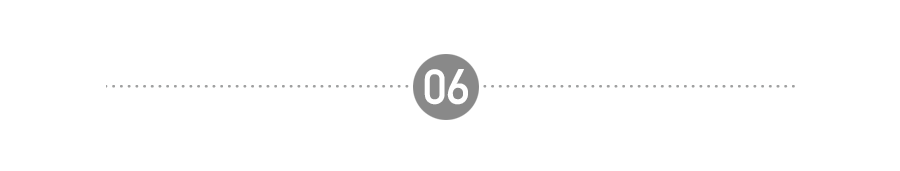
马尔克斯就像我的家人,
博尔赫斯转世成了小壁虎
南方人物周刊:拉美作家里你最喜欢谁?
阿瓜卢萨: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觉得自己与他之间有种强烈的亲近感。加西亚·马尔克斯1977年访问过安哥拉,写下关于古巴人在安哥拉驻军生活的报道《卡洛塔行动》,那次安哥拉之旅让他找到了儿时在哥伦比亚的回忆和感受。我读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觉他就像我的家人。他的书哪怕出现什么错误,我都觉得这种错是可亲的,但博尔赫斯并不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贩卖过去的人》开篇引用了博尔赫斯:“如果我必须重活一次,我要选择完全不同的事物。我想当挪威人。也许当波斯人。不当乌拉圭人,因为这就像是搬了个街区。”这段关于身份的假设与你的心声有关?
阿瓜卢萨:如果重活一次,我还是当安哥拉人。(笑)引用这段话最主要的还是“勾引”读者,就像捕鱼者使用鱼饵,让读者对整个故事产生兴趣,这本书的叙事者就是博尔赫斯的转世,我让他投胎在安哥拉,所以开篇做了引用。作为作家,我非常喜欢博尔赫斯,但作为人,博尔赫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在书里我让他投胎成了安哥拉的一只小壁虎,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报复。(笑)

南方人物周刊:提及动物,你给它们取名很有意思,《遗忘通论》中的小白狗“幽灵”、猴子“切·格瓦拉”、小酋长的鸽子“爱”,还有《生者与余众》中的盲鹅“命运”等,说说给动物取名的灵感?尤其是“格瓦拉”。
阿瓜卢萨:这个猴子真实存在,当时我住在那栋奢华公寓里,真的就看见了猴子,还有小说里的那些天线,无数根天线,但总有一个是朝反的方向,无论天线还是猴子,在我看来都有一种反叛的意味,所以我很自然就想到了“切·格瓦拉”。
在非洲的口述传统里,动物的存在感很强,给它们取名很自然。在我们的传统里,动物与人之间的界限甚至可以没有,会出现变形。我在《生者与余众》中写到一个女人变成了蟑螂,之前有批评说非洲作家写这些是魔幻现实主义,但没人记得卡夫卡也这么写吗?我想中国文学传统里应该也有这些动物与人的故事。
(感谢余沛霖现场葡语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