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云也退
鼎鼎有名的《安妮日记》,距离其首次出版至今已整整七十年,但中国人恐怕对它相当陌生,因为印象告诉我们,这本书大概无非诉苦和励志而已,生于苦难的小女孩乐观而顽强地活着,不幸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暴徒的罗网,并死于集中营。但我们不知道,书中所述的内容还远不止此。自其被人读到伊始,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留下的这些文字,就不单单被看作希特勒发动的屠犹暴行的直接佐证,否则,犹太世界自己不会如此推崇它——他们早就过了煽动苦难记忆,要世人铭记大屠杀的阶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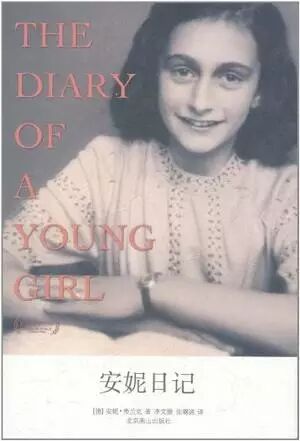
▲ 《安妮日记》
“我这就开始吧。
“此刻是这么宁静。爸爸和妈妈出门去了。玛戈特和几个年轻人到朋友家打乒乓球去了。近来我也常打乒乓球,甚至我们五个女孩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名字叫‘小熊座减二’。一个将错就错的怪名字。我们本想取一个特殊的名字,因为我们有五个人,于是马上就想到小熊星座。我们以为小熊座有五颗星,可我们搞错了。小熊座有七颗星,和大熊座完全一样。这就是‘减二’两字的由来。
“伊尔丝·瓦格纳有一套乒乓球设备,瓦格纳家的大餐厅随时供我们使用。由于我们这些打乒乓球的女孩尤其在夏天都爱吃冰淇淋,打球会热,因此打完球就常去光顾最近一家对犹太人营业的冷食店‘绿洲’或‘德尔斐’。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身上有没有带钱。因为‘绿洲’通常都门庭若市,我们在许多熟人中总会找到几位慷慨解囊的男士或某个追求者,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淇淋多得一个星期也吃不完。
“我想你一定会感到奇怪,我这么小小年纪就已经在谈论追求者。……”
这就是安妮日记的画风,提笔的时候,她已经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间密室里,之后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一直在写,直到被纳粹抓捕。她的这些信,首先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写给另一个自己——一个名叫“吉蒂”的女孩的,这使其文笔更加自由,就好比平时我们喜欢把自己的事安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说给别人听一样;其次,她写信也是做好了将来发表的准备的,自己反复删削、修改多次,因为她从当时流亡的荷兰政府的讲话中听到,战后要收集战时的日记整理出版。
根据战后的统计,90%的荷兰犹太人后来都没能逃脱纳粹之手,惟其如此,安妮的天真,对未来充满希望,从没想象过迫害会真正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等等特质,才显得那么耀眼。尤其是,她的文字将读者带离、而不是驱近残酷的现实那一边,读者跟着她沉浸到她的世界里,这里有乒乓球,有伙伴,有孩子对成人的纯真观看,还有“小熊座减二”——在任何一个时代,能玩这种字谜的人都稀罕地同时拥有两份内在财富:聪明与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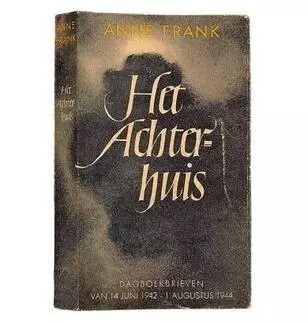
▲ 《安妮日记》初版封面
安妮记录了大人们的行迹,不时发着可爱的牢骚,也替别人抱怨:“范丹先生和太太大吵了一架……彼得当然很为难,他夹在中间。”对父母,她的好恶但言不讳:“爸爸对我总是很好,也更理解我。啊,这种时候我受不了母亲,我对她而言也是个外人……她连我对最平常的事情是怎么想的都不知道。”她写自己阅读心得,都是直感,从无成人的欲言又止:“《夏娃的少女时代》写到女人在街上出卖肉体,换取一大笔钱。我要是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她还在幽闭之中面对成长的秘密:“我多么希望来例假呀,那样,我至少就长大了。”
只要谈及大屠杀,就必须正面说出其悲惨、恐怖,这在战后的氛围里渐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安妮日记,这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屠杀文献”的文本,就显出其独具犹太特色的矛盾性来:对于屠杀和迫害,安妮并不是不提,而是一提到就作轻笔,例如她曾说,与那些躲无可躲、但又必须活下去的犹太人相比,“我总是总结说,我住的地方是个天堂。”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记里,安妮说出了“我的悲歌”,她听闻一批又一批犹太人被抓走的消息,也预感到了他们的命运是“等候处死”,不过,她以向“吉蒂”吐露心声的方式写这些听闻和自己的心情,多多少少,你会感觉她在写时的心情不算太坏。
安妮日记是在安妮死后由其父亲整理出版的,起初,一批专家质疑这些文字是否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之手,后来鉴定为真,人们又困惑于应该怎么“使用”它。安妮够真挚,也够乐观,却不够“正确”——不符合教育后人的要求。这里面的悖谬令人犯难:人们可以拍出很正确的影片,出版很正确的纪实或虚构作品,将历史事实化作一种固有的善恶印象,永远扎根在人们的内心并代代传下去,然而,这历史事实的第一手经验者自己的记录,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一印象。这可不可以视作一种“当局者迷”?
当然,学者们给出了解释:安妮困居一室,行动受限,随着时间推移,能接触的人越来越少,她不可能洞悉全局。解释很合理。不过,人们依然一直在讨论,如何给孩子们读安妮的日记,让他们以何种方式知晓安妮的故事,这关系到如何传承大屠杀文化——并用它来警示世人。是灌输给他们一个“真相是什么”的结论,还是一上来就捆绑着把当事人的态度也说给他们听,并且启发他们认识到,即使对于一个大体确凿无疑的历史事件,每个人也会操持不同的观看和理解的角度?
如果是后者,那么,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就能学到重要的一课,将学会在各种看法和意见之中形成自己的判断,而相信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的、终极性的答案。也许还能更进一步,相信个人的力量能在外界现实之外创造另一个现实,一个如安妮日记中的现实一般的现实,打满了作者人格的烙印。犹太人总是相信留下文本的意义,但在实践中,文本绝非终极的目的:它们会引起更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需要以更多、更大的问题来回答。
(题图为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手握奖杯,1971年,他因《安妮·弗兰克日记》售出100万册而获奖)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