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谈论美食时,食物对我们的身份塑造作用不可回避,因为食物是人类不同族群的共同命运,而不同族群通过食物进行的交融,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作者覃里雯现居柏林,她曾描述这个城市 “ 除了纳粹时期,它习惯于接纳情愿或不情愿的游荡者。” 然而,当世界正日益封闭时,人类还有什么牢不可破的连结存在?此次她介绍与评述了陈楠的新书《在中西味蕾间游弋的食谱》,本书循着中西饮食与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皆以美食为着眼点,汇集了多篇介乎于笔记、游记和历史考证的文章。而书中的各色美食的共性似乎暗示——食物,或许自我与他者和解的可能方案。

他者之食
覃里雯
隔着 2016 年 11 月萧瑟的秋窗,坐在工作台前之时,关注和谈论食物并不是我那一刻最想做的事。因为 6 月的英国脱欧和刚刚发生的美国大选,整个世界正在急速堕入一个封闭社会的漩涡。日常生活的地板被抽走了,露出大地之下深深的裂缝。在曾经以种族融合和宽容为傲的国际性大城市——伦敦和纽约——也出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仇恨、对立和对少数族裔的攻击,有些女性仅仅因为生病或保暖而戴上头巾就被殴打或咒骂,因为被当成了穆斯林,对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攻击也翻卷而来。煽动对立和仇恨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却坐视仇恨像癌症一样蔓延;启蒙时代的精神遗产被冷漠地嘲笑,人道主义被咒骂。在这巨大的黑暗面前,逃避是怯懦的,而讨论食物,看起来太像逃避了。
纽约……当我望向窗外,被糖浆色的秋叶勾起纽约市的记忆时,食物的记忆却真的第一个浮现心头。那是每个周末中国学生会背着空包造访的唐人街菜市场,回到寒酸的学生公寓里时,背包里会塞满了价廉物美的新鲜食材,从龙虾到苋菜,从牛腱子肉到五香豆腐干。在曾以黑帮和枪战闻名的哈莱姆区,拉美邻居厨房里传出的香气和欢快的音乐,让初见世面的中国年轻人克服对异族的害怕,产生真正的好奇。
我们居住的地方曾是纽约早期犹太移民的居所,一套公寓里挤进了五家中国人,让前来调研的纽约社工同情地摇头不已。但中国住客不知道的是,100 年到 50 年前,犹太难民们在那些拥挤公寓里的生活要糟糕得多:食物匮乏、工作稀缺、帮派之间争夺地盘、宗教冲突,他们只能团结起来自我保护,好歹在纽约,隔离区和毒气室都远隔大洋。我后来才知道,在那些年月里,犹太人也和中国餐馆结下了缘分。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举家去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吃大餐:左宗棠鸡、酸辣汤和橙子鸡这些由早期中国移民发明的“传统中国菜”(虽然中国居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都赢得了他们的胃和心灵。

2012 年 12 月的Tablet杂志和 2014 年 12 月《大西洋月刊》的两篇文章,追溯了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这奇异的纽带。原来,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犹太人和中国人是纽约两个最大的非基督教移民群体,这种共同的“他者身份”把他们既偶然又必然地联接在一起——在圣诞夜,两个异教徒群体,一个不能庆祝圣诞节却需要全家团聚,另一个的餐馆坚持营业,于是他们找到了彼此。犹太教禁止把肉类和奶类食物一起烹煮,而中国菜正好不爱放奶制品,符合宗教戒律。中国餐馆为贫穷的欧洲犹太移民提供了一个感受大都市和精致生活的机会(来自东方的食物!)。
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还解释了中餐馆为犹太人提供的身份认同:“是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犹太人唯一不害怕的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他笔下的主人公 Alexander Portnoy 充满嘲讽和自嘲的解释:“首先,他们(中国人)讲的英文会让我父亲的英文听起来堪比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其次,他们脑袋里也只是充满了炒饭;其三,对他们而言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白人,甚至可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怪不得他们吓不倒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不同种的 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大鼻子罢了。”
这个略带辛酸却又含着温情的食物故事,背后是漫长的亚欧大陆的艰难岁月、作为少数族裔的移民辛酸和喜乐,以及人类之间奇妙的、无处不在的纽带:事实上,纽约的“特色中餐”早已融入了深深的犹太烙印,而纽约犹太人在自己的文化里又重造出了一种“中餐”,使其成为认可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一个仪式。
当我们谈论食物,也可以不是逃避,因为食物是人类不同族群的共同命运,而不同族群通过食物进行的交融,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也正是我在翻开陈楠的新书《在中西味蕾间游弋的食谱》)(此后简称《中西味蕾》)时想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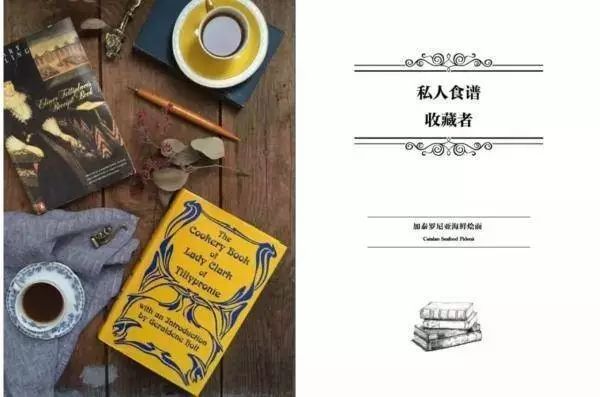
大约在 5 年多前,我把刚认识不久的陈楠推荐到《纽约时报》中文网写美食专栏。那时候我对她还所知甚少,只知道她热爱食物和历史,学识丰富也涉猎甚广,对细节有高度持续的敏感和较真。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编辑最喜欢的那种作者:交稿准时、稿件和照片质量控制一流、应时应景,能收能放,让编辑极为省心,有趣独特的内容还带来了不少忠诚读者。她随即从澳洲搬到了巴黎,在那流动的盛宴里完成了这本丰厚的作品。其中许多发表在纽时中文网,但还有不少内容是书中首发。
我得承认,陈楠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我所熟悉的作家们在描述生活时,经常被一种非常基本的消极态度主宰。这种消极的态度偶尔是因为对生活之美迟钝无感,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作家内心的重负——美好事物的易朽,或者因为在享受的孤岛上却不能忘记周边苦楚的大海:普鲁斯特的小马德琳蛋糕芬芳里弥漫着死亡的灰烟;曹雪芹写雪天烤鹿肉的觥筹交错,夹杂着富裕家族琉璃崩塌的细微声响;余华那喷香的炒肝尖和小酒窗外,是贫困乡村底层的血肉自啮;显克微支的罗马盛宴上,烂醉的贵族们呕吐出孔雀的舌头和罗马民主的污秽……
总之,在流行的食物书籍和“严肃的作品”之间似乎有一道警戒线,这个警戒线由过去几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划定,以悲观作为标杆:毫无保留地歌颂食之享乐,似乎是不够高级的。
被这些概念影响潜意识的我,在刚开始阅读陈楠时,感到些微挑战:她的写作里没有任何嘲讽、迟疑和否认,却总是一种乐观的、些微兴奋的聊天语气,不时展示毫不掩饰的自豪;她的词汇是平实的,带着不少北京口语对话的特点,但这些词汇却足够被熟练地用来传递欧洲各国历史文化,从中世纪宗教油画到“面包”一词作为拉丁语“团体”一词的起源。《中西味蕾》这本被出版社削砍却挤满了 415 页的书里,充满了穿插的历史文化考古索引,但用互联网的词汇来说,“用户界面却很友好”,这也使得这些精简之后的内容易于传播。

我和很多读者和朋友一样,渐渐习惯了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她热火朝天地描述生活里的大小确幸,细读她定期慷慨而投入制作的免费美食指南和照片。就像被她热情地引领着,在各种混杂的各种知识和实用技能的长廊里散步,这虽然已经很好,但真正吸引我的却不是哪些单个的知识或者技能,而是她罕见的持续热情和对世界的爱意。这种热情和爱意,以及随之产生的近乎剧烈的积极态度,对我来说完全是异质而不可理解的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熟悉了这种热情和爱意,但却越来越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维持它需要高度精力旺盛,也需要极度的忠诚。将这二者结合为一体的人是不太常见的,也不太可能靠技巧伪装出来。她对食品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近乎执拗的发掘,把她自己变成了一个活字典。字典的自豪在于它的丰富和系统化,并不十分热衷于自己的价格。她没完没了地收藏书籍和餐厨具,把巨大的公寓塞得满满当当,每本书和每样器具都留下充分用过的痕迹。
当然,除了书房里的研究,用编辑朋友海生的话来说,她的知识也是“真金实银”在世界各国吃出来的,当然也有自己不怕弄糙皮肤、亲手做出来的。从北京街头的酱牛肉到西班牙市场上“贵如钻石”的玻璃鳗,从古罗马的一锅烩菜谱到家制罐焖牛肉做法,她都一视同仁从不歧视,兴高采烈地对待之,几乎每天都以过节的态度开始和结束。
这种兴高采烈的一视同仁,继承了启蒙时代的精神。和我同时代的不少朋友一样,我们是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的一代,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里,很自然地接受了传统国家边界因为贸易和人口流动导致的弱化和变形。我们喜欢寻求新奇的经验,并相信不同文化、阶级和种族之中人类不变的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应当被用于保护和平与友谊,而不是发起零和游戏的战争。
陈楠的食物探索过程里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发掘不同时期和文化中食物和美食家背后的共性:中国饺子和意大利饺子,陕西的馍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桌上的发酵面包,从 17 到 20 世纪的三位欧洲私人食谱收藏者……她理解和记录这些食物和食谱背后的人的情感,整本书就像一封写给人类的情书。这种敞开脑袋和肠胃拥抱一切的态度,与启蒙时期代表作、拉伯雷《巨人传》里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她听从了神瓶对庞大固埃的召唤:“喝吧!”并且永不疲惫地对朋友们和读者说:“喝吧!”这些谜一样的激情感染了我,帮助我在重新立足欧洲的孤独年份里敞开了眼睛、头脑和肠胃,在世故之龄重新获得了部分孩童般的好奇:我学会了去发现17世纪荷兰油画中水果、动物和蔬菜展现的财富和全球贸易之繁盛,也更轻松地在旅行中借助食物与异乡人快乐地交谈。

在启蒙思想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重新被部落主义和仇恨驱赶的时候,谈论食物的起源也有助于恢复神智。 2015 年一个互联网流行的段子很形象地说明了开放社会的重要性:一个人不小心穿越回到先秦,进了家酒馆,结果发现面条要到宋朝才出现,包子得等诸葛亮抓住蛮人孟获之后才有,辣椒和花椒还没从西域引进,最后只好饿着肚子气愤地冲出门去。没有不同文明(包括古代中国疆土上的列国)之间的交流,就不会有丰富的食物,越是馋嘴而好求知的人,越了解这一点。
食物对我们的身份塑造作用的确不可回避,而且很多时候会被用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在“英国活着的国宝”、前大英帝国博物馆馆长 Neil McGregor 的新书《德国——一个国家的回忆录》里,有一个章节专门描写了德国的啤酒和香肠。“公元 100 年前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日耳曼》一书里谈到了那些金发碧眼的部落,他们给莱茵河地区的罗马军团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还有更远处在波罗的海海岸收集琥珀的相似部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一种用燕麦或其他谷类酿制的酒精饮料,发酵成像葡萄酒那样。可以从早到晚地饮用,却不会让人失态。’”在 19 世纪德国崛起的过程中,许多画家绘制了德国部落与罗马人争战间歇畅饮啤酒的场面,这使得啤酒逐渐成为现代德国的民族主义象征。
但在中国,以一种食物获得全国的认同却是不可能的事,甚至可能酿成地域争端:关于南北甜咸豆腐脑的争论,肉粽子还是甜粽子,清淡粤系食物还是麻辣食物。即便在一省之内,比如安徽,就会分裂成三个受不同邻省菜系影响的地区。食物和种族一样,关于“正宗”身份的争论只会导致无限的分裂。不幸的是,舌尖上的爱国主义,因为对历史的追溯局限于疆土之内,很容易制造“自我凝视肚脐眼”的习惯,和对边境之外广大世界的鄙夷。而口味这种严重依赖于少年时期经验的东西,时常被奉为鄙夷的圭臬,用来为阶级、国家、宗教或者种族的优越感赋予证据。

陈楠制作的有文艺复兴风韵的泡芙
《中西味蕾》中提到作者在墨西哥的遭遇:“按照墨西哥官方的文宣,梅斯蒂索( mestizo ,指西班牙裔与印第安的混血)文化就是欧洲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混血。可因断人不愿承认这个名称。对他们来说,印第安文化和西方文化间没有共同点,不是一回事儿。所以露丝.哈克内斯几十年前说的‘强烈对比’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也清晰地折射在墨西哥美食上,比如,我们去朋友推荐的一家位于 Polanco 的餐馆吃饭,餐厅提供无国界法式菜品,菜单上竟然没有辣椒提供。在墨西哥最高档的餐馆里几乎看不到辣椒的影子,至少不会作为主菜出现。因为,那些欧洲化的精英阶层认为辣椒是代表印第安族群的‘上不得台面’的食材。”
但是,在仔细寻找一番之后,她终于找到了体现当代墨西哥种族融合的“爱国菜” Chile en nogada :“一个被塞得鼓鼓的硕大的辣椒,神气地浸在浓稠的白色酱汁里,辣椒上还点缀着一颗颗晶莹的石榴籽……这道菜所需原料来自墨西哥各地,最好的原料汇集一盘,再加上西班牙人带来的石榴,完美地体现了墨西哥文化的多样性……”一道菜也承载了复杂的情感,但最终是人达成和解的最佳方式。
承认食物对我们身份的作用,但又不将它当作身份和行为的牢笼,拓展边界,对不同的习惯和饮食报以理解,就能造就部落主义最本能而强大的敌人。在这点上,一个狂热思念重庆火锅的美国人,一个为法国奶酪疯狂的中国人,和一个热爱葡萄酒的伊朗人,和《中西味蕾》这本书,都有共通之处。在厨房里拿起这本书,按着里面那些穿越大陆和时空的菜谱做饭的时候,与陌生人之间隐秘的联系让我感到温暖。
▍
注:文中配图除注明外,其余均为内文页面。


作者: 陈楠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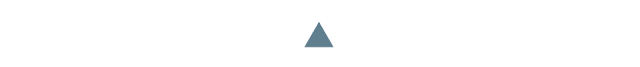
编辑 | 嫌仔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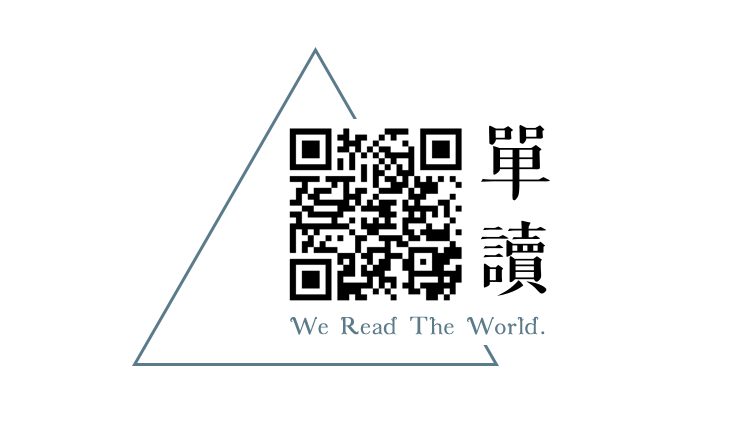
▼
▼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
在中西味蕾间游弋的食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