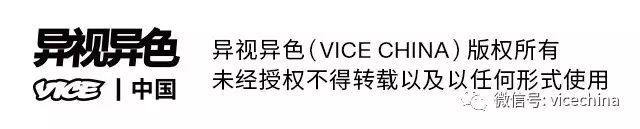我的1997,以及与香港有关的所谓记忆
汤博

1997年我上初一。开学之前,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第一,我考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成绩,高得有点离谱,以至于所有人都怀疑是不是阅卷老师出了差错,不过没有谁傻到真的去查。
这个成绩原本可以择校,但择校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赞助费用。当时下岗风潮已经席卷鞍山全市,我所在的家属院里人心惶惶,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一个少年的未来,与一个家庭的此刻相比,不足为首选。
更何况,择校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美好的前途,更多是想让我脱离一种可预见的中学生活 —— 因为按学区划分,我会升入一个以青少年暴力闻名全市的初中。在那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意想不到的另一种人,而你究竟会变成什么,个人的努力和毅力往往是不够的,更多要取决于运气。
几起学生好勇斗狠的事件经过编排演绎,已在城市流传开来,甚至常有社会上的大人,以认识这个学校的学生为荣。可想而知,我那被忽然被发掘出的一点学习天赋会遭遇什么。你不可能寄情于老师的保护,因为折辱师尊的行为在这个学校近乎传统。
第二件重要的事是香港回归。当时觉得香港太过遥远,虽然只是一水之隔,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香港已属异域风情了。只是不曾想到,随后的中学时代,香港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呼应着我们的成长。我在接受到这种呼应时是无意识的,有点润物细无声的意思;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了新词 —— 文化输出。
回归之前总能在电视上见到香港明星,播放最多的是刘德华和那英合唱版《东方之珠》,听多了觉得词写得美,还知道了罗大佑,一个在香港写歌的台湾人。小学校门口有几个卖海报的小商贩,四大天王和张曼玉周慧敏最为走俏,有的女生会省下零用钱,集齐心仪明星的所有海报,那时已见女生对明星产品的绝对消费力:同一款海报,不同厂家的印刷质量不同,女生会反复对比,最终选择最优一款,如今女孩修照片时对滤镜的精挑细选与当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是明星地,当我踏入那所著名的暴力中学时,陌生的同学靠讨论香港明星的八卦而迅速结成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后来发展成几次大规模校园械斗的主力,这是后话。
1997年,他们的稚嫩还没有被蛮横取代。此后,《古惑仔》系列电影海报成为学生间的收藏爆款,江湖梦在少年心里变成主流价值观。好几个团伙的头目去纹身,图案都是陈浩南胸前的那条龙。纹了身就得露出来,否则岂不白遭了罪(都是用纹眉机纹的)?这些纹身从胸口缠绕至大臂,想要露得全必须得打赤膊,然而毕竟是学生,白天需穿着校服,放学后大家又做鸟兽散,欣赏者寥寥 —— 苦闷之余,几个头目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浴池,就是那种被称为 “澡堂子” 的廉价浴池。
于是有一次我去洗澡,碰到几个民间南哥,他们从水池里集体起身的瞬间,几条图案相同但画风迥异的陈浩南牌大龙从水底冲入半空的水蒸气之中,非常后现代。多年后采访郑伊健时,我向他描述过这个画面,他觉得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学校里的暴力级别在我所处的这一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带刀上学的男生越来越多,后来大家觉得每天带来带去的麻烦,索性放在学校里。刀是凶器,学校不容,刀客们就用胶带纸粘在班级背后的黑板后面。
有一次班级打扫卫生,班主任掀了下后排黑板,一把没有粘好的刀掉了下来,砸了她穿凉鞋的脚。班主任勃然大怒,召集了保卫科的人,逐年级逐班检查,搜出各种类型的刀几十把,装在一个破箩筐里,像极了刚被警方打掉的犯罪团伙的赃物。学校将此归罪为《古惑仔》电影的影响,自此,校园内与《古惑仔》相关的东西绝迹,书皮如果是《古惑仔》海报包的,也会被勒令换掉。那时正是 VCD 的黄金年代,《古惑仔》系列电影以租赁的形式游走于各个家庭,但家长却都谈虎色变。
随着《古惑仔》的没落,TVB 古装电视连续剧和 beyond 乐队取而代之成为校园文化的主题。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重播数次,仍能吸引大家一次次追随,甚至直接带动了校园武侠热: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一众武侠作家渐次成为新的偶像,书里的横刀立马、快意恩仇,于那时的少年来说,是更畅快的江湖梦。武侠小说风靡全校的时候,老师已经无能无力了:总不能将打架斗殴归结于看武侠小说吧?因此禁不得。而且我猜老师也舍不得禁 —— 难得这些孩子还看看书。
1997年岁末,市面上忽然多了一大批奇怪的旧书,多是有关政治人物、黑帮人物和娱乐明星,或几者兼有,书皮通常会用极其醒目的字体写着“揭秘”、“内幕”,当时那种设计很有视觉冲击力,若有所指的书名更是引人想入非非,你会错觉这些旧书如同一把神秘的钥匙,将带领你开启一个不曾想象过的世界。
当时曾有一本讲述张国荣与谭咏麟争夺香港乐坛一哥的书在校园广为传阅,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帮派、资本、娱乐圈这些原本平行的领域之间,竟然有着如此复杂的交叉,甚至是盘根错节。香港大概就是从那一刻起开始变得意义丰富,不再是艾敬《我的1997》里那种平民化的视角所看见的一个个关键词。回归后的第一个春晚,王菲和那英合唱了《相约98》,将一种正确愿景做了诗意的表达,打动了很多人,“马照跑,舞照跳”在大众娱乐生活中开始有了注脚。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香港,印象颇深的是报刊亭仍然大量摆放印着“揭秘”、“内幕”之类的书。随手翻翻,有些“内幕”因过于言之凿凿而显得滑稽可笑,为追求戏剧效果不惜罔顾常识,作者似乎也不觉得读者真的会相信,不过是一消遣罢了。这些书旁边摆着的是大量的色情杂志,政治与色情的距离如此之近,不知是真理,还是偶然。随手买了几本回酒店,书太新了反倒有种疏离感。后来我在酒店露台看着香港的街景,总是觉得旧了 —— 或许是被我们看旧了,也或许它从没变过,只是我们变得太快了。
曾经以为20年是个比香港还要遥远的概念。而此刻站在曾经的遥远里,好像只记得开始和现在,中间的很多情节都丢了帧 —— 就像1997年的录像带被转成了 VCD,再被上传到互联网时代后,又要费尽全力地在2017年把自己修复成 1080P 一样 —— 生怕落后于时代,被快速的人们所忘记,却又总是觉得那些闪烁的颗粒之间遗落了某些之前从未留意过的情节。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从他人的故事里找寻到一些,关于这个时代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