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莹,1994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硕士,现于牛津大学读博,学业之余从事创作,曾任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
昨天夜里,奎恩的几个朋友都来过了。她们在坞房前的草甸上铺了一张灰扑扑的毛毯,逐一坐到了毯子上。小百利、柠檬水、日本的清酒,都被依次地打开,大伙儿把纸杯碰成一捆米白花束,叫奎恩常回玛格丽特玩。“过阵子你们都要来吃乔迁晚饭,我一定会备好月饼。”她回应道。当脚边的草甸也变得乌黑,她们在毛毯边点上了一圈小烛火,火苗就那样摇晃在甜涩交加的晚风里,这时附近街区的派对开始了,不远处有人合唱着:“不知为何,我就这样逃离……”她的朋友们也放开了嗓子:“请将泪水留——待——来日,留待来日——”
奎恩没有跟着哼唱,为了和朋友们口中的那个罪犯保持距离,她也不得不从这里逃离。她们不止一次地告诉她,他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施害者,理应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两个月前的那件事就算得上是刑事案件。她也想象过自己和她们一样激进,目睹他俩之间浓烈的硝烟、绵长的悔意,还有一些她应得的补偿。可是,一个夏天过去了,她还在为他是不是嫌疑犯而多虑:她捉摸不清故事的全貌,某些记忆凭空消失了,似乎有一把无形的长镊子,从她脑中精准地取出了最关键的那部分,又把一捆真假难辨的说辞植入大脑。“让病毒都滚蛋吧!”她提起脚边的清酒,再次给朋友们满上。一个中国朋友叫她少喝一些,第二天她还要去打第二针疫苗,其他朋友也附和着说:“已经不早了。”
“一切都打理好了吧?”署名为萨意的人发来几条消息,“我在门外,黑铁门这边。”
奎恩赶紧套上一条黑色过膝卫衣,抽出脖子后那把红褐色的鬈发。她匆匆跑下楼,瞥见大门外停着一辆象牙白的货车,司机从驾驶座跳到地上,努力扯顺身上的荧光夹克。
“两小时前我就来过啦。”司机对着奎恩喊。
“不好意思,”她走出门房,捏紧口罩上的金属片,说,“我睡过头了。”
“不要紧!”他把鸭舌帽檐往脑后一掰,露出暗棕色的前额。
“跟我上阁楼吧。”她说。萨意跟着挤过门房,沿着一座枫叶红的长楼走了几步,说:“这四面的建筑真像中国麻将牌,都长条形,背面的颜色还差不多。”
“这是我住的排居楼。”奎恩拐了个弯,来到另一排通体砖红的长楼。
“排,排排,排居楼,”萨意凑到门边的黄铜牌匾边上,搓着下巴说,“这是新楼哟,这么好的住所,你干吗搬家,南边可不太安全啊。”
“想换个环境。”奎恩进门说。她也是这么和朋友们解释的:在这里待了一学年,几乎没离开过方圆半英里的地方,是时候去城南住一段时间了。萨意夸她很有胆量,就像他当时跑到外面去,在印尼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又一个人去马来、加纳、利比亚,后来又在伦敦待了几年。他们走进一条铺着猩红地毯的走廊,过道没什么光亮,到了廊子的尽头,背后的声控灯才逐一点亮,萨意张开手臂,巨大的黑影投射在眼前的步梯上。“宽度,一米二,”他说完低头看了一眼脚底,往大理石台阶上磨了几下脚掌,说,“这么滑。”
奎恩一路踩着影子走到了阁楼,随手拎起门边的消毒液,转身给他挤了手指甲盖大的一些。他搓了搓桃木色的手心,扫视了一圈她的房间。床边的塑料袋鼓的和瘪的都有,每个袋口都欹斜着,露出没有摆端正的小东西。她还没决定把哪些袋子腾到行李箱,这些本该在昨晚就整理好。垃圾也都没倒,门后的毛毯皱巴巴的,易拉罐和酒瓶都堆在上面。昨晚她喝得太多了,一点也不记得最后是谁陪她上楼的。她们喝完了最后一轮,夜色已经漆黑一片了。她只记得自己梦游似的跟着几个人影跪到地上,轻手轻脚地把空瓶垒到一起,捻起毛毯的四个角。像这样,她总觉得自己身处一团被随意揉捏而成的人事里:草甸、坞房、波浪、晚风中的火苗子,还有和那个男人相关的所有忽明忽暗的碎片,它们的外形那么逼真,发出高低不一的声音,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这么多书啊。”萨意看着天窗下的一整面书脊,问,“有大箱子吗?”
“没有,只有一个大行李箱。”
“你打算一个个地拎塑料袋?”萨意说,“那太花时间了。”
“我绝对能在半小时内搬完。”她跨过塑料袋走到床尾,跪到一包四方袋边上,旋开袋子中央的小气阀,拿那支比小臂还短的抽气筒对准气阀,嘎吱嘎吱地不停拉扯着,袋子里的被褥慢慢变成了干瘪的鳕鱼片。
“哎,别慌张,这又不是什么考试。”
“我可没慌。”她抬头问,“搬家费是按小时算的吧?”
萨意哈哈笑起来,说:“搬家么,花多久总是很难说的。”
“新房东在等着我呢。”她往气阀上套了一颗密封纽扣。
“我这就去拿纸箱。”他并着拇指和食指,用她不熟悉的语言吐了几个音节,似乎是一,二,三,最后总结说,“起码四个。”
萨意下楼了,奎恩掰开口罩喘了一口气。她从紧绷的书脊中央抽出那本封面明红的厚书,匆忙塞进行李箱的夹层。书中夹着几份文件,最后一页是那个中国朋友的手迹,字体是Goudy
old Style,比最常见的Times要圆一些,扁一点。在靠近结尾的地方,她说奎恩变得“真令人担心,事发之后,她在练口语时总是心不在焉的,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开朗外向的性格了……她的眼神经常飘向……”。类似的陈述也出现在其他文件里,她们坚持说那个人是个惯犯,肯定对很多人下了手。奎恩不敢看这些语伴的神情,愤怒中略带着歉意,她解释说自己还没完全恢复记忆,接着继续复述汉语教材里的对话,比如布兰卡说了什么,古波是怎么回复的。等她们都离开了,她才不由自主地发抖,尝试着通过别人的眼睛去了解一个受害者的模样:一个十七岁的红发女孩被黑啤和雪利酒灌醉,然后像一只垂死的乌鸦那样被一个男人摆布。
不过,她还是回忆不起这些“至暗”的时刻,记得的是那天晚上,她像现在这样从衣柜里拿出所有的裙子,一把将它们摊到床上。她选了一条银灰色的派对短裙,把一对鸳鸯形的玛瑙耳坠扣到了耳垂上。在酒吧门口,几个服务员不停地从她面前走过,轻声把托盘上五颜六色的威士忌、干红送到不同的圆桌去。没有人招待她,他们大概还受着疫情的影响,不会主动地接近顾客。她走了进去,到处是油黄的微光,四壁和天花板上拼贴着歪斜的海报。很巧,有一张海报和那本历史小说相关,镀金的Quo Vadis浮现在一片橘红色的火焰中,莉吉亚和戴着金色头盔的男人在火光里深情对视。她忘了这个男演员叫什么,泰勒,或者罗特什么的。她要见的人就坐在这张海报的斜前方,穿了一件海蓝色的polo衫,淡棕色的头发被黑发箍拢向后侧。先前几次她在学院的小教堂看到他,白衬衫外套着深色大衣,背朝合唱团和晚祷者适时按下管风琴键。后来他也出现在拉丁文圣餐仪式上,还是同样的装束,只不过和她一样坐在祷告席。
他起身和她握手,说:“放心,我早上刚测过,阴性。”
“我刚打完第一针疫苗。”她拂住裙子的后摆坐到他对面。
“我到现在都还没打,”他笑着问,“奎恩,我没叫错吧?”
“古温,可音,奎恩,都可以。”她摘掉口罩。
“Wojciech,沃切克,华司科,乌杰丝,”他解释自己的名字在不同语言里的发音,问,“你喜欢叫哪一种?”
“快乐的战士。”她说。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像是搞军事的。”
“你名字的前半部分是战争,后半部分是快乐。”她说。
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原来你懂波兰语。”她没有接话,继而聊了聊背后那张1951年电影的海报,问他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他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只是补充说他父亲有一张纪念显克微支的绿邮票。奎恩不再提及小说和电影的细节,她对此过于熟悉。刚开始学波兰语的时候,她就尝试着通读Quo Vadis的原文,那是华沙的一家出版社印的,封面通红,中央有一些擦破的痕迹,书底有一根饰有金色燕尾牵绳。
“你来自哪儿?听上去一点不像华沙人。”他问。
“威尔士和中国,布里肯小镇和南京。”她回答说。
奎恩的妈妈来自金陵小镇,十八岁去威尔士帮忙料理兄弟开的中餐馆。在那儿她认识了奎恩的父亲,他在镇上的打印店干活,为当地的店铺设计一些菜单和广告单。他俩是在讨论菜单时熟络起来的,入冬了,她往菜单里添了几个适合冷天吃的菜,他帮着拍了海鲜砂锅和铁板牛肉的摆盘照,又登门把菜单的样稿送去。在一起三年后,妈妈在附近的福利学校找了一份教职,照顾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
后来奎恩出生了,父亲在小镇南部买下了一座小石屋。屋子只有一层高,四壁被水泥抹得发黑,像长年被雨水浸透那样灰暗,不过,两侧倾斜的屋顶是红棕色的,木制门框的颜色更浅一些,有着明红的波纹。门外是一面和肩膀同高的灰围墙,墙外的石子路通往镇中心的学校和小教堂。每天清晨,荞麦粥和香蕉都会被摆在靠近前门的木方桌上,吃完了这些,父亲常常把黄油兑到浓茶里,那股奶香味会一直弥漫到午后时分。到了傍晚,妈妈就把晚饭摆到靠近后院的圆桌,通常有芹菜水饺、腊肉和烤茄子。奎恩坐在离火炉最近的位子,抬头就望见院子里低矮的红辣椒、西红柿,不远处无人问津的太阳花丛,还有远处茂密的柏树林。林中坐落着两户做帆布的人家,他们之间隔了一处叫“奎林之泪”的湖水。湖中经常浮动着带着黑斑的灰鱼,它们的鱼鳍上常透着蓝色荧光。要是在夏夜,林中的萤火虫在暗处轻盈地浮游;入秋以后,长脊海蝎子偶尔伸出带着长刺的头颅,在靠近泥岸的浅水里栖息。到了周日下午,父亲会带着奎恩到湖边钓鱼,林中时常下雨,妈妈每年都要用麦草编织两顶新的风林帽,它们的边缘比普通的遮阳帽宽一些,在底面还缝有防水的帆面。奎恩戴着帽子回家的时候,大衣还是干的,父亲的就说不定了,他的肩膀和后背经常被打湿。她还记得,他总是在进门的石阶上展开宽厚的肩膀,蜕皮一样地脱掉黑色大衣,把它挂到木门后的铁钩上。妈妈会在地板上铺上一条白毛巾,对折起来,让大衣上的水珠落到毛巾上,那样就不会有滴答的声音。
到现在,奎恩还没把那件事告诉妈妈,那个天天给孩子们翻好衣领的女人,和父亲一起创造了安详家园的四十五岁女人,会怎么表达她内心的惊骇?
“哎,大不大?”萨意在门外提起一摞比他高的棕色纸板。
“多少钱一个?”奎恩问。
“五块。”他沿着纹路把它们折成纸箱,往底面缠了几圈透明胶带。
“三个就够了,我有个琼·路易斯的袋子,能装不少小东西。”
“行吧,”萨意小心捧起一堆书,说,“你会讲这么多语言啊,你爸妈也精通很多种吧?”
“没有。”她说。在家里,父亲跟她说英语,有时候带上一些方言,而母亲只说英文,她说普通话不标准,不让奎恩跟着念。
“都能读整本的中文书了,真不简单。”萨意捧起一摞中英对照的《史记》。
“不过是从小就学罢了。”奎恩把另几包鳕鱼片似的衣物袋塞进行李箱。
“这是什么语?”萨意问。
“左边是法语,右边那几本是波兰语。”
快乐的战士捏着酒杯细长的高脚,前倾着身体问:“告诉我,你怎么会说波兰语?”
“中学学的。”她说,“不过我的第一门外语是意大利语。”
他又要了一杯黑啤,吞了几口,没有打断她的回忆。她告诉快乐的战士,小学的外教这么教她,讲意大利语就是用舌尖在门牙底部折五边形,她尝试了几天,很快就找到了入门的感觉。外教在退休前送了她一本《麦当娜·菲亚梅塔的挽歌》,“
Elegia di
Madonna Fiammetta
,”她噘着嘴唇慢慢吐出每个音节,“不过,我对这个故事一点不感兴趣。”奎恩显得轻松愉悦,说第二门外语是拉丁语。第一次听到拉丁语的时候,她觉得牧师在用嘴巴剔鱼刺,“不是三文鱼的鱼刺,是长脊海蝎子的刺,那很好玩。”她请求父亲送她去学拉丁语的夜校,这样她就可以听明白圣餐仪式的原文,父亲答应了。后来她慢慢学会了法语和波兰语。“说法语是最容易的,只要噘起嘴唇想想家里满屋子霉斑,就能完美表达那种感觉,哦,带着怨意想要论争的感觉。”她喝了一整杯黑啤。快乐的战士说奎恩很聪明,她从没怀疑过这一点,她的父亲也这么评价,因为她总揪着菜单样稿上的毛病不放,埋怨道:“古乐先生,这里要用a啊,一盘菜又不是只有一只蜗牛。”父亲托着腮帮说:“瞧瞧,她又觉得自己聪明了。”她咯咯地笑起来,用铅笔在纸上注明:“语言顾问:打印员的女儿——奎恩。”
“该你了,”奎恩问,“你什么时候学的拉丁语?”
“小学,那时候我们都要学。”快乐的战士说,“我在一个奇怪的男校读书。”顺着她的话题,他聊了一会儿拉丁语和波兰语的异同,时不时捻几下酒杯的高脚,最后他描述了挪威语给他的感觉:“音符碰到玻璃片后一片片轻快地滑落。”奎恩大笑起来,她喜欢听到这种比拟。
“差不多了吧?”萨意把门后的空瓶都放到了垃圾桶,地上的袋子都已经装箱了。
奎恩使劲拉上行李箱的拉链,萨意笑着说:“哎,你别慌张。”
“我可一点没紧张。”她反问道,“我的紧张写在脸上吗?”
“哈哈,不在脸上,可是在眼睛里啊。”萨意嚓的一声用牙齿扯断了胶带,说:“歇会儿,喘口气。”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看着萨意打开天花板上的倾斜的天窗,清风一下子涌了进来。秋天已经来了,窗外的爬山虎露出了焦黄色的边缘,叶片也开始掉落,藤条之间变得松散。这些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回想盛夏那会儿,它们曾经那么紧密地排布在她的床头,叶面上一点斑点也没有。的确,她忽略了时间的变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蜘蛛已经在窗框边编织了几张浅灰色的小网,网上沾上了密密麻麻的小水珠。她站了起来,取下窗边新拆的除湿盒,凑近看了看,底部已经积了一层水。是啊,秋天已经来了,阁楼的湿气更重了。她希望这里有一个壁炉,就像她在威尔士的家里那样,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在火炉边烘干变潮的书、枕芯和毛毯,要是手背变干燥了,妈妈会帮着抹上一层肉桂味的精油,cinnamon,cynamon,cannella。
“你去楼下等着吧!”萨意说,“我来搬。”
“谢谢。”奎恩提着琼·路易斯的环保袋东摇西摆地下楼了。她转身看了一眼萨意,他屏着呼吸捧起纸箱,用脚碰了碰台阶,才呼出一口长气,好像不想让她留意到似的。奎恩走到车尾,往车厢里张望了一会儿,角落里有一摞没有用的纸箱,堆得比膝盖高,纸板后露出两个轮子,那可能是小推车,又或者是千斤顶。箱子一个个被抱到车厢一角,萨意掏出一块青绿色的手帕,抹了几下脖子和后颈,大口呼吸了几次,一下子蹬进了车厢,从门后抖开一块硬邦邦的紫罗兰毛毯,说:“放心,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东西,看看——”
毛毯紧紧覆盖住那些箱子,几根麻绳把它们勒得死死的。
“完美!”萨意快速跳下车,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叫奎恩拉紧右上方的把手,她像死乌鸦那样被托举到半空。
“还没坐过这么大的车吧?”
“没有。”奎恩陷到摩洛哥红的坐垫上。
“好好享受吧!”萨意跳上驾驶座。车身启动了,奎恩觉得自己在很高的地方,和两边的橡树一样高。在她的身后,楼群麻将牌似的排成四方形,其中最高的是图书馆楼,平顶上高塔矗立,塔顶竖着一枚乌黑的十字架,再往后看,学院小教堂露出猫头鹰头形的顶部。大半年了,她都没走遍学院,对这儿的印象似乎只是枫叶红,猩红的一片,以及东北角查威尔河岸上孤零零的草甸和坞房。
“小奎恩,你来英格兰几年了?”萨意问。
“一年。”
“有出去玩儿吗?”
“没有。”
“对哦,疫情嘛!”萨意追问道,“你读完书去哪儿?”
“南京,看看能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
“那是你妈妈的故乡吧?”
“是的。”
快乐的战士帮她剔出了黑啤里的几个冰块,问她南京在哪儿,她回答说那是明朝的首都。他朝着天花板沉思了一阵子,说北京是清朝的首都,南京北京都有“京”,“京”是首府的意思吗?她回应说,不完全对,这只是“京”的其中一种意思,“南”是和“北”相反的一个概念。他继续问,那么南京在中国的南方吧?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在明暗交替的烛光里,他深色的眼睑透着一些倦意,而浅色的眼睛却是过分有神,似乎被一种新鲜的东西刺激,想要往前一睹究竟。奎恩摇头说,你猜错了,它在南北方的中间。这确实令人困惑,他托着脑门想了片刻,把身体倾斜到那张海报上去,露出胸口银色的十字架。
“你什么时候皈依的天主教?”奎恩问。
“那不重要。”他说。
“做礼拜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他没有答话,似乎这是个无足轻重,又或许是过于沉重的话题。他转而说他的母亲过分虔诚,父亲是完全不信上帝的,他是个搞物理的,总开玩笑说他俩实现了完美的民主,这样的两个人都可以在一起过了三十年。奎恩想到父亲的世界:“上帝庇护着我们。”他总是这么说,用食指指向头顶,然后揽着妈妈和伞架一样瘦窄的肩膀。妈妈说:“庇护的是你,我只不过是没有脾气。”“是的,是的。”父亲还是满足地说。在镇上的小教堂,他聆听、下跪、默念、祝福,看上去比谁都虔诚。有关建造家园的教义,似乎是这些礼拜的仪式教给他的。她看到一个跟随上帝的父亲,在布道声中反复淘洗着自己的里里外外,在他看来,上帝也确实给了他相应的馈赠:一个来自远方的好伴侣,一个在牛津读书的好女儿。
“这么跟你说吧,”奎恩不加掩饰地说,“我不觉得所有人都知道教义是怎么一回事,要我和闭眼顺从的人一起跨入上帝的怀抱,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快乐的战士对着她敬了一杯啤酒,又帮她点了几杯雪利,问:“你想过在哪里落脚吗?”
“这我怎么知道?”她说。她才刚从威尔士出发,在漫长的公路、赛文河面和密布的灯海中经历了第一次单独的迁徙。未来?她还没有想过,一切顺利的话,过几年她就会在亚洲留下一些足迹,其他的她怎么知道呢?
“你呢,要去哪儿?”奎恩问。
“快乐的战士么,当然是到处走了,可能去意大利,或者东南亚。”
萨意的货车开到了班布瑞街,街头大写的V印在玻璃门上,兽医院到现在还没恢复营业,它的后侧是北巡街,那里藏着一家很不起眼的比萨店,叫小威尼斯,这两个月她常在这里要一份羊肉比萨,比萨是现做的,得花上一刻钟,她总在斜对面的浦路咖啡吧等着,要一杯冰镇柠檬茶,一块不加乳糖的胡萝卜蛋糕。每光顾一次,她就能在会员卡上收集到一个印戳。有时候她一天可以拿到三个印戳,一周下来就能喝到两杯免费的柠檬茶。她不想回到密闭的阁楼,那颗经历了戒严和冒险的心脏快速跳动,使她整个人和弹簧那样反复弹跳在这条街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她这么说服自己,一进阁楼快要窒息,就跟有成群的马往她脸上呼着热气一样,于是她跑了出来,像逃离一场红光冲天的火难。
“马可,我要走了。”昨天中午她又去了一趟小威尼斯,告诉店主她要离开了。
“去哪?”马可问,他还是穿着那套雪白的厨师服,连前胸的纽扣也是白的。
“新家,离这里很远。”她说。
马可照例给她放了两倍的羊肉,说他会想念她的一切,小小的身影,红头发,白口罩,还有一眼就可以看透的眼睛。她靠近烤炉,盯了一眼银器上的眼睛,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从她的眉眼里读懂她的一切,骄傲、羞耻,那些过于直白的气焰和转瞬即逝的感伤。这是真的吗?她难道不是那种善于隐藏一切的人吗?她皱眉头说道,几乎是在喊叫:“可是我眼睛是乌黑的啊,你可以从深黑色里看透什么呢?”马可呵呵地笑起来,说:“你还太小。”她一点也不满意他的答复,背过身翻了翻柜台上的新杂志,封面的标题是大红色粗体,它们排布在几张表情愤怒的人物图上:“不只是出轨,竟然还有这秘密!”她打了几个哈欠,合上杂志,听到外卖订单的提示音嘀嘀嘀响个不停。这不是双周的礼拜六,不然她可以在这条街上逛一会儿自由集市。那些天的清晨,人们支起海蓝色的大帐篷,帆布底下飘浮着鲜花、印着鲜花的明信片,还有自制的木刷、毛刷。37号摊位后坐着一位卖镀金耳饰的老太太安娜,她告诉奎恩自己十八岁到东方冒险的往事,坐上游轮、火车,徒步,一直往东走,走到了华沙,再坐游轮、火车,徒步,走到了北京……北京和华沙真像呀。
“哦,是吗?”奎恩说。她什么也没听进去,但她需要这些声音,需要它们从耳朵里涌进去,再毫无改动地流淌出去,咕隆咕隆的声音,这是第一处和家乡相似的地方,她想起手推车载着农具从窗前驶过,从维修厂过来的几个青年用方言轻快地交谈,他们的腰带上装着不同的小工具,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窸窣作响。
“你在等谁吗?”安娜把耳饰收到四个天鹅绒的黑匣里。
“没有。”奎恩说。
“得回家了吧?”安娜轻声说,“小宝贝,这里收摊了。”
“是的,回家了。”
为了继续收到他的讯息,她做的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赞同他说她醉酒的说法,偶尔模仿他有礼貌的口吻说话。在零碎的一些短信中,他们聊一会儿天,谈及一定程度的性与爱。后来她瞒着朋友们又见了他一面,他在唱诗晚祷后脱下西装,站在管风琴边对她说:“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会在希腊,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我就在波士顿了。”他告诉奎恩,他是那种在原地栖息一会儿后就启程的人,从这里毕业后,他会去夏威夷,悉尼,或者南非。那种不合时宜的,由离别引起的感伤充斥了她的大脑,她原本可是要和他对峙的啊。他邀请她到他房间去谈一谈,像那天晚上一样,他把她领进房门,先是抱了她一会儿。她靠在他的肋骨上,想象着自己的处境:刚抖动翅膀学会起飞的罗宾鸟,碰到玻璃柱后迅速坠落,那个和挪威语有关的比拟变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她卸下发绳,把红卷发解了下来,努力遮掩自己乌黑的眼睛。聊到最后,他的记忆也还是没有改变,就像在那天一大早说的,他们只是都喝多了酒,而她当时也没有不愿意。
“这是哪儿了?”奎恩问萨意。
“南边啦!”萨意沿着一个大圆盘,把车拐到了三条分叉路中最中间的一条,低矮的餐厅不断地浮现,店铺的门楣上印着咖喱的摆盘照,阿拉伯文弯曲的钩形,再往前看的时候,透明玻璃窗内立了一座镀金的菩萨塑像,那或许是家按摩店。
“不是南公园吗?”奎恩问。
“啊,南公园啊?”萨意拍了拍方向盘,说,“那就是去联和街的另一条路了。”
“我要去一片很大的绿地,很大很大的……”
“是啊,走错了,得挑隔壁那条路走。”
“你怎么还往前开?”
“别慌张,我在找能掉头的路口呢!”
车子往一个雾霭渺渺的远方开去,奎恩的头皮渐渐发麻,那个迷雾一般的身影把缀满银色亮片的小裙丢到她身上,说:“现在你可以走了。”走去哪儿?她摸黑走进枫叶红的排居楼,踩上猩红长地毯,微小的电流毫无声息地在脑海蔓延,在她酒醒以后,他在短信里这么说:“哦,我忘了,你很容易醉酒,不是吗?”毫无准备地,那些微小的亮光轰隆地爆裂着,她觉得自己身处电闪雷鸣的中心,很快就要迎来狂暴的风雨,然而实际上,那些巨大的痛苦一直都很安静,没有什么呼喊,连哀怨的细语都没有,安静到像围观一次身在其中的默片,他的好奇心是虚假的,看上去无害的polo衫也是虚假的,连认真回答南京在南边的推测也是虚伪的,什么是真实的呢?她可怜的模样,旁人看来在有限的时间里自得骄傲的姿态,以及可以预测到的苦头,任何人都知道的大限将至,别慌,萨意的声音从她的耳朵里钻进去,别慌张,她握着门上的把手,头顶吱吱发痒。
“开进来!”一个黑发女人在路边对他们招手,身后的绿地在皑皑迷雾中泛着金光。
“好,好,没问题。”萨意探出头说。
女人背着绿地走向一片低矮的居民楼,拐进两个独立小楼间的分叉口。车子颠簸着拐了进去,穿过一座拱形的木架子,架子上的豌豆花、叶和藤蔓刮擦着挡风玻璃。
“快点,派对快开始了。”女人喊道。
车门被打开,奎恩被抱到地上,她听到女人咳嗽了几声,说:“小宝贝,你终于来了。”奎恩问萨意能不能用推车,他搬下一个长木板,放在四个轮子支撑起的小台面上,什么拉手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把柄,板上粘满了黑色的霉点。
“没必要,这有电梯啊。”女人瞥了他一眼,说,“哎,你进不去的。”
“好的,好的,”萨意略带歉意地对奎恩说,“真遗憾啊,没办法用推车了。”
“不要紧,非常感谢,”奎恩说,“一共多少钱?”
“不急,”萨意卸下一圈圈麻绳,把箱子搁到前门,他听到身后的鸣笛声,赶紧跳上驾驶座给车辆让路,说,“小奎恩,再联络,再联络!”
“你也没入场券。”女人对奎恩耸了耸眉,她的眉毛都被剃光了,只留下两道眉峰高耸的棕色眉粉。
“什么派对?”奎恩和女人一起推着纸箱,走到电梯口。
“去年的,去年没搞成的——你几岁?”
“十七。”
“最好别溜进去,每年都有人被灌酒的,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向来对派对没兴趣。”
“你给我看看,现在花园里有人吗?”
白烟从两排红帐篷钻到半空,奎恩说:“只有两个抽烟的保安。”
“快进来,快!”女人将夹着后门边的餐车推进电梯,匆忙把大箱子抬上餐车,电梯一开就推着餐车跑到走廊的尽头,在一扇红棕色的木门旁停下,把车上的大箱子丢到门前。“别被发现了!”她气喘吁吁地说着,肚子上的赘肉在黑雪纺衫里不停地抖动。奎恩看着她把另外几个箱子扛上车,不停地在长廊上推车小跑,从一端跑到另一端,又跑回来,她不知道谁更孤独一些。
“去吧,晚上够你收拾的了。”女人递给她一把银色钥匙。
“我还得出门。”
“干吗去?这会儿附近可不太安全。”
“去打疫苗。”
“第二针?”
“对。”
“看样子我这把年纪的人都打完了。”女人提高了嗓音说道:“祝你好运,红头发的小东西。”
奎恩在纸箱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电话和邮件地址。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拖走她的东西,她想,不过,她还是把电话涂黑了。她走到电梯边的步梯,几个穿露脐上衣的女孩走上来,迎面对她说了几声借过。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一个穿着金色亮片短裙的女孩,她护着左臂,应该是刚打完疫苗。这些人都没戴口罩,奎恩快速跑到楼下等公交车。车子迟迟不来,越来越多的松鼠跳到站台的平顶,她的头顶咚咚咚响。她有点害怕,担心这些松鼠都会敏捷地弹跳到她的肩膀上、头上,像弹性十足的线球,毛发浓密。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到了后座。司机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她转念想到萨意,他已经发了好几条付款的消息,最后一条是一串双手合十的表情。她想立马转账,不过手机自动关机了。她又想起那个胖女人对萨意说的:“哎,你进不去的。”可怜的萨意,她想,他会反复回想被人拒之门外的瞬间吗?或许不会。她想象着,在驶离小路的那一刻,他立马叼起一支烟,悠闲地哼些调子,或许他才不会去管这些房东怎么看他。他帮客户搬了家,做了他该做的,也即将领到给他的报酬,至于其他的事,别人的脸色,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她希望事实如此,这样就没有不必要的恻隐和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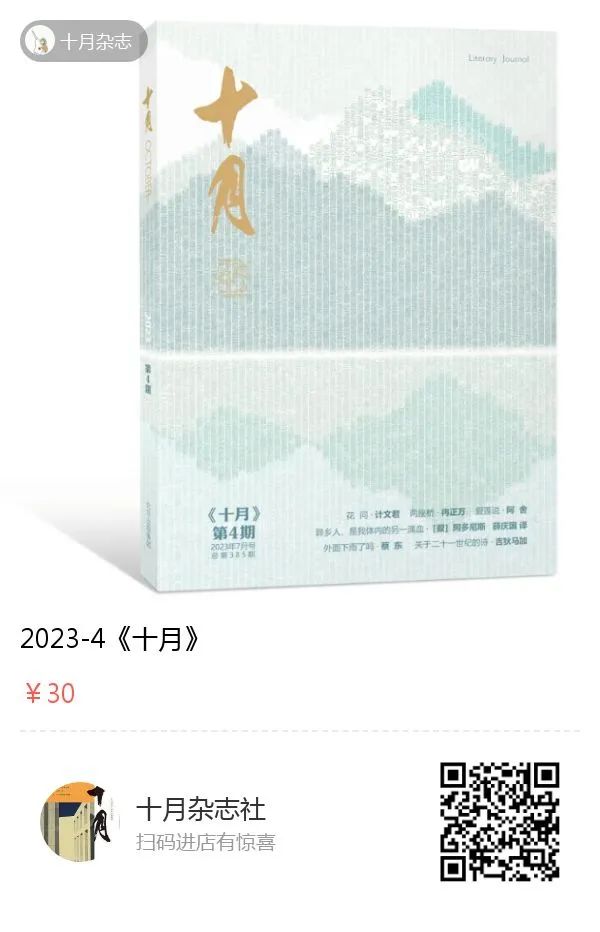
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