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利党的象征“皇家橡树”,
英王查理二世曾经钻入这颗树洞里躲避圆颅党和克伦威尔的追捕。
* * *
托马斯·曼的
《魔山》
实际上是一部带有历史范例性质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精明且简洁地概括了
博林布鲁克圈子
反资本主义心态的大概轮廓:
文化
意味着真正的心灵体悟,而
文明
则是机械的传动。
事实上,无论是古典范式还是人文主义范式,直到今天在解释
亚当·斯密
时都坚持
布克哈特
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中首次给出的扭曲设定,将历史归纳为国家、宗教和文化三要素之间的缠斗,三要素构成了无可侵犯的神圣三位一体,其中
圣灵的地位
尤其重要,甚至不容时间侵犯,至少他们的内在情感是如此认为的。
逻辑结论由此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人类历史的叙述或者说世界史叙事最终只能是“内在的”,并且如同三位一体的神圣结构所呈现的那样,只能是从一个时代“抽取幽灵”,借此来启示另一个时代。此种情形之下,便无法指望
克罗波西
(Joseph Cripsy,芝大已故著名教授,亚当·斯密的研究专家,生前担任列奥·施特劳斯的文学遗产执行人)
和
波科克
能够对亚当·斯密进行一种“无偏见旁观者”式的解读。
问题本身实质上是二选一的,要保持或者捍卫政治的神秘特性和尊严,就只能将亚当·斯密视为头等敌人。不过,至少应当仔细斟酌一下,亚当·斯密对政治所施行的“祛魅化”手术,究竟是因为他太不了解政治了,还是因为他太了解政治了。就此不妨听一听温奇的中肯评论:
“就政治人物的动机、野心和意图来说,读者会感到,亚当·斯密的政治学是怀疑论的、悲观的。同样,就那些认为人应当不断地增加对自然的控制,包括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控制,以改造社会的观念来说,
亚当·斯密政治学在对待过去社会的价值并没有乡愁式的,因此对将来的探讨也不会是乌托邦式的
。人性和人的理性看来不太可能完成的事情,超个人的历史力量也不太可能依据某种规划将其完成。社会是变化的,变化有可能促成社会进步,就像不久前发生的那样。社会的增益必定只能是一种‘净数’,是以许多
旧时日的德性
为代价的。人们的经济活动将会促成一些强有力的原则和准则,将人们在社会中联系起来,而在政治领域,原则和准则的力量则要弱很多。没有什么固定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兴衰循环应当中止。在当前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偶然的和特定的环境会起到作用,而且总会存在整合和稳定的力量,
但历史不乏失败、停滞、愚蠢和非正义的例子,这一方面是对人类自满的警告,另一方面也是给人类智慧的行使创造空间
。”(
D. Winch,
Adam Smith
'
s Polit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
,第
182
页)
麦考莱
用在
克拉林顿
身上的话若是转用于汉诺威王朝之下的博林布鲁克身上,应该说要更贴切一些:
“……这位宰辅乃属于一个逝去的世界,是过往时代的遗老,
他所代表的是过时的思考模式、过时的罪恶和更加过时的德性
。他遭受过为时漫长的放逐,这让他成了他出生的这个国家的陌生人。他的心灵因冲突和个人际遇而灼烧着,使得他较之在内战开启之际更坚定地反对民主和宽容路线。
他对古老白厅的那种优雅暴政心怀乡愁
;在那位圣徒国王统治的日子里,国王剥夺了人民的财富和耳朵,不过放过了他们的妻女;这位宰辅无法适应一个拥有后宫但没有
星室法院
的宫廷。因此,他所采取的政策使得各方对他的恶感日甚一日,君主爱娱乐远胜过爱特权,而人民则担忧王家特权远胜过担忧王室娱乐;最终,宫廷对他的恶感超过了反对派领袖,议会对他的恶感则超过了所有的宫廷弄臣。”(麦考莱,“威廉
.
坦普爵士”)
博林布鲁克乃在汉诺威王朝之下彻底沦为在野势力,
他对此命数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他便专心构筑英格兰的政治反对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乃兼具议会反对派和超议会反对派的双重特质和双重诉求。
“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舞台乃是小册子和周报的天下;反对派的政治效能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得以坐实;也就是在这个舞台之上,人们发现博林布鲁克圈子对腐败的关切远非仅限于
沃尔波
其人、其事,而是远远超越了这些。博林布鲁克对沃尔波不依不饶,在他眼中,文化腐化、社会腐化和政治腐化乃在沃尔波这里道成肉身,人们常常说,这是纯粹恶意的理性化表达而已。然而,事情可绝非仅止于此。博林布鲁克完全可以像尼采在‘瞧,这个人’里面说的那样,‘我绝不搞人身攻击;我只是利用人,把这个人变成倍数极高的放大镜和哈哈镜,令那日渐渗透近来的普遍灾难变得人人可见,否则便无法除之。’……
博林布鲁克及其圈子乃以诗篇、小册子和报刊为武器
,不过,他们所写的一切都并非对当时英格兰的准确评估,对英格兰之未来的预测更是破落不堪
。他们策动的大量攻击之词,对沃尔波难有公平可言。在我看来,博林布鲁克式的先知言说所包含的价值和信念,并不比他攻击的那些价值和信念,更有价值,更值得人信从。”
从这个极为现代的角度观之,博林布鲁克可以说是
现代政治反对派
之基础诉求和理想范式的开创者。在彻底沦为政治反对派之后,博林布鲁克致信威廉
.
温汉姆爵士,阐述了
1710
年到
1714
年间置身自己那段生涯转折期背后的观念和态度:
“
1688
年革命
之后的,我们政府当中普遍盛行的原则,在我看来,就是要毁灭我们的真正利益,就是要令我们过分地卷入大陆事务,就是要令我国人民陷入困顿,就是要放松教会和国家的体制纽带。我认为托利党乃是土地利益的中流砥柱,并无相反的利益诉求融入其中。辉格党……则是依托长老派和其他的教派,同时也依托银行和公司体系,当然包括荷兰在内的盟国体系也是辉格党的依托。”
很显然,博林布鲁克圈子的“现实政治”取向乃是为这个经济地位相对沉降的落寞阶层以及小商人、小店主群体展开政治代言,为此,他们严厉反对
丹尼尔·笛福小说中或者霍布斯自然法体系当中呈现的那种绝对孤独但也因此具备强劲和正面的立法能量的“个体”观念
,并转而诉求“事实上的个人”,确切地说,他们并不反对、也并不抵触英格兰社会传统中的个人及其自由观念,但他们的个体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无论是保守的还是现代的)中的“自我”,“事实上的个人”,或者说是靠着眼前的常识支撑起来的个体。
置身
18
世纪上半叶
的疾进且普遍动荡的社会潮流当中,必然会对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实产生绝望和恐惧。
这样的恐惧并不是来自
霍布斯
那种纯逻辑的和原子式的心理分析,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它所激起的政治情感也不是那种
霍布斯
式的基于强烈自我保存欲望的“普遍战争”,更不是
洛克
的那种“强者的个人主义”,更不会像
鲁滨逊
那样,对于那陌生船只上的“货物”的来源不闻不问,将全副身心专注于朝向未来的建设工作。
相反,这样的恐惧迫使人退却,退却到无路可退的、但也绝对安全和平静的简单生活和简单常识中去,支撑这种生活持续下去、并尽可能使之长久的伦理基础,就是那种以赛亚·伯林所提倡的充满世俗感和淑世智慧的怀疑主义
。
谁能不恐惧一个人人感到害怕的社会呢?不妨说,他们的思路乃像极了
孟德斯鸠
的思考路线,将
免于恐惧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视为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
和孟德斯鸠以及
刚刚经历过残酷的宗教战争的那代疲惫不堪的欧洲哲学家们
一样,在博林布鲁克圈子看来,政治生活应当将“残酷和恐惧乃是首恶”奉为第一原则。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政治理想主义当然是不可能容留
杰斐逊
这样的“政治希望派”的。确切地说,他们乃将“希望”看作是不祥的礼物,并不得不像宙斯那样展露出保守和残酷的面相。
也许他们自己真的不曾意识到此一逻辑的这种必然结果。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恰恰是因为人是极其有限的,恰恰是因为主宰人类命运者乃是太多的罪恶、不幸和愚蠢,所以
人所不能控制的世界的范围将远远大于所能控制的范围
,后者同前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只有面对那如同无路攀爬的大山般坚定不移的困难时,劝人消极隐退才是明智之举。
没错,
杰斐逊在其有生之年就已经经历着深深“孤独感”的煎熬,杰斐逊民主哲学的追随者很快便变得寥若晨星,并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
。
不过,造成此种
垂死局面
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如果不返回到早期的杰斐逊式的农业经济中去,返回到早期自由时代的简单资本主义方式中去,这样的民主哲学就将丧失得到捍卫和恢复的惟一物质基础,只要缺乏这一物质基础,一切的理想都将沦为空谈。
既然如此,那么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承认这个事实上的世界中,一切都已经坚定不移。
然而,博林布鲁克圈子似乎忘记了,在他们一直加以称道的罗马精神中,历史往往不得不与悲剧取得和解;在维吉尔的笔下,罗马精神中最真实、因此也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就是他们善于通过回顾遥远的过去,从而为塑造同样遥远的未来而采取实际的行动;最激进的革命精神与最传统的历史精神总能在罗马人身上取得惊人的合体。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具备
马基雅维利
那样的洞察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愿意具备马基雅维利那样的精神意志。正是这样的意志驱使马基雅维利敢于同“命运”开危险的玩笑。
在此种局面下,
负有保持记忆之责的历史学也开始蜕化为文人手中的审美工具
,他们开始以鉴赏而非批评的态度对待历史;他们觉得历史作品应该表现为华丽的形式,因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发现、确立并承担真相,而只是一种精致的消遣。
萨克雷
在著名的
“斯蒂尔”讲座
的开场白中对此作了直白的天才表述:
“当我们在研究一个过去时代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是去了解政治交易和领导人的性格吗?是让我们自己熟悉那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物吗?如果我们抱着第一种暗淡的意图,那么真理在哪里,谁又相信他拥有完全的真理?”
他宣称,在他看来,我们在历史书中发现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严肃论述都是没有意义的,他通过引用
斯威夫特的《联盟的行为》和考克斯的《马尔伯勒传》
这样一些标准的
旧式神话作品
来表明他认为的历史是什么。
“当我们阅读到那一本本让人赏心悦目的
《闲谈》和《观察者》
的时候,
过去的时代
回来了,我们
祖先的英格兰
再现了。
五朔节花柱
在伦敦的浅滩上伫立,教堂里充满着
虔敬者
;
花花公子
们
在
咖啡店
里聚集,
士绅
前往会客厅,
女士们
拥挤在
玩具店
,
权贵们
在大街上赶路,而
仆从
则拉着四轮车奔跑或者在
剧院
门前忙碌。我认为小说比那些旨在把握全部真理的大部头著作承载着更多的真理。正是在小说式的著作中,我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了印象;那个的社会的习俗,运动,衣着,乐趣,笑声,讥讽——古老的时代又重生了,而我则在这个
古老的英格兰
旅行。即便是最重量级的历史学家还能为我做得比这更多吗?”(转引自,
《英格兰的扩张》
,第二系列第一讲,“历史与政治”,林国荣译,待版。)
延伸阅读
英国史短章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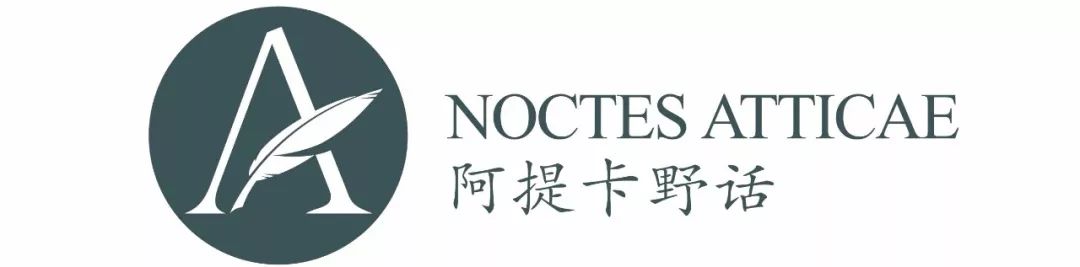

漫漫冬夜,阿提卡乡野蛰居的日子,草草写下这些笔记,是为“阿提卡之夜”。
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
,Prae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