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学校负责一门倍受欢迎的明星课程。这门课连续开了20多年,年年都是选课大热门。就连这位63岁的老教授自己偶尔也会感到费解,这门课这么有魅力吗?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陶国璋 受访者供图
毕竟,翻开它的课程大纲,这门课是这样的——听课,写报告,看电影,读小说,去寿衣店,访问坟场,参观殡仪馆,观察遗体解剖……
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通识课《死亡与不朽》。这门课向学生系统地讲解死亡问题。20多年来的每个学期,它都会带着学生“反思死亡”。
“当人们谈论死亡时,往往容易将其视为‘他人之死’,而忽视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其实,死亡是人类对存在的自我反省,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一生的感受,同样也是一生的促进,这样一来,它也许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陶国璋说,“我教这门课20多年了,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和经验,给那些对死亡话题敏感的学生多一些参考。”
你们才这点年纪,
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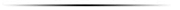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陶国璋的死亡课很受欢迎,最忠实的粉丝是那些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第一堂课开始前,他们总会争抢这门科的选课指标,早早涌进教室占座。
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陶国璋都会感到“有点幽默”。每次上第一堂课,他都会开玩笑地盘问这些年轻人:“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死亡与不朽》 课堂 受访者供图
对陶国璋来说,这是一个过于熟悉的人生命题。他在7岁那年肾脏出现问题,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招呼”。上小学的时候,英语老师教ABC字母表,他在学到L的时候不得不退学住院。后来的校园生活断断续续,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把L和I搞混。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英语字母表的终点就是L。
陶国璋没有学到L之后的字母表,但他比同龄人更早学到,死亡是一件注定的事情。它是一桩每天在医院上演的无可抵抗的自然规律。他常偷偷观察候诊室里人们的表情,久而久之他能一眼看出,谁是偶然生病的健康人,谁是等待死亡宣判的末路病患。
在那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脸上,挂着一种沉重的绝望。他说,相比于疾病带来的痛苦,这种绝望感反倒是自己对死亡这件事最大的恐惧。
“我将自己的精力大量放在哲学上,其实也就是这个目的——用哲学解决死亡的恐惧。”他说。
在课堂上,他也试着让学生体会这种面对死亡的绝望感。陶国璋和学生一起读《潜水钟与蝴蝶》这本书,书中主角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在课堂上,他们试图模仿主人公的状态,试着去贴近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如果自觉未来无望,你会不会想要放弃生命,选择死亡?

《潜水钟与蝴蝶》剧照
这的确是一种接近绝望的体验,陶国璋自己也要花上半个小时,累得眼睛一直流泪,才传递出第一个信息。但让他有点忧心的是,在这堂全是健康年轻人的课堂上,也有很多人轻易地选择了放弃。放弃似乎是一种香港年轻人流行的态度,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没读完大学就选择退学,因为挫折就放弃生命。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不能仗着青春盎然就不把它当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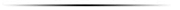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在陶国璋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他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理解死亡不一定非得有一个标准答案。”他说,“信奉科学的人觉得多巴胺的分泌带来了爱情,虔诚的教徒相信每件事都会有神的参与,我们各自找到了一种方法认识世界。”
当然,讲授死亡也是需要“技巧”的。在死亡课的课程任务里有一项“参观殡仪馆”。陶国璋说,一开始没人愿意去;后来他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在学生写给陶国璋的参观感受里看得出,年轻人对这个素日陌生的话题多了很多切身感触:
——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坟地墓碑看得出这个人的生前,有的墓碑镶龙雕凤,也有零星的墓碑无人认领。安躺在内的先人,可有想到子女会怎样纪念身故后的自己?可会与生前所受待遇有出入?真耐人寻味;

——棺木的花款之多,手工之美实在令人惊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棺木的价钱。当听到其中两具棺木高达100万港币的时候,我不禁下意识地走远了一点,这次并不是忌讳死亡,而是避免自己因破坏了它而破产……
在回程的巴士上,陶国璋和学生们聊天,大家会选择如何安葬?这引来了七嘴八舌的反馈,有人说自己怕黑,所以不能土葬;有人说自己不喜欢虫子咬,土葬也不行;还有人说自己怕热,没有办法接受火葬。有人觉得关在小小的龛位里太闷了,提议选择“生前葬”,在活着的时候与亲友做真情流露的对话,或许比生死相隔的纪念好些。全车人嘻嘻哈哈地讨论了一路,几乎要忘记这原本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会刻意规避的沉重话题。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遗体,但他们却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
“死亡这回事,我一直觉得很遥远。香港女人的平均寿命有86岁,现在我20未满,为什么要担心呢?现在我开始明白,仗着青春盎然而不把它当回事,其实太不成熟了。”曾选修过《死亡与不朽》课的学生金露说,“我想着手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对这个世界多些影响,让自己有感不枉此生。因为据说人有二次死亡,第一次是自我肉体的消亡,第二次是所有认识自己的人的消亡。这么说起来,如果逝世后,自己仍不时在后人脑海中浮现,未尝不算一种安慰。”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入殓师》剧照
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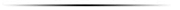
每学期《死亡与不朽》的最后一堂课,都是陶国璋和谢建泉医生共同主持的“生死对谈”,这一期的主题也固定叫做“未知死,焉知生”。一个从小得病的哲学教授,和一个在临床亲历许多死亡案例的医生,与学生坐在一起探讨有关“死亡”的心得。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陶国璋说,“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偶尔我会有点羡慕谢医生。和我不同,他是一个有虔诚信仰的人,他相信神的存在。这让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更多精神支撑。”陶国璋说,“相比之下,我是很理性的,我信仰哲学所提倡的怀疑精神,很难被说服。我念了好多理论,很多时间里我都没办法安顿自己的死亡观。”

一些线下的死亡体验馆颇受欢迎
不过,与年轻人一起学习的这门死亡课,也终于改变了陶国璋。他说自己过去不会主动与人攀谈,上完课就离开,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他说:“但这些年我对年轻人的关心多了很多。现在的我会希望能够多跟他们倾谈。这个亲近世界的过程,让我有一种‘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感觉。”
2015年,陶国璋正式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但是休息了没多久,他又决定重返学校,继续教课。除了《死亡与不朽》,他所讲授的课程还包括《爱情哲学》和《幸福论》, “比退休之前还要更忙些”。
陶国璋说,这堂讲述死亡的课程让他感觉“非常享受”。“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现在我相信,再大的绝望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他说。
只是对学生来说,死亡课也许没那么享受。不止一个学生提到《死亡与不朽》这门课打分很严格,能在死亡课得高分的学生凤毛麟角,“要么死亡,要么不朽”,“九个死亡,一个不朽”。
事实上,“死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陶国璋一直以为课程打分要严格符合学校规定,一门课只能有5%学生得A。直到他最近跟其他老师聊天,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部分老师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数字规定。
“现在我也学会轻松点了。”他说,“在死亡课上,希望更多的人能得到‘不朽’。”
本文由G.P.A经授权转载自每日人物(ID:meirirenwu),作者李斐然。

合作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G.P.A 保留所有权利
后台回复关键词获取干货
懒癌晚期丨自律丨金融职场丨Office丨读书
毕业演讲丨求职秘籍丨留学丨时尚丨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