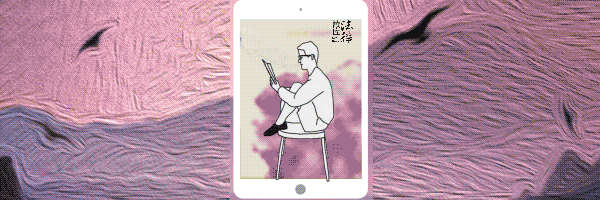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作者:
陈文凯
在去年的年底,韩国block b组合成员朴经在推特上直接点名炮轰一系列歌手,表示对于“机器人刷榜”这一在娱乐圈已经众人皆知且长久存在的现象的一种抗议。
这一行为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但是事情的发展在之后发生的变化,被提到的歌手所属公司纷纷否认曾经实施过"机器人刷榜"行为,并表示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名誉,同时朴经所属公司发表了道歉声明。
时间到了今年的三月底,又传出一位朴经炮轰歌手的所谓刷榜的一系列"证据",暂且不论这些“证据”是否是事实,但这一现象不由得引起人的思考。
二、“机器人刷榜”与道歉声明
在文章的起始,我们首先需要对于“机器人刷榜”这一行为有个基本的理解。
这一行为一般指的是娱乐公司寻找相关的第三方公司采取如大量购买虚拟账号的方式来冲高公司歌手歌曲的点播次数。点播次数在大多数的音乐平台直接决定了歌曲在平台排行榜上的位置,而根据传统营销学的原理,越高的位置往往会吸引到公众更多的关注。
朴经所属公司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道歉声明,很多网友对此非常愤愤不平,其实从法律意义上来看,其公司所做的行为是很正确的,因为针对于这种行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是难以运用法律手段予以处理的,而朴经炮轰的行为却是显而易见地存在着极大的名誉权侵权的风险。
三、如果"机器人刷榜"出现在我国,我国法律有无规制点
下面,我们假设所谓的刷榜行为发生在中国,我国的法律规定是否可以充分地处理这一行为。
首先从最严格的的刑法来看,大家很容易联想到这种行为是否是一种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行为。
按照非法经营罪的原理和其立法目的,第三方公司所做的行为可能会为第四款的兜底条款包含在内,但音乐市场的特殊性,使得这一路径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这些年来,有多少首歌曲是凭借一个短视频或者一个节目,一夜爆红,音乐市场的热度到来是不规律的且具有极强的偶然性,而这导致如何判断一首歌的榜单排名是否不符合常理,是否为通过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行为所得到的,存在着极为难以考量的现实困难,如果每首长期处于榜单下游的歌曲的突然上升,都有公安机关予以介入审查,判断其是否为非法经营罪规制的行为所导致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时也会给公安机关造成繁重的办案压力以及因为错误侦查造成的损失赔偿的法律风险。即便,不由公安机关介入侦查,而由相关公司提供报案材料,报案材料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证据,而这种证据显然作为报案公司是无法提供的。故,无论是从公安机关主动侦查抑或是相关利益主体主动报案的路径来看,都具有极大的实施难度。
其次,如果从对于刷榜行为的行为属性关联性最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行为的规定中并不存在刷榜行为的类似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批指导案例中的45号指导案例所指出的,只有按照公认的商业道德和普遍认识能够认定违反该法第二条原则性规定时才可以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考虑的因素还包括三点,
一是行为实施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二是经营者从事商业活动时,没有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定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三是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这样的解释,显然如果第三方采取模拟刷榜行为的并非市场主体便首先不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条件。其次其是否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也存在很大的疑问,在目前的国内音乐界由于对于榜单的规范性与认可性的问题,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群体认为模拟刷榜是一种基本的营销行为。再其次,其损害正当经营者权益的形态并非间接利用或者直接造成损害,并不是常规的侵权形态。故,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来看,还没有到证据层次,就遇到了针对这一行为是否具有适用可能性的问题,这一路径存在着巨大的未知与实际难度。
再其次,从行政法角度来看是否有合规规定来规制这一行为。
2017年以来,国家相关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数据与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数据合规开始成为中国律师领域的新蓝海。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在宗教信息、科学数据、信息数据、医疗数据、环境数据等等数据类型都有相应的细分领域数据法规,而本文所述的刷榜行为所在的文化娱乐领域则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故,行政法路径比起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路径目前更不适合,连最基本的规制基础都很难举出。
从上文的叙述来看,如果潜在的"机器人刷榜行为"在我国出现,在缺乏全面的证据的前提下,是几乎没法以法律手段来规制的。
在本文的最后,作为一个深度的粉圈爱好者,我认为刷榜行为的存在同样在法意义上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点,在当年音乐市场集中化特点下,大量的优质资源掌控在某几家公司手中,这一点在韩国尤为明显,无论是公司自身的营销资源还是媒体宣传资源,大公司与小公司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要不然也不会有小公司艺人成功就会被称为奇迹的客观现实,然而大多数小公司艺人取得成功往往是来自某一个特别的契机,例如颁奖礼即兴歌词表现出众,否则即便他们的实力十分强劲,按部就班的发展也很难有脱离下游的表现。这样的现象促使一部分小公司采用了如"机器人刷榜"的方式来推动自己的艺人,从竞争和垄断的冲突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点,"机器人刷榜行为"本身与粉丝团体的刷榜行为,极容易存在混淆现象,一旦采用强力手段规制,容易直接影响到目前作为文化市场主体的粉丝经济,因为在本身的刷榜这一行为上,粉丝与机器人的原理是基本一致的,区别在于其主体身份,而这就像刑法中的主观因素一样,需要从外观来进行判断,粉丝作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群体,很难从具体的行为对其身份进行判断,也颇有一些法不责众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