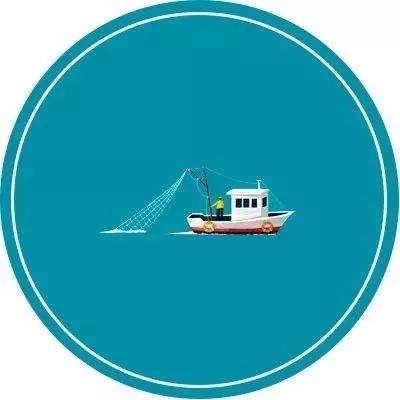“潘岱静:Mute”,展览现场,慕尼黑艺术之家,2022-2024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2024年第12届德国国家美术馆奖(Preis der Nationalgalerie)首次同时颁发给四位活跃在柏林的艺术家,其中,潘岱静为首次获得此奖的中国艺术家。同年间,她于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举办个展“Mute”,新作《After Fugue》目前正在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Hamburger Bahnhof-Museum für Gegenwart-Berlin)国家美术馆奖联合展览中展出。本月,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宣布潘岱静入围第三届希克奖(Sigg Prize),将于2025年9月在M+“希克奖2025”展览中展出其作品。
潘岱静1991年出生于贵阳,2012年前往旧金山旅居两年,自此开始她自学的创作生涯。
2015年开始,潘岱静活跃于柏林,通过对建筑空间的介入,运用包括影像、声音、行为表演、装置、灯光等媒介,将自身的具身经历与对社会的观察转化到她塑造的精神空间之中,触碰人藏于皮肤之下的情感。她关注人类共通的语言,比如爱和痛苦;她擅长在创作中制造亲密与不安感,其作品展演的建筑内部就如她肉身的延伸。
如诗人诺埃尔·阿诺(Noël Arnaud)所说,“我是我所处的空间(I am the space where I am),”[1] 潘岱静的所在也参与塑造了空间。
建筑不仅可被视作人类躯体的外化,也可以被看作是心灵对身体空间的投射。心灵的体验被转化为身体与建筑为一体的感官震荡。
这种体验可以用建筑现象学派学者尤哈尼·帕拉斯玛(Juhani Pallasmaa)所提出的建筑“氛围”(atmosphere)[2] 来尝试理解。存在于人类潜意识,氛围包含了人类在能够运用理性思维理解事物前,身处空间中所有境况的感官体验,包括气候、味道、声景等等。某种程度上,就如潘岱静所欣赏的作家残雪,她们所建构的作品是一种氤氲缭绕的“氛围”,激起人们早已积累在体内的具身图像。
“音乐具有与生俱来的抽象性,历来被视为与建筑最接近的艺术形式。然而,电影比音乐更接近建筑,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而是因为建筑和电影都表达了(被)赋予生命的空间(lived space)……这两种艺术形式都定义了存在空间的维度和本质;它们都创造了生活情境的体验感。”[3] 尤哈尼·帕拉斯玛的建筑理论巧妙地揭开了潘岱静从旧金山接触声音创作,到后来涉及空间与影像创作,如今更投入于电影制作的创作轨迹。时间与空间交叉的流动体验在她的创作上是必需的。在2024上半年慕尼黑艺术之家的个展“Mute”中,潘岱静在展览准备前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其建筑结构,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实验性的空间介入。慕尼黑艺术之家是史上第一个受纳粹党委任而建的大型建筑,1937年曾用于展出表达纳粹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二战后,美军曾占领此地用作军用餐厅,直至1946年,艺术之家才再次被用作展览场地。建筑整体使用石块搭建而成,被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古典风格。
不受建筑空间实际功用的束缚,潘岱静有意在空间内部逐一安上提供生命机能的部件——移动影像、声音、行为、灯光与装置,重塑建筑的生命形态。空间里安装了约50件作品,但潘岱静的创作过程不是从某一媒介先开始,而是先感知空间,再进行整体有机的设计,不作线性叙事,更偏向水墨画一般的留白,在其中埋下诸多伏笔,等待行为表演者、观众与作品一起自然生长。
“潘岱静:Mute”,展览现场,慕尼黑艺术之家,2022-2024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在慕尼黑艺术之家这个与外界严密隔离的空间里,潘岱静埋伏了巧思在灯光上。
相比于美术馆内其它空间,“Mute”的展览空间屋顶被打空,自然天光透过斑驳的玻璃屋顶洒落在无灯的空间,与透过窗户从户外打进来的人造灯光相融共存,同时也让空间的骨骼清晰地袒露在观众眼前。
在表演之夜,安装了动力装置的悬挂钢架在灯光的照耀下,制造出了整个建筑左右摇晃和倾斜的错觉。这个空间醒了,连同里面的人一同被唤醒。有时一度给人一种地震或空袭的虚幻恐惧,这种极度私密的情绪体验因个人经历不同而异。正如帕拉斯玛所说,“艺术家构想的建筑直接反映心理意象、记忆和梦想;艺术家创造的是心灵的建筑。”[4] 我们的身体反应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空间。
“潘岱静:Mute”,展览现场,慕尼黑艺术之家,2022-2024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在“Mute”的表演之夜,观众一开始在人群之中并无法分辨出表演者,他们与所有人在一起,看起来是那么地和谐。而当他们开始表演时,表演者之间散发出的氛围带着抽象的忧伤、抽离和空虚席卷而来。他们之间的行为曾经那么亲密,而后又那么疏离。潘岱静设计的现场表演,多数是带出层叠的抽象情绪,而非一些具体的情景;但其共情效果是强烈的:无所适从、恐惧或触动,以及其它种种混杂的情绪。
潘岱静希望当她带来对当今人们所处的极端环境与苦难的警醒时,也能同时给观众带来希望与韧性[5]。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潘岱静说道,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需要勇气去面对一种不舒适或者痛苦,现在人们日常接收了过多的信息,需要通过麻木自己进行自我保护。
这也是当代哲学家韩炳哲所观察的当代生活:人们活在同质化的地狱,却躲避能使自我成长的否定性。“只有在彻底的分裂中找到自己,心灵才能获得其真相。只有裂隙和痛苦的否定性才能使心灵保持生命力。”[6] 在潘岱静的作品中,撕裂理性的力量偶然会露出这种微妙的裂缝。
“潘岱静:Mute”,展览现场,慕尼黑艺术之家,2022-2024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人声对于潘岱静而言是一种乐器。
“人声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觉得每一个个体都是很独特的,很平等,平等在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一面,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感受、独特的痛苦、独特的挣扎,我对这个很好奇。声音也是非常独特的,在声音跟时间的关系中,声音不会变老,它只会更成熟。人声作为一种乐器,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这令我很好奇。这种好奇心促使我通过这个不断地去发问。”
潘岱静说。人体发出的声音实际也对应了人体内部的空间。物理意义上,由胸腔与其它器官协作的空隙,声带共鸣将内部空间吐出后与外部空间连成一体。在“Mute”中,偌大空间里回荡的声音渗入观者的皮下,不断亲吻低挂麦克风的表演者,发出痴痴的低喃或是耳语,瘙痒着观众的心,逐渐充盈着空间的空白。人声天然携带情感,胁迫着人的理智空间,心理与身体空间互相吞吐后重组,如同迷宫。无数的空间环环相扣,无限循环。
当人沉浸在情绪之中,一个瞬间,表演者陆续向着光逃逸,观众紧跟其后。观众的身体随即遭遇赤裸的射灯,冰冷的空气与入夜的天。最终,观众抵达户外。在建筑空间外部,艺术家放置了多盏大型射灯,仿造无法醒来的梦境般的刺眼光芒。表演并没有设置明确的结束,艺术家通过一系列真实的身体感知,把人从梦境中无言地引回现实——但氛围说话了,所有人读懂了沉默。这是潘岱静独特的艺术语言。她的词汇散落地飘浮在空中,只等着观众呼吸进身体后呼出,便成了每个人的话语。
“潘岱静:After Fugue”,展览现场,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2024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Mute”在质地较为冰冷的空间内进行,而目前在柏林国家美术馆展出的“After Fugue”则相对“温暖”。潘岱静用红色毡布覆盖整个展览空间,制造出一种流淌在身体内的、暗潮汹涌的私密感。红色毡布上有几处被割开,展露出了管道的内部空间,像是空间之肉被剖开展示。当观众习惯了空间的黑暗后,在不同的角落里便开始浮现出一些人类生活的痕迹,比如放在天花板管道旁的两瓶喝过的水,如情书一般卡在天花板的照片,以及窗帘留下的一条光缝。光是时间的指引,它告知人类所处的真实时间维度。这条光缝是艺术家留下的一条真实现实与建构现实之间的缝隙。潘岱静说,
“在夏天,往从这条缝看向窗外,有光在动,树叶被风吹动。虽然人走进了一个内脏感的空间,但实际它也通往更大的世界。我很喜欢这种无限(infinity)的感觉。”
类似地,在形容2023年奥地利格拉茨当代艺术协会(Grazer Kunstverein)的展览“Until Due Time Everything is Else”的同名艺术家书时,潘岱静提到,这本书是五轨影像《Grief Lessons》的第六轨影像,也是影像的残留物,
“当人翻书时,里面的图像就成了模拟影像……拍摄时的身体经验和翻书的身体经验是很雷同的,”她说。翻书这一动作,不仅将二维转变为空间,且涉及翻书当下的光线、时间、味道和触觉。她看待不同的媒介似乎都天然地携带着对“氛围”的偏执。
“潘岱静:Dry Score”,展览现场,奥地利格拉茨当代艺术协会,2021-2023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在“After Fugue”的单屏投影影像中,点燃的火光温暖了房间,影像中的空间则是展览“Mute”的发生地——慕尼黑艺术之家。在慕尼黑艺术之家展览里,则只能看见燃尽的蜡。这是一场完美的倒叙,将人从“After Fugue”的体感拉回到在“Mute”的体感中。影像空间的微妙之处,是观众会把自身身体融入其空间中。人在物理意义上尽管身处一地,精神也可能身处他地,这是人类想象力的无限性。
潘岱静的创作一直以来都是连续性的,她喜欢通过反复利用、重组作品,探索多重回响的可能性。
潘岱静很喜欢弹古琴那种与山对话的全然融合之感。尽管古琴无言,只有几个音符,但山间会返还无数的回响。
“就像在自然界里一样,万物中总有一些事物,是可以从中产生变化的。”[7] 她开放给观众的想象空间就像是掷石掀起万重浪。
“潘岱静:Tissues”,表演现场,泰特现代美术馆,伦敦,2019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欲望、梦境空间与对时间的感知,也是潘岱静反复地在建筑与影像空间里探索的主题。
除去蕴含时间性和温度的光和火以外,水作为在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常被用作潜意识、欲望和恐惧的象征[8],同时隐喻着深不见底的心灵深度,也是潘岱静介入空间时反复使用的物质。潘岱静从2019年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进行的歌剧《Tissues》已经开始用水进行实验。“Mute”中作为装置出现的水缸,以及渗着水迹的浴室空间,也延续了这一意象。尽管她的作品并不使用大量理论文本作为其内容,但她所阅读的文学、哲学、精神科学与心理分析学研究,对她的思考和创作过程提供了鼓励与共鸣。
潘岱静依赖身体直觉来创作。从小生活在被山包围的城中,潘岱静对空间与声音的感知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宿命的,因为人的“初始知觉一开始就诞生于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场之中,并在这一空间场中被塑形,被纳入其结构化的逻辑之中。这样,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就导致了不同的知觉结构。”[9]
她很早就对人与空间之间的比例差距有意识并感到好奇。她认为身体虽然渺小,但并不能束缚住身体与空间的融合。人对体外世界规模的感知是多变的。当人身处房间,人在心理上会认为世界在肢体可控的范围内;但当人处于森林或是层高极高的建筑之中,人心理所投射的自我则相对渺小。
潘岱静生活在自然与现代化高楼共存的贵阳所意识到的,是人那可以被无限放大或缩小的心理空间。山林没有屋顶,人类的身体暴露在自然中,没有庇护所的保护,此时人的安全感来自于心理空间的建立。
而人身处在建筑空间内,尤其是体量宏大的美术馆,人的体量与其相比而产生的渺小感,既像在宇宙之下的空灵,亦像回到母胎被子宫所包裹的安全。“人类构造空间的主要好处是,它为做白日梦提供庇护,保护做梦的人,让人可以安心做梦……空间是人类思想、记忆和梦最强大的整合力量之一。”[10] 潘岱静对世界的认知打破了这种人造的安全感,把人暴露在心灵的荒野,是危险且勇敢的尝试。她从不畏惧自己的空间实验失败与否,因为每一场展览获得的珍贵反馈都可以是她创作的养分,喂养心灵中更庞大的巨兽。
“潘岱静:Echo, Moss and Spill”展览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1-2022年。图片来自大馆
提起“家”,潘岱静这样说道,
“心在哪,家在哪。我的家在柏林,因为那是我一手打造的。我的朋友、我的街道、我的自行车、我的房子、我的工作室、我的家具……这是我对家的定义。在这之前我都是没有家的,都是‘被给予’的。”她是以感知为中心的人,感知是无限的,同时也是有记忆的,
“从情感上来说,我没有想回到过去,但我会有一种亲密感,一种树的味道,街道的光线,食物对我非常重要。我是长到17岁才离开的,我是‘非常贵阳’的贵阳人。我很喜欢这种归属感,但不一定是乡愁。这种归属感我在柏林也找到了,但是是不一样的东西。”
在采访中,潘岱静提到家乡贵阳某个摊位上卖的辣椒酱,以及城市气候给她带来的一种归属感与身份,“那是我成长的足迹,那是我的身份。我知道我从小就有这种感知。”
非艺术“科班”出身的潘岱静拥有某种自由,“我不在市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自由。”她对“获得认可”的认知也与艺术系统里的规则并不一致,
“我更感动的是莫名其妙的人给我发一封邮件,一个陌生人和我说,他/她正在度过人生中的艰难阶段,听到了我的音乐,看到了我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认可。”作为独立艺术家,潘岱静没有画廊代理、赞助人、工作室,但她说,“我什么都没有,就是自己。”
然而,对于现在的潘岱静来说,她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这么做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这座桥不直,就游过去吧。”
参考文献:
[1]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137.
[2] Juhani Pallasmaa, “Space, Place, and Atmosphere: Peripheral Perception in Existential Experience”, in Architectural Atmospheres On the Experience and Politics of Architecture (Berlin: Birkhäuser, 2014),p.27.
[3] Juhani Pallasmaa, The Architecture of Image: Existential Space in Cinema (Helsinki: Rakennustieto, 2001),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