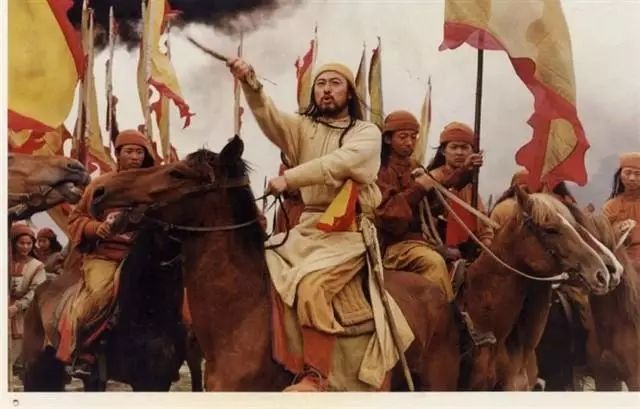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10日,曾陷入“杀妻案”风波的前美国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O.J. Simpson)因癌症在洛杉矶去世,终年76岁。1994年的一个深夜,辛普森前妻妮可与情人郎高曼被发现死于位于洛杉矶的一处豪华住宅区中,由于现场物证与不远处辛普森本人的住宅中的多处迹象高度吻合,且案发现场血迹中被检测出含有大量辛普森的DNA,辛普森随后以谋杀罪名被逮捕起诉,但一年后法院因“检方证据不足”宣布其无罪释放。

辛普森在法庭试戴手套,这是案发现场发现的一个有力证据
“辛普森杀妻案”在当年从立案到判决都是非常戏剧性且轰动全美的。
在一开始警方在逮捕试图逃跑的辛普森时,美国有7家电视台全程直播洛杉矶的高速现场;在宣布最终判决结果之际,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迟了计划中重要的会议与演讲;华尔街当日股市交易清淡;数千名警察全副武装遍布洛杉矶街头以维持安全秩序。30年过去了,辛普森去世的消息重新唤起全球对这一案件“死去的记忆”。
“辛普森杀妻案”首先对美国司法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400多个案件重新侦察,3000多个案件重新审理,40多名警察因制造伪证、违反程序等罪名被逮捕立案;洛杉矶市政厅通过法案决定增加警察局刑事化验经费与设备。案件也为全球法律带去重大影响,
它具有普世性,几乎是全球所有法学生的经典学习案例,其意义在于彰显了法律概念上「程序正义」和「疑罪从无」的巧妙运用。它也具有独特性,案件从审理到判决混杂了浓厚的美国种族议题色彩,当年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将「黑白之争」炒作到高潮,很难说法理完全不受这一因素的干扰。

媒体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曾左右了辛普森案的判决
程序正义,顾名思义强调程序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即使表面看起来案件铁证如山,仍然需要一系列的程序,并且必须有直接或间接证据链证明嫌疑人有罪。与之呼应地,在美国法律中还有一条著名的规则,“面条碗里只能有一只臭虫”。字面意思是,如果碗中发现一只虫,那么会索性将一整碗面倒掉,而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虫。这比喻了美国的一大司法规则,
即如果在所有提交的证据中有一条不成立或存疑,则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被法院所采信。
程序正义的概念都源于欧美古早时期。古罗马帝国的人治色彩浓厚,皇帝有时不需要经过司法就可以处死“罪人”,后来在英国法律中“自然正义”(Nature Justice)概念的影响下,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在20世纪通过立法将程序正义原则纳入行政法之中,以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美国的建国历史相对较晚,在建国后也参照了英国的标准,制定了术语为“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原则。

疑罪从无原则同样起源于现代英美司法体系,随后被全球多国法律体系采用,其中也包括中国。随着今年贺岁档电影《第二十条》的热播,这一“沉默的概念”被广泛热议。张艺谋导演近几年的影片都换了一个路线,常常把目标对向一些可讨论局限性较强的问题,比如《坚如磐石》的反腐话题,或者不太受关注但本应审慎反思的边缘性问题,比如《第二十条》的法律争议。
疑罪从无是个比较受争议的概念,其本意是体现现代刑法“有利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理念,优势在于法律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但弊端也很明显。
它一来存在“放过坏人”的可能性
,这也是一些国家在实际的法律实践过程中难以完全掌握这一原则调用尺度的原因;
二来也容易让关键的人证或物证“消失”
,欧美的黑帮片经常出现的证人被灭口的故事片段,都是因此真实发生的。

美国的“保护被告”的原则似乎有些趋于偏执,其宪法修正案规定,“被告不能因为同一个案件被起诉两次”。也就是说,假设辛普森承认当年杀妻,就意味着当年判错了,但美国司法也拿他无可奈何,他是可以逍遥法外的。旅美作家林达曾在他的书中《历史深处的忧虑》评价过,
“美国人深知任何制度设计都不会完美,一定会有犯人逍遥法外,这是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在美国的法律认知中,宁可错放一千,也不会冤枉一个。
当年著名刑侦鉴定专家、时任美国康涅狄格州刑事鉴定中心主任的李昌钰博士,作为辛普森高薪聘请的“梦幻律师团”中的一员,就是调用程序正义和疑罪从无原则质疑检方采取和呈现证据的流程存在漏洞,从而成功为辛普森“脱罪”,却也因为这一案件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被指责“帮助坏人逃避惩罚”。

李昌钰的证据至上理念是对的,但全球至今有很多人仍相信辛普森就是凶手,他只是为数不多的侥幸钻了法律程序漏洞的人。辛普森的一位辩护律师罗伯特·卡戴珊,也是辛普森的好朋友,后来公开承认,尽管最终赢下了官司,但他对自己这位好朋友的清白是存疑的,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来往。“梦幻律师团”的其他多数律师也选择和辛普森保持距离,一位律师后来更是直言不讳道,“我们并不认为辛普森就是无罪的,只是利用警方低下的能力和拙劣的手段,让法庭无法证明辛普森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