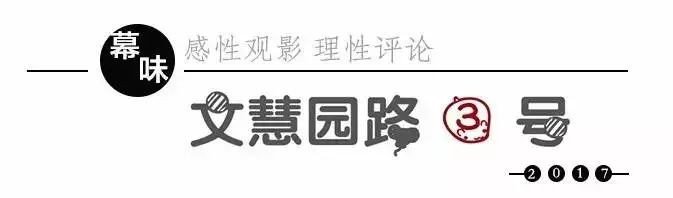
文 |
布鲁姆
这两天一篇“号召”抵制《敦刻尔克》的文章刷了屏,继而又被六神磊磊piapia打脸,斥之为年度“最蠢文章”。结果,在万众鄙视的眼神中,原博主终于认怂删帖。
贴是删了,只是不知道这种以博眼球、晒无知、搞煽动赚到的不菲的“打赏”还会不会原路退回?同时,
这件事让人惊叹于今天互联网文化的污糟混乱,也更让我联想到当今电影批评的问题。
诺兰,能不能骂?当然可以。因为他确实远不够完美。但到底应该怎么批评,我觉得,没有两把刷子,你也不要轻易提笔动口。
影迷对9月的期盼,也就是对《敦刻尔克》的期盼。克里斯托弗诺兰本人也降临了北京,可见中国市场崛起到底带来了许多福利。
笔者有幸在首映礼之前看到了这部作品,作为一名坚定的诺黑,这一次,也不得不给电影打上个高分。

《敦刻尔克》和诺兰的其他作品看起来不太一样。
首先因为这是一部改编自二战史实的历史巨制;其次,历史为诺兰式故事解开了谜团,节奏与情感交付于结构和音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影片在影像上做出了实验性的探索,以70mm IMAX 胶片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增强的真实,通过技术手段创造了观众非同寻常的感官体验。

过去我们常常在资深迷影前辈口中听到一种观点,认为一部电影的头十分钟足以证明其价值
(有趣的是,这种说法在网络点播时代被提及得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它太容易被误读为对粗暴付费逻辑的支持)
。
“十分钟定律”的存在有时是鲜明的。它或者展示了作者的风格,或者标定了影片的品质,或者已经将故事和主旨全盘托出。
《敦刻尔克》的开头,伴随不停打断画面的历史陈述,几个年轻士兵在被战争清空的城市街道信步闲庭——但他们突然遭到不明来源子弹的攻击,随之而来的是死亡和逃亡……然后,唯一的生还者,看到了一片海。

海边是敦刻尔克事件的主要舞台,上万英国士兵曾经从这里横跨海峡撤离法国。
当这一片海出现时,“头十分钟”结束了,《敦刻尔克》所集中刻画的情境已经锚定。后来的整部电影,也就是在通过各种方式的努力,牵着观众去体验这个关于生存的情境。

诺兰在各种访谈里描述《敦刻尔克》,常见的两个词语里,一个是“生存”,相比于战争,survival才是影片的内容,另一个是“实验”,这大概就是形式风格上的关键了。
参考对照《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70MMimax胶片的高色彩还原度、高动态范围以及高分辨率为增强现实的意图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但更明显的实验“方式”,在于台词的减免与情节的弱化。
《星际穿越》里,诺兰曾将角色的对话音量调低混入背景声,这一次他走得更远。影片尽最大可能还原战场真实的细节,按导演的说法,意欲让观众沐浴于战争、求生、逃亡的体验中。

遗憾的是,实验总是存在偏差。《敦刻尔克》的偏差可能出现在汉斯季默马不停蹄的配乐上。
诺兰把滴答作响的时钟“交给”季默,要求以此奠基配乐的主题,务必制造出战场的紧张感。如此设计的煽动效果不俗,但观众煽完之后却并不买账。
表述简单的嫌影片太吵,认知复杂的则声称“如果诺兰对自己的影像有信心,不会如此一边倒地倚重强节奏的音乐”。

实验不能为他作答,因为这算不上什么匠心独运、自我先锋的做法。
反面看来,这更可能是妥协的结果。
如果没有音乐带节奏,更多地观众恐怕接受不了影片平缓的线索和概念化的影像——士兵在海岸上排队、援救船在海上飘摇、飞机在空中盘旋,nothing happened。
作为当代最“成功”的导演之一,诺兰的趣味当然是匹配于大众耐性的。

不过,音乐的偏差带来的只是一点点买椟还珠的问题。它让《敦刻尔克》显得有些笨拙和匠气,但对于大多数人,还没有到扣分的程度。
有人就这个片子把诺兰与库布里克作比,其中的一些段落和镜头,比如士兵们列队在沙滩上、海岸白色高柱分割了视野的几个镜头确实令观者产生了一种简单而伟大的经典感觉。

对海陆空三重结构的吹捧各种文章已经写得很多了,确实厉害。不过,就我的体会来看,三条线索与其说是关于时间的,不如说是关于空间和速度的。
在速度上,士兵小于船舶小于战斗机;在空间上,海岸大于船舶大于机舱,而士兵受困于海岸、海员受困于船舱、飞行员始终困在他的飞机之中。

人为求生存,在敦刻尔克所指困境中不断挣扎。他几乎架空了一个历史事件,就是为了把敦刻尔克打造成一个关于人类抽象困境的隐喻。
是不是有些存在主义的意思?

关于速度的影像可能令我们联想到了以速度为名的一些实验电影代表,诺兰自己也大谈experimental,可他为《敦刻尔克》选取的参照影片里却没有我们所期盼出现的美国实验电影。
名列其中的都是电影诞生以来最伟大的作品——比如经典默片《党同伐异》、《日出》、《贪婪》以及布列松静默极简的《扒手》。
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受强调的一部——曾获得第6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被美国影评教母宝琳·凯尔称为“存在主义惊悚片”的《恐惧的代价》。

导演,活跃于40年代、擅拍惊悚片的法国名家亨利-乔治·克鲁佐,在今天的影迷眼中大概不算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但他的多部作品都是法国影史不可忽视的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