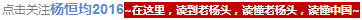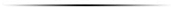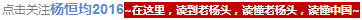
【 回复数字关键词“
001~010
”,阅读↙老杨头最新原创热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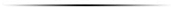

2016-09-10 11:04:12
阅读数:3476
我将尽我所能抗击社会的不公正,锄强扶弱,以对得起离乡背井去打工的李广学老师。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湖北省随县草店利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他是个瘸子。感觉对所有学生都和蔼,就是他在上学登记名字后在班上宣布,“杨红军”的“红”有点女性,就叫“杨军”吧。当我和班上孩子辩解说,这里的“红军”是长征的红军哦,他说,没听说过“不爱红妆爱武装”吗?
给我留下最深影响的老师也出在利民小学,他是音乐老师,会吹笛子拉二胡,我拉二胡就是从他那里学的。他个子很高,脸色有点苍白,他叫李广学。他的故事我写在《我的老师李广学》里了。他在我最艰难的一次受到同学欺负时,出手“救”我,让我终身难忘,并立志要保护弱小,对付恶霸。但由于李老师是工农兵学员,改革开放后被辞退,他只好到外地打工,和家乡人失去了联系。可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世界上最有水平的老师,我就是他教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我在随县天河口(公社)初中的班主任刘老师。他看到我们班同学不学习,嘻嘻闹闹,就常常漫不经心地一个人在讲台上灌输他特有的心灵鸡汤:“哦,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都是一样的,什么区别也看不出,但十几年后,那些努力学习的同学都穿上了皮鞋,到县城里工作了;那些不听我说的,仍然像我一样只能传布鞋,在我们这个只有一条街的天河口混。”
这话对我努力学习,争取穿上皮鞋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班有几位我至今都认为是“国色天香”的女孩,“她那粉红的小脸,好像红太阳”——很久后我才知道,她们脸蛋当时一到冬天就冻伤,红扑扑的。但烂苹果似的脸蛋当时对我的吸引力,不亚于范冰冰对你们的感官刺激,我好多次忍不住想牵她们的小手,走到校园后面那“遥远的地方”去呆一会,可一想到刘老师的“皮鞋和布鞋”理论,就硬生生地打住了。我要考上好学校,穿上皮鞋进了县城再回来聚她们。当然,我离开公社不就她们就陆续结婚了。其实在我硬生生地打住时,其他男孩子都没有能够忍住。我至今心里还很失落,不知道如何计算得失。
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老师叫朱宝训,他也是个瘸子(原谅没有使用“腿脚不方便”,因为需要延续当时的说法),那时我已经考到随县一中上高中。我们是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朱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采取了军事化训练和管理,每天24小时监管我们学习。两年后取得了随县一中当时有史以来最好的文科成绩,全班几乎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就有十几个。
有两个原因让我和朱老师始终心存芥蒂,第一个是父亲说他是文革时的造反派,打过不少人,也被打过。他也好像不太喜欢父亲。第二就是他的严酷训练对全班绝大多数同学确实有作用,可对当时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逐步有了自己学习方法的我来说,简直就是“法西斯”噩梦。
例如,他一定要每天晚上背诵语文课文,可我知道,语文课文再背多少,考试成绩不一定见效果,更何况我早就读过这些书,可如果用这个时间背诵历史课本,效果就不一样了。结果,有好多次他从我的语文课本下面搜出了历史课本,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把六本历史课本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大家知道,我现在连朋友的名字都记不住,就是那时背得太多,可能记忆力永久受损,脑残了。
如果只是这些事,可能也不会提起他,后来发生的事,对我人生影响实在太大。我读高一时是班长,高二时坚决不干,因为我要集中精力学习,朱老师很不高兴。这也就算了。突然有一天学校团委书记通过朱把我叫去,让我交代自己的思想,交代给同学们说过什么反动的东西。我怎么都想不起来,结果,团委书记告诉我,我在几位同学中讲我爷爷如何去镇上赌博,以及回来后看到土匪来了,拿起枪就冲,带领乡亲转移,还有好像说日本人来时,也是我爷爷带领乡亲躲到后山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我爷爷1949年后因为有三十亩土地而被划为地主,16岁的我,立即被团委书记定性:歌颂地主阶级赌博和个人英雄,含沙射影对毛主席的不满。
结果我被关在集体宿舍好几天(是三天还是一个星期不记得了)不能去上课。当时高考临近,我以为考试资格也没有了,悔恨交加,一度想到自杀。但可能当时朱老师和团书记只是想吓我一下,还是放我出来了,也没有给处分。这事我从始至终没有告诉父亲和家人。那是1983年,我因为讲了我爷爷的两个故事而被关禁闭。
后来朱老师和我一直有联系,但我始终没有想到要问他到底是哪位同学去告状,以及他们当时和当今到底怎么想这件事的。朱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一切都可以放下了,半年前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去广州玩,希望我陪他,他要带唐伯虎的画去卖。可惜我不在广州了。而且我也有点狐疑,他怎么会有唐伯虎的画嘛。
复旦大学四年也有不少老师难忘。我的班主任是周棋和浦兴祖,两人都不错,对我也好,否则以我当时的成绩,好像不应该分配到大家都想去的北京外交部系统。当时两位北京的同学竟然都没有被分配到北京,也引起了一些同学对我的误会。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
大学老师在生活上同我走得最近的是祝老师,她当时就快退休了,一个快乐的喜欢说话的老太太,对我们班几位来自农村的总是问寒问暖,很温暖。但她特别喜欢告诉我们有关国政系老师的小道消息,例如,哪个其实不是老师,而是安插在这里的特务,让我们要留意,保持距离——可问题是,我们本来就是学习国际政治的,系里本来就有情报部门退下来当老师的,我们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对“特务”反感嘛。大学毕业时,三十多个同学中竟然有八九位去了国家安全部门,就能说明问题。不过,我进了外交口而不是国家安全系统,估计就和她整天数落特务有关。
另外一位对我后来发展帮助不小的是国政系系主任、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他在课堂上第一次挑起了我对美国的兴趣,虽然他为了惩罚我的粗心(写英文用中文标点符号)而给了我大学四年唯一的一个不及格,但毕业后联系最多的也是倪老师。倪世雄老师对当时开辟中美关系学界对话通道功不可没。但由于他的观点持中,不激烈,好像进入国际关系互联网时代后,渐渐被人忘了。不过,我永远记得他。
然后就是我在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导冯崇义,旅居悉尼的中国自由派学者。他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就不多说了。在学术上在工作甚至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扰,我还是会不时向他请教。如果你来悉尼旅游、游学,有搞不懂的问题,我带你去见他。
这些只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在校老师,实际上,在工作中,在社会上,我有更多令人难忘的老师。今天是教师节,我要对他们鞠躬感谢。他们都在我生活中留下了烙印,没有他们——好也罢坏也罢,不会有今天的我。
光阴荏苒,杨红军成了杨军,杨军成了杨恒均,杨恒均又变成了老杨头,老杨头也开始被一些人叫做“老师”了,这让我很开心,也很惭愧。我常常想,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老师应该教我们什么?言传身教,教育我们做人?还是做事?还是传播我们知识?我知道老师的重要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把我们牵引到不同的道路上,送去不同的未来。
我一生都是学生,未来还是学生,我自认为是一名合格的学生,但我也试图去做一名老师,一名合格的老师。
杨恒均 2016/9/10 教师节
 家乡什么都拆了,唯独利民小学,包括我当年的教室,竟然还在,改成了民居而已
家乡什么都拆了,唯独利民小学,包括我当年的教室,竟然还在,改成了民居而已
附录一:我的老师李广学
自从小学时开设了作文课,“我的老师”这个题目就一直是最熟悉的,小学语文老师引导我们如何从描写熟悉的老师入手刻画人物的外貌和言谈举止。一直到初中,还在写这个题目,只是那时强调的不再是老师的外貌而是他们的内在品质。到了高中准备高考时还在练习这个作文题,而且已经背诵了很多既可以用于描写老师也可以用于描写其他人物的高尚品质和独特个性的经典范文。
正因为这样,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好像突然穿越时空,回到了儿时的课堂。我猛然抬头,虽然并不见眼前有老师站在那里,但心中却产生了一种诚慌诚恐的感觉,那是一种正准备完成一篇命题作文的感觉。
不错,我正在完成一篇命题作文,虽然并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然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现在是完成这一篇作文的时候了。这些年,“我的老师”这个题目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而我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总有一天,我必须完成这样一篇作文,不但是用笔,也用我的一生。
大概是由于自己的愚笨和好学,我有很多很多老师,中国的有,外国的也有,在我足迹所到之处。他们传授我知识和学习方法,给我帮助、教诲和扶持,没有这些老师,我根本走不远,更不用说走出原来的自己。
记得高中的数学老师废寝忘食挑灯夜战,终于猜出了大部分高考数学题,使得我这个至今对代数和几何一知半解的学生获得了数学高分的高考成绩;也无法忘记大学的老师根据我的情况,向海外推荐我去做研究的用心;更感激那么多被我请教的老师不厌其烦的教诲……至今,这些老师虽然几乎都失去了联系,但我会永远记得他们。
然而,这却都不是那个和“我的老师”这个作文题目一起悄悄深印在我心底达二十多年的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叫李广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湖北省随州市草店人民公社利民小学读书时,他是那里的民办教师。
随着岁月的流失,对李老师的记忆不但没有淡薄,而且,和那个作文题目一样,越来越多地浮现在我脑海,冲击我的心灵。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要求我必须完成这篇作文。与此同时,我的心灵深处也为没有完成这篇命题作文而越来越惴惴不安。
我一直没有落笔,一是不知道如何写,二也是因为我不愿意窥视自己的灵魂深处——现在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我强烈感到,如果再拖延下去,对不起我的老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到利民小学上小学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达到高潮。这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说,那时我们家的日子很艰难。父亲是中学老师,家庭出身又不好,在“地富反坏右”中占了头号,外加“臭老九”,所受冲击可想而知。好在我上中学时,“春雷一声震天响,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父亲翻身得解放,姐姐回城把学上。”——记得这是当时父亲教我写的一首革命诗歌。我上大学后,父亲经常找机会教育我,给我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折磨。然而,我的表情一直很漠然,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归咎于我那时太小,什么也不记得,也就自然没有什么感受。
然而,事实到底如何?那事实已经深埋在我心底太久,久得我不愿意把它挖出来。就在父亲认为他受到冲击遭受折磨的时候,作为地主狗崽子和臭老九的后代,我几乎每天都遭到欺负和污辱。那些欺负和污辱来自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知道,只要一喊出“地主狗崽子”这句话,我就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们可以任意欺负我,甚至让我跪下,接受他们心血来潮的惩罚。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或者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毕竟太小,还不到十岁,但就是这十岁的心灵,已经早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天生是一个罪犯,是低人一等的,我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必须老实……我没有权力和人吵架,更不用说斗殴,但如果我老老实实,接受其他家庭成分好的孩子的惩罚,我会得救,我的父亲会感到安慰,我不能为他添麻烦了……
这就是我的世界,这就是我整个小学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十岁的孩子接受了事实,他是一个低等人,是一个其他家庭出身好的孩子的出气对象。我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父亲早就交代过我,而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每次当我在外面受到欺负,衣服肮脏甚至破烂的回到家里,父亲都以为是因为我顽皮而不爱惜造成的,他甚至为此打过我,而我只能咬着牙关,一次也没有告诉父亲,他十岁的儿子正因为他的成分在遭受炼狱的折磨。(请参阅《父亲的两次眼泪》,里面有一次遭遇)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当时的成年人向我声泪俱下的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我都很没有耐心听下去,有时甚至会生出不屑。我一直认为,作为成年人,他们无论受到什么迫害和冲击,都有能力应付,你可以选择抗争,像张志新烈士一样千古流传;你也可以选择屈服,像大多数人一样;当然你还可以选择成为凶手或者帮凶,从而遗臭万年……你甚至可以选择自杀,结束自己无法控制的生命,像那位勇敢地走向水中的老舍那样……作为成年人,既然有那么多选择,事后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可是,我,当时不到十岁的我,有选择吗?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自己是阶级异己的后代,是地主后代,我只能逆来顺受,我不知道我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可以打架可以还击,可以哭可以报告老师,当然更不知道人还可以用自杀来获得解脱——于是,只要有同龄的小朋友不高兴了,只要他们叫我一声“地主狗崽子”,我就得凝固不动,任他们欺负污辱……而在学校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活动和聚会中,我内心心惊胆颤,外表垂头丧气,我察言观色,对所有随时可以把我打翻在地的人陪着笑——我想,大概从那时起,我的心灵就再也无法长大,我的灵魂就此被彻底扭曲了……
被打倒的成年人终于等到平反的一天,可是,谁来平反我那扭曲的灵魂,谁又能平反那无数被扭曲的孩子们的灵魂?
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李广学老师,我那扭曲的灵魂会把我带向哪里去。李老师当时是利民小学的民办老师,他自己没有读什么书,因为家庭出身好,他成为学校的音乐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二十出头的他瘦高个头,头发有点乱蓬蓬的,皮肤有些苍白,好像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眼睛很大很有神。他负责学校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始终没有直接带过我的课,只是,在我遭受欺负,不得不大多数时间一个人呆在学校的墙角时,我常常听到他指挥的乐队演奏的革命歌曲。
大概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的某一天,在学校大扫除时,我的扫帚不小心碰到一位同学的脚跟,当他转头看到是我时,口中喊了声“狗崽子”冲上来就打,我抱着头蹲下来,以为像往常一样,只要他发泄完了,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大扫除,到处是扫帚,那位贫下中农的后代抓起一把扫帚劈头盖脸打下来,我的头被打出了血——
在我抱头痛恨自己又惹祸,痛苦地思考如何向父亲解释身上的血从而心里也痛苦得流血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大吼,随即,那位同学停下了手里的扫帚。我怯怯地抬起头,看到李广学老师满脸怒容地站在我面前。他斥退了那个打我的同学,然后走过来,弯下腰,向我伸出一只手。虽然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但我仍然认为那情景是那么的不真实。当他用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走向他的办公室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自豪……在我们湖北一些农村地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比北京和上海要彻底得多,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来关心一个地主和臭老九的后代,就连我的父亲也无能为力,在我还没有懂事时他就开始告诫我在外面不要惹事,能低头就低头,不能低头也要低着头,我也确实这样做了——现在,在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低人一等的现实的时候,一个苗正根红的学校老师少有地牵住了我的手。
我高高地抬起沾满血的头,仿佛那是一面胜利的旗帜,我看到操场上很多同学羡慕地看着我。
李老师一路都没有松开我的手,我记得由于他个头高,我不得不把手高高举起,生怕脱掉了。我随李老师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擦红药水,问了情况,我含着眼泪承认了自己是是我不对,碰到了同学的脚跟。他打断我,大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我长到十岁鲜有见到的亲切怜惜的目光。他叹了口气,问我,想学拉二胡吗?随即,就从墙上取下一只二胡。他说,今后课余你可以到我这里学习拉二胡,拉得好,就可以参加文艺宣传队了。
从此我就经常到李老师那里练习拉二胡,我发现到李老师那里学习乐器的人不止我一个。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孩子中有些是因为体弱多病,无法参加学校经常性的体力劳动,大多却是像我一样,父母是阶级敌人,自己在学校经常受欺负……李老师显然不只牵过我一个人的手……自从李老师把我保护起来后,那些本来欺负、骚扰我的同学有所收敛,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有了靠山,心里踏实多了。
在我整个无法言述的痛苦的童年里,李老师一直用他特殊的方法保护我,这是在那个年代我唯一感觉到的关心和爱,至今我不但还能感觉得到,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反而越来越强烈。
离开家乡后我一直没有回去,听家乡人说,改革开放不久,由于李老师没有系统学习,也没有文凭,最后被学校辞退了。生活都有一定困难。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里拿出一些钱托人给他,但所托之人告诉我,他早就离开了,先是到河南种木耳,结果碰上洪水,之后他只好带着家人到南方打工去了,至今音信全无。
我的李老师应该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他能干什么工作,身体是否受得了?
在我一生中,传播我知识给我教诲的老师很多,但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我的李老师。他的学问和知识有限,没有给我带过课,他沉默寡言,更没有教诲我什么人生的道理,就连那让我能够呆在他身边的音乐,我也是半途而废,然而,我知道,他传授给我的是我一生都用之不尽的对生活的希望,对弱者和幼小者的关怀和那广博无边的爱心。
没有李老师,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已经干出了什么。因为我真不知道自己那被成人社会扭曲的幼小的灵魂会把我牵引向何方。是李老师轻轻牵起我的手,用爱抚平了我那本来伤痕累累、充满仇恨和报复的心灵。我原本想让那段历史淡忘,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风雨半生之后,童年的经历连同李老师的形象,在我心中反而愈益清晰和明亮。我终于坐不住了,我决定拿起自己的笔,写出邪恶和善良,写出绝望和希望。
然而,首先,我得完成这样一篇命题作文。
在我终于有勇气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的同时,我早已经下定了决心,自己的下半生将不再沉沦和沉默,我将尽我所能,以我能想到的方式方法抗击社会的不公正,锄强扶弱,以让自己的灵魂能够永远平安,也以此回报我那早已经背井离乡在外打工的老师——李广学。
杨恒均《百日谈》之003发表于2005年教师节
后记:
重贴此文,依然让我动容。相信看过此文读者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在微博突然说,真想亲手结束那些欺负同学的校园恶霸了吧。当然那是气话,我们是法治社会。实际上,我小学遭受同学欺负只是少数情况,尤其是欺负我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个别的,包括文章中这位和《父亲的眼泪》中的那位,都是一位草店街上的小混混,我打得过他,但不敢打,他不到十岁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这位同学改革开放后,去南方打工,由于身材矮小,使不上力,生活过得并不好,我在街上见过两次。而当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第一要做的就是为家乡那些农工包括这位欺负过我的同学呼吁,维护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和我们这些大学生一样,享受改革红利,活得像城市人一样。这在我《致命武器》里非常明显。这说明,我已经跨过那一页了?或者,我用其他的形式延续我的思考和经历?我希望你们也这样,留下爱,不要仇恨。
 戴上博士帽的我和我的导师冯崇义博士
戴上博士帽的我和我的导师冯崇义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