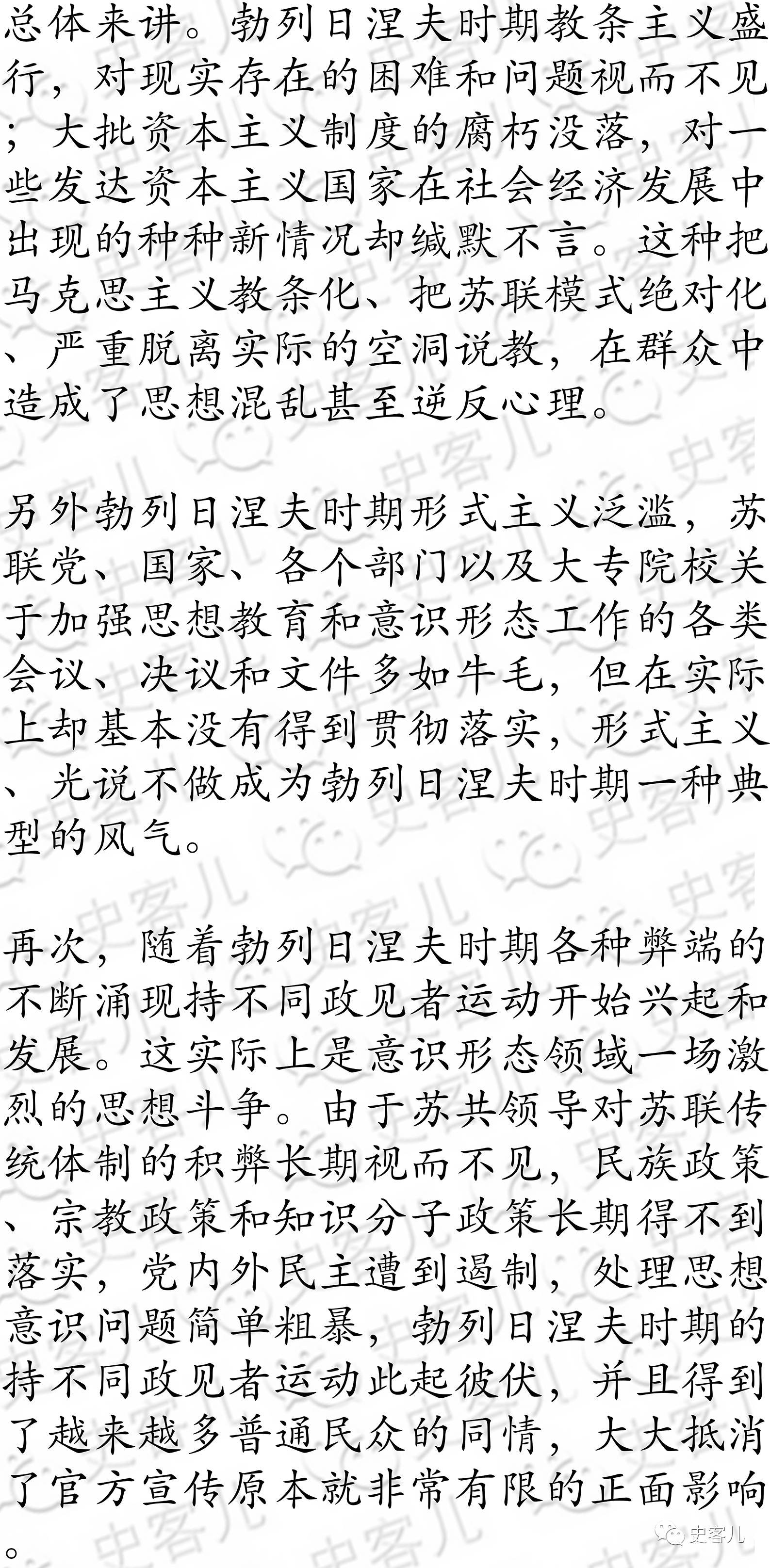斯大林时期,苏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政治经济模式相适应,苏联思想文化体制也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清洗"。从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开始,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在"清洗"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另外作为作为书报检查机关,国家新闻保密局是最重要的新闻检查机构。列宁时期,最开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承担书报检查的职能;到1917年1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强化了书报检查工作;1918年6月,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开始实施对书刊出版的军事检查;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局开始履行书报检查职能。为改变政出多门的状况,1922年6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新成立了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属人民委员会系统管辖,承担了对所有印刷品进行书报检查的职能。
总体上说,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对各种要出版的作品进行预审,确定出版方面应遵循的规则和实施细则,编制出版清单和禁止作品的出版等。1929年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规定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
后来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过滤机制:
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随着书报检查制度的发展,它最终变成了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的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另外1927年之后,苏联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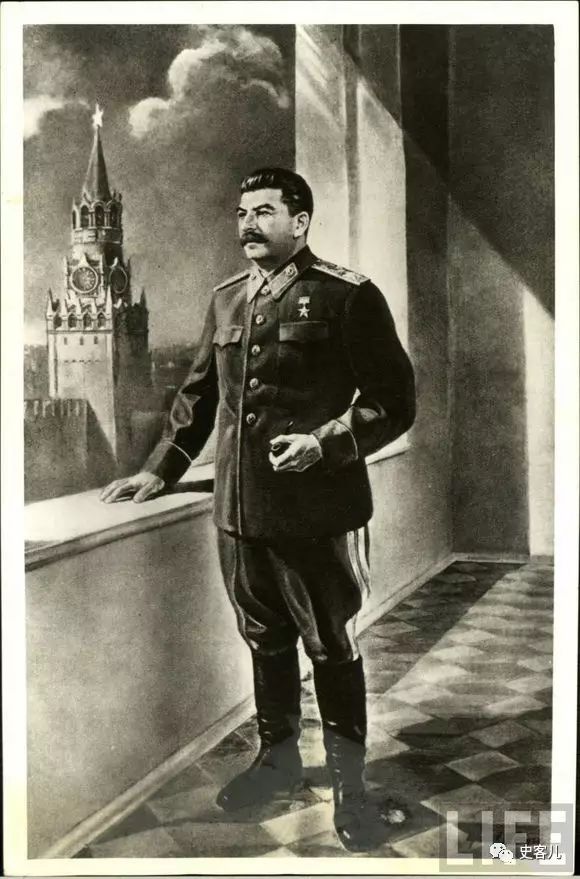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文化专制政策开始延伸到文艺界,对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讽刺幽默作家左琴柯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柯被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阿赫玛托娃则被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最后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指向了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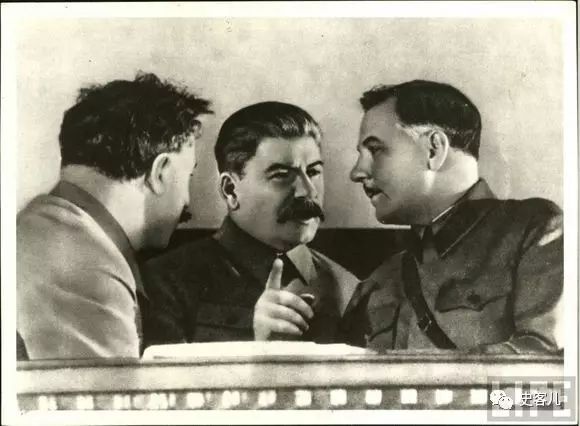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
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
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开始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等问题,发表了创见。
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的金科玉律。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上世纪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也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是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
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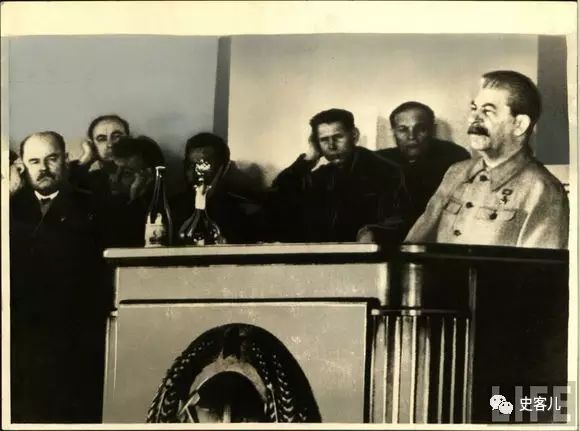
总之斯大林时期,在思想文化各领域、各部门甚至各学科层层设有全权负责的领导人,权力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之手。苏共根据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取消文化艺术团体和派别,官方直接自建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成为党和国家层层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属机构,促使其走上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
另外判断意识形态的标准完全是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成为真理化身、思想源泉和理论权威。苏联思想文化领域按斯大林要求发起一波又一波批判运动,裁决一场又一场学术纷争,使斯大林理论观点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绝对权威或垄断地位,从而导致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滋长,也阻碍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另外把学术领域的争论等同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斯大林往往直接干预学术论争,习惯于以政治斗争或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学术论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打击或肯定某种学派,以最高权威的身份评判学术论争,妨碍学术民主和批评自由,挫伤有学术造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成思想理论界的沉闷空气。
相对于斯大林时期文化控制和高压政策,赫鲁晓夫时期则被称为"解冻"时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治、社会开始发生大的转折和变化。自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领导力量》一文直接批判"个人崇拜"以后,苏联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1953年7月16日,《文学报》发表了社论,提倡文学作品的真实性。

1954年5月,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的第一部。用文学的方式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褒贬不一、就这篇小说发表了各种评论和意见,在苏联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解冻》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1954年12月15日—26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苏共中央至大会的贺辞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干预生活",同时对"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现实"两种倾向进行了批评。在1956年2月14—25日召开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在总报告中不满意苏联文艺的发展现状,批评文艺"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在苏共20大召开前后,苏联文艺界总体上就是强调"现实",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斯大林时期拘泥于教条和领袖观点的做法与路线。
苏共20大召开一年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路线又产生了新的变化。1957年5月14日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三次全会召开,大会主报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崇拜对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战后年代,是无可怀疑的",但同时又强调,不应夸大个人崇拜的有害影响。
到了1958年,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大体上又回到了1957年以前的发展轨道。这个时期强调继续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开始出现人道主义思潮。1958年2月8日,在知识分子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希望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上更为勇敢,更注意对生活、对人生的观察!""下更大决心来面向现代生活","抓现代的重大问题"。1960年3月,《共产党人》第10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对人的社会主义关怀》,强调"人道主义、人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活动的主导原则之一"。这一年,苏共还出版了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取代了斯大林时期的《联共(布)党史教程》,成为苏共党史新的理论教材。

1962年,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以后,在苏联文坛掀起了一股"集中营文学"的浪潮。面对无数新的作品,对苏联历史的揭露与讽刺更加露骨、深刻,赫鲁晓夫执政集团重新开始实行紧缩政策,意识形态领域又出现控制的迹象。
1962年以来,格罗斯曼1960年写就的战争题材小说《生存与命运》一直不能发表。1962年7月23日,在同格罗斯曼进行谈话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指出,小说政治上是敌对性的,可能带来的危害比《日瓦格医生》还要大得多,"要出版的话,可能也得等2、300年"。1963年6月,苏共中央就"党的思想工作和当前任务"召开全会,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共处"。他认为"谁要是想置身于党的政策之外,否认意识形态中的党性,那就等于组成一个非党人士的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党。反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反对我们的现实。"

总体来讲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在解冻与控制之间摇摆。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深入、全面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解冻"成为时期,苏共相关意识形态机构也没有放松警惕,而是同样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对各种他们认为对苏联党和国家有害的作品和人物进行行政上的控制,很多优秀的作品被无情地封杀。
当然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在意识形态领域,赫鲁晓夫时期工作方式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彻底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残酷镇压、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极端做法,但碰到了难题,尤其是需要减缓"解冻"的步伐、扭转方向的时候,赫鲁晓夫同样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斯大林时期的某些色彩。
随着经济的发展,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为了加强思想控制,防止人们在思想领域出现异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机构空前膨胀,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工作部门。

按照1966年5月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苏共中央组织结构,苏共中央宣传部下设13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刊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办公厅。这13个职能局的工作范畴,基本涵盖了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承担着领导作用。其所确定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苏共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决策与动向。
与其他意识形态机构领导人很少变动不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相对频繁地变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人,说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极不满意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而对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大多数宣传部的部长们没有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
苏共中央文化部最初由四个局组成:创作文艺局、艺术局、电影局和办公厅。从四个组成部门的名称可以看出,苏共中央文化部的职能主要就是负责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创作知识分子打交道,同知识分子的各种"离经叛道"作斗争。与中央宣传部部长频繁更换不同,苏共中央文化部的部长人选一直比较稳定。与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工作出现某种程度的波动不同,苏共中央文化部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波澜不惊,一定程度上成了保守的代名词。

克格勃第五局成立于1967年7月17日,是根据当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建议,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的。
克格勃第五局虽然不直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苏联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的开展与工作的具体内容大多与这个机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第五局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逐渐凸现,而且异常特殊,不仅为苏联党和国家及其他意识形态机构提供大量信息与情报,还包括拟定处理意见,负责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
克格勃在意识形态工作决策中地位独特。虽然本质上是国家安全机关,不属于意识形态机构,但克格勃第五局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地位非常独特,它们提供的情报在实际决策中作用很大。克格勃严格按照苏共中央的旨意行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工作,所获取的情报、提出的建议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于这个机构,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中国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都是控制思想言论的特务机构,特务机构的加强反映了当时苏联当权者内心的一种思想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