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源,以水开始,西方文明展开了一场探索生命起点的漫长路途,这也趋势无数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们迷恋一个悖论,即渴望在遥遥无期的终点处遇到起点。在回溯本体的激情驱使下,约瑟夫·布罗茨基曾 17 次踏入威尼斯,“带着温柔,带着感激之情”在这座城市寻觅“在水中诞生的时间”。他曾毫不隐晦地流露对这座城市的深情,称其为“水上金色的鸽巢”、流亡者的故乡。
唐克扬曾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学习建筑学,现为独立策展人。在他的回忆中,“沉浸”在水中的威尼斯像一副朦胧的印象派画作,但也不失建筑学的精确,她身体上的刻度来自乔尔乔内、卡罗·斯卡帕、勒·柯布西耶、马可·波罗,她既是永存的,又是变化的,既是客观的和身外的世界,又是我们感受到的一切......

威尼斯:水上的和水中的
唐克扬
和我们类似,初次到达威尼斯的人不免都是从水上莅临,只要他们还在乎那招牌式的明信片式风景。在水波荡漾中行船片刻,会觉得整个城市真地是“漂浮”在水面,那不是吹皱一池春水的写意,而是时速二三十节快艇的惊心动魄,是载满游人的“刚朵拉”和各色游船的大呼小叫,绕岛一周的旅程并没有起点终点的区分。偶然下得船来,没有三尺平地便要上桥下桥,别过窄小的巷道,五步之内又是旅人告别的码头;由于谈不上多么有规律的水面的分割,那些近在咫尺的往往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用来解释这座城市独备的格局,也许冯至八十年前的诗句最为精辟: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
一座座都结成朋友
当你向我拉一拉手
便象一座水上的桥
威尼斯并不是建筑在水“上”,而是建筑在水“中”,这细微的差别并非无关紧要──城市本身,而非它的基础,其实是一座浮岛。历史上,从中南欧地区,例如今天的斯洛文尼亚西部砍伐来的数十万个木桩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根基,水下没有氧气,因此那些没入水下的木头都修成了不坏的金身,经过富含矿物质的海水冲击。年久之后,它们成了类同化石的坚硬基桩,深陷海底的泥沙中直至不再下沉。1
相形于海面下的威尼斯,水面上的城市只是一层细腻的油泥──近看是红色屋顶的海洋,百年人事的精华,放大了却是斑驳的灰色风景,和周遭百里的湿地沼泽混杂在一起,没多大分别,如果是从飞机上遥遥地俯瞰,几乎都看不出什么“城市”的征象。这种悖论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出了机场,坐着“水 的” (water taxi) 趋近威尼斯的人,隔得太远时看不出什么端倪,岛和岛之间好像只是植被的不同 (纽约的天际线就不然, 独立于地平线上的摩天大楼一下就现出了自然和人工的分野) ──明信片模样的威尼斯几乎是突然闪出画面的,一时间眼前就是满满匝匝的城市了,一座,两座,千万座建筑,每一座都是恰如其分地“如画”,正是阿城形容过的“表情过于丰富的女人”──但因为她笑着,并不真的使人厌恶 。2
在城市设计的形态学里,这种尺度渐变乃致感受跃变的现象是有意味的,万千细节的集合,合在一起是一个面貌截然不同的整体。仿佛谷歌地球的卫星地图,粗粗看来只是浑浑沌沌的大地沟壑,放大一级或两级精度便细节宛见,一切变得不同。 若论威尼斯的秘密,大概藏在“上帝之眼”在城市上空百来米的俯瞰中,寻常照相机记录不来。只有航拍图,多少使人明瞭这水城九曲弯回的几何之美;相形之下在人视的高度,甚至巴洛克城市中常见的透视也失效了,因为静态的目光来不及追赶运河快速的转向。如果不是实在博闻强记,剩下的就只有使得资深驴友也晕头转向的细节,细节...... 当代城市倾向于面积上贪得无厌地展延,拿标准化的制件稀释风格的浓度,更不用说填海而成的各城市都有得陇望蜀的趋势,威尼斯岛的岸线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有乔尔乔内 (Giorgione) 的画作为证──现代城市基建让本岛逐渐下沉,潮水时有涌进圣马可广场,自下而上的根基摇摇欲坠,从外而里的营造却越发密致、沉着,里面塞满逐渐暗色的人生──这西方文化中罕见的内向生活,和它周遭的一切,无论是威尼斯 的“新区”,还是城市所在的 Veneto 大区的青山田园,都没有显著的关联。

Jacopo_de'_Barbari 笔下的威尼斯。
作者资料。
这样的城市几乎不可能有十分“先进”而凸显个体的建筑风格,却留下了两位著名现代建筑师与众不同的足印。一位建筑师是长期没有从业执照的卡罗·斯卡帕,他的作品衔接着摩 登和乡土,未必显摆什么先锋派的大手笔,却是地道的当代威尼斯建筑。在我驻足此地期间和朋友去了他位于特里维索 (Treviso) 的布里昂家族墓园,他作品的魅力全在于微末中, 任何细小节点似乎从不会爽快地一蹴而就──斯卡帕著名的 5.5 cm×5.5 cm 的混凝土线脚,不厌其烦地出现在类似于麦金托什室内作品的直角空间转折里。不同之处,是他似乎从不将 这些重复的细节看成某种特出的个人风格,而是视为本地化的辽阔风景的部分。
另一位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勒·柯布西耶,倔强虚妄,却又九死不悔的瑞士人,现代主义的“四大师”之一。他暮年规划但最终没有建成的威尼斯医院,位于这座城市的北缘,现在以威尼斯双年展闻名的军火库 (Arsenal) 地区。乍看起来,柯布壮志未酬的建筑──城市项目和斯卡帕微雕式的小品并无关联,但它们同样标定了威尼斯独有的细节和整体的有机关系,,使得这些项目的逻辑共性超越了物理尺度的差异,点线面搁一块儿就像是建筑理论的图解。威尼斯医院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局部的形态学,相反,大多数的单体建筑是近似和雷同的,远看完全就显不出任何“风格”的痕迹,这些眼花缭乱般重复着的细胞所重构的,是城市道路和运河系统,出现了灵活组合的内向庭院,是西方现代主义都市发展中的异数。如此的项目介于建筑和城市之间,既提示了单体结构又铺陈了基础设施,正是 埃利森·史密森 (Alison Smithson) 加以阐发的“垫式”建筑 (mat building) 3,一一相属、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的古怪的巨型大块,提示出了城市中比“形象”更本质的因素,那就是──变化。
柯布 1965 年去世前,委托意大利人芬特 (Guillermo Jullian de la Fuente) 继续这一项目,他的项目之所以中途夭折自然有人事的原因,可是细细想来似乎也属命定──威尼斯已经建在阔水之上,这里并不真的缺乏“变化”。对于变化,在岸上的瑞士人和水上的威尼斯人有不同的理解,对后者而言, 从纷繁的现象开始经建筑又倒回纷繁,费劲儿的“传译”多此 一举。 我在长江边长大,见多了这种风涛变幻的场面:在水中,人们需要适应另一种自由感,初学游泳的人,不能因为恐慌沉没而挣扎,而是要像骑马一样,让自己的身体跟着潮汐律动, 才不至于在没有一刻消停的船舱里晕船。
水中的镜像造就了另一个威尼斯,并不清晰但也许更加真实。风浪鼓舞起潮汐,推动着映入水面的倒影,使得本来已经不甚稳定的风景愈发地迷离,在本地人看来,无论是岛上繁密的城市和粼粼波光中片面的印象都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水上的”和“水中”的威尼斯合而为一,“实质” 和“观感”,“生活”与“服务”的二元律在此失效了。没有四环五环路上飞也似的汽车,使人望而生畏的立交桥,这里富有特色的,是不停在水中波动着的船坞和栈桥,彼此间并不怎么紧密连接的活动建筑,让海潮的压力,在金属碰撞的闷响中逐渐消散到陆地上,物质的对立最终转化为韵律统一的运动。

英语之中有 “trouble water” 这种说法──保罗·西蒙 (Paul Simon) 的老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翻译为“忧愁河上的金桥”,似乎是中文的过于诗意了,“祸水”又有点言 过其实,但威尼斯似乎就是立于这种不安分的 trouble water 之上的。海潮倒涌进运河的力道之大,是一天天停留在这里的我所充分领略的,这种使人心惊的野性,挑战着朱自清看到的威尼斯“团花簇锦似的东一块西一块在绿波里荡漾着”──他没有坐过飞机,不知道是在哪里看的?
无论如何,这绝不是一座“小城”,而是九到十二世纪野心勃勃膨胀起来的城邦国家,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赞助商和出发点,如果你去过始建已近千年,年久失修的军火库,看到拉丁的粗汉坚实的臂膀,想象着当年的战船出发,暗潮涌进城市的各个角落,就会理解这座城市赖以发家的绝不是明信片风景,不是运河里簇集的刚朵拉游船,而是同样不安分的剑与火。威尼斯不止是一座水中的孤岛,它同时也是建筑在一片动荡人心 的海洋上,在世人不定的想象里漂浮,这样的景片,永远是在外来者的眼光里更光鲜。
十七世纪英国贵族所发明的“壮游”(Grand Tour)中, 威尼斯是“堕落的意式诱惑之地”(locus of decadent Italianateallure)。4 起初,“他者”也许是一厢情愿地寻求故事,可是,看来最终故事里的主人公主动加入了叙事。托马斯·布罗德威克 (Thomas Broderick) 写道:“在威尼斯人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有心有肺,却会做脸色的女人,你不能据此推断出,所有的威尼斯女人都是婊子,但在威尼斯人们看起来不顺眼的只能是妓女了。”如果这段话还使人有点费解,罗伯特·格雷 (Robert Gray) 说的则直接一些:“在英国,出于宗教和对真正幸福生活的尊敬,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忠诚和美德的价值,那些出轨的人们被迫改邪归正,要么就得从社会上消失”──可是在意大利不是这样的!他暗示,在这里并没有“荡妇”和大家闺秀的区别,一个正经女人也总是风情万种的。三百年之后,恐怕没有哪个威尼斯女人会反感异乡人这么打量她们,在“天使坠落的城市”,寻常的生活和寻找故事的艺术也合而为一了。
从来没有想到这里的日头如此毒辣,晒得静坐不动的人也常汗津津的,瞬间又让那份热度蒸发光了,黑 T 恤上不一会就留下了斑斑盐花。可是不管天气多热,穿梭于海边酒桌上的 侍者却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白桌布上没有些微酒渍水痕;身后奇观般的建筑,水中摇曳的生活,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不可思议,“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的确,威尼斯到处都有着梦一般的偶遇,陌生人的一见钟情,混杂着失窃和幻想破灭。这不是什么严谨的论文,而完全是一种脚下动荡的水面所滋生的随想或臆想──使人不禁想起庄子所说的 ──“其生若浮”!
如同马可·波罗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向忽必烈汗报告的那样,这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切城市的总和,它的丰富不仅在于它真的品类,而且也在于它不定的情态,威尼斯像风情女子 不像朱自清笔下“日光里鲜明的少女”。满城满街闲逛的“职业旅行者”,就像布拉格,布鲁日,却又比它们更加动荡、喧嚣,这古怪地塞满身心的魅力,让我烦躁、抗拒,直到嫉恨。
我们住在一个小岛上,起初觉得非常不便,因为经历了几天本岛难以形容的喧闹,却喜欢上她一水之隔的平静了。每天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和不能被其它机动助力装置代替的步行,就会拖着汗津津的身体走到码头上的栈桥边,当来接我们的小艇颠簸着离岸时,隔岸的灯火渐渐远去,威尼斯岛的画面像是装了消音键一样,恢复了白昼不曾见的安宁,岸上灯红酒绿,狡黠不失风趣的伙计,依偎在一起亲吻的情人的身形,最终都变成剪影,变成谷歌地图上的画面,万千赞叹不已的建筑细节仿佛还历历在目,这些细节在不同尺度逐次扩大的景框中,最终失效。
无厘头地想起中文的一句成语,人心叵测,就如日本某小说之中的情节,一个人面对此情此景,会臆想这惊人的美突然毁掉,坐在船上面对暮色莅临,又应了中文的一句成语──隔岸观火。
从水上回望,海洋是静止的,而陆地正在移动。
1 “中世纪开始的一个特别例子是威尼斯,它起源于罗马帝国之后的乱世中,在与世隔绝的水域中寻求避难所的岛礁社群,在 9 世纪早期,岛礁王国的首领将他的居所从今天离岛 (Lido) 的位置移到了后来成为圣马可广场的地方,它在不规则形状的小岛群的一个核心位置上,得以壮大发展。这一特别的进程既带来了迷宫般的城市形式,又产生了它的水上街道。”参见 Spiro Kostof,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 Bulfinch, Reprint edition, 1993, p.61.
2 Sebastiano Serlio 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城市图景 (scene) ,悲剧性 (tragic) 的,喜剧性 (comic) 的和讽刺类型 (satiric) 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非如它们的字面意思一样有确定的道德训诫的含义,相反,它暗示着城市形式确实存在着某种超乎文化情境的一般生成路径,一座城市可以“笑着”,它的“表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压倒一切的关注。Spiro Kostof,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 p.223.
3 垫式建筑并不仅仅是这个“语象” (mat) 所揭示的形式特征,它的成立同时需要“硬”和“软”的条件,城市既是低平广大,单体类似且不断重复的聚合体“类型”,也从社会组织和文化社群上成为垫状复合的“超级结构 ”。参 见 Hashim Sarkis, Le Corbusier Venice Hospital (Case Series), Prestel Publishing, 2002.
4 Utrecht 的 Erhard Reuwich 为“壮游”风俗所绘制印行的城市图景广泛流传于当时的欧洲贵族之中,类似于今天既销量广大又强调“独家”,“深入” 的旅行指南,“壮游”在培养高贵风格(Grand Manner)的同时,又培育了蓬勃的世俗好奇心。


《十城画记》
作者:唐克扬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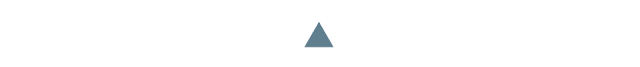
编辑 | 朱玥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识别图中二维码,购买《单读 14 ·世界的水手》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购买最新一期《单读》,成为与我们同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