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撰文|黄大拿
文人搞投机,不是横死就是笑话,这样的教训,会留下来吗?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使命,《论语》上有一句著名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翻译一下:读书人不可以不弘大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
但这样的境界可能太高了一点。历史上,罔顾士人职责,搞投机的文人真是不绝如缕,而且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一
李斯被腰斩前的一声哀鸣
如同影视剧中所描写,一个人告别人世的时候,总是要说几句话的。
类似“遗言”,因为内涵丰富而传世的并不多。
但无论如何,大秦帝国丞相李斯的几句遗言注定会留传千古。
《史记》中说,李斯被秦二世腰斩,临刑前,李斯对儿子说:好想与你重回老家,牵黄狗逐狡兔,可惜再也不可能了!
以丞相之尊,牵黄狗逐狡兔,居然成为一种奢望。但李斯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种必然。

司马迁为李斯作传,开头便讲述了一个李斯与老鼠的故事:李斯看到公厕里的老鼠食物肮脏,人畜一来便惊恐万状,而粮仓里的老鼠则大吃特吃,悠哉游哉,而且看到人一点儿也不惊慌,于是李斯悟出了一个道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意思是说人其实和老鼠一样,你混的如何,关键在于你所处的环境,所居的位置。
从这个所谓的道理里,李斯发现了攀附权势的极端重要。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李斯在秦始皇意外驾崩后的选择。
众所周知,秦始皇属意的接班人是长子扶苏,但因其死出于意外,遂给了次子胡亥一个机会。
当宦官赵高代表胡亥来与李斯商议时,李斯根本没有把赵高放在眼里,斥责说:“安得亡国之言?”但赵高接连发问:“丞相您自己掂量一下,才能是否比得上蒙恬(扶佐扶苏的大将)?功劳是否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是否比得上蒙恬?和扶苏交情笃厚、深受信任是否比比得上蒙恬?”
赵高的意思是说,一旦扶苏当上皇帝,他最倚重的肯定是蒙恬而不是你李斯,这样,你当下拥有的权势可还会存在?
显然,赵高准确地把握了李斯的特点。正因为权势的砝码太重,李斯才可能乖乖入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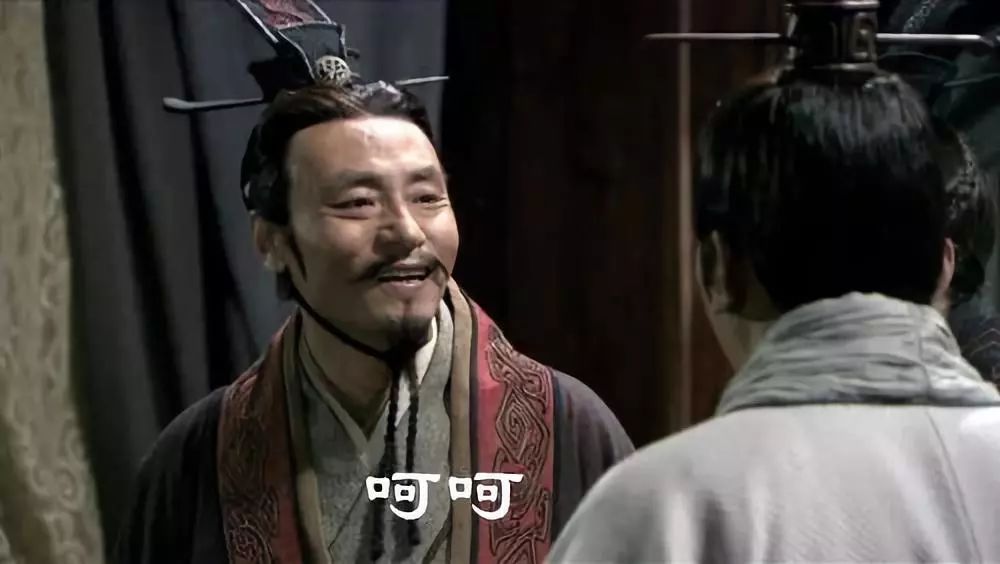
所以,当李斯临刑前的那一声哀鸣穿过历史,在今人耳边响起的时候,大拿只有两个字送给他:活该!
二
献九鼎为什么成为笑话
所居不算陋室,却也远不能说宽敞,买书的欲望近年只好一再遏制。但犹豫了一段时间,终于未能经受住诱惑,还是将精装十二厚册的《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搬了回来。
展卷先看这位史学大师1943年的日记。因为在这一年,政学两界有一大事,也是一件趣闻,而顾氏恰是主要当事人。
1月28日,“将刘起釪所拟九鼎文重作。……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刘起釪是顾颉刚的弟子,这个“九鼎文”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天顾氏日记也有补充云:“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

原来,因为1943年1月11日作为抗战友邦的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废除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复由于国民党官方理论向来认定列强侵略和不平等条约是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所谓“中国与英美之新约”遂成为国民政府眼中可以自矜其功的一大盛举。于是又有了国民党党徒一手操弄的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
“九鼎”之意义,国民党中央社当时的一篇通讯说得十分清楚,“九州贡金以纪念禹之功绩,故自夏至周,世世保守,传为历史上之佳话”,而今向蒋介石献九鼎,正表示其勋绩“较之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诚无多让”也。
至于国民党官方属意顾颉刚来作九鼎文,当然缘于其在士林之声望,同时也因为顾氏以考辨古史闻名,并多次撰文讨论九鼎及相关问题。
然而在顾颉刚那一面,他似乎还没来得及体验被最高当局垂青之荣耀,就很快品尝苦涩了。1月28日当天日记的最后,有他事后的补记,“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

批评究竟来自何方?当然主要还是在顾氏厕身之知识界。1943年5月13日,顾氏日记记载,“孟真(即傅斯年)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
陈寅恪赋诗,还属于“雅虐”,另据相关人士追忆,当时知识界更把献鼎当作一个笑话。
学者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说:“以前在重庆的时候,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奉承蒋介石,要献九鼎,当然都比较小,请人写铭文。四川有许多老先生很擅长此道,但他们都不愿意写,后来找到顾,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实际上他不内行。……后四句是‘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朱家骅有政敌,就去对蒋介石说,他在骂你。四川人骂装疯卖傻者是‘献宝’,把后四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我在(载)献宝’。后来蒋介石看到,果然如此,一脚就把鼎踢翻了。”
程千帆的回忆近于野史,但从这个笑话的流传中至少可以窥出知识界对献鼎和顾氏作鼎铭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态度其实是有传统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倔强地认为“道”高于“势”。
任何一个时代都很难避免不出现几个向权力献媚邀宠的知识人,但如果献媚邀宠成为知识界的笑话,却无疑证明士林正气犹在,文化还有希望。
文人搞投机,不是横死就是笑话,这样的教训,会留下来吗?
往期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