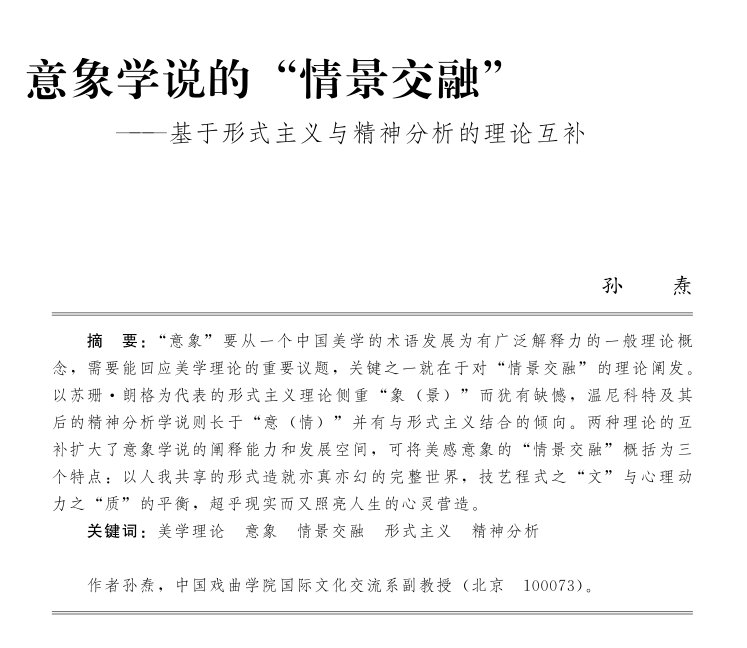
摘要:
“意象”要从一个中国美学的术语发展为有广泛解释力的一般理论概念,需要能回应美学理论的重要议题,关键之一就在于对“情景交融”的理论阐发。以苏珊·朗格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侧重“象(景)”而犹有缺憾,温尼科特及其后的精神分析学说则长于“意(情)”并有与形式主义结合的倾向。两种理论的互补扩大了意象学说的阐释能力和发展空间,可将美感意象的“情景交融”概括为三个特点:以人我共享的形式造就亦真亦幻的完整世界,技艺程式之“文”与心理动力之“质”的平衡,超乎现实而又照亮人生的心灵营造。
关键词:
美学理论 意象 情景交融 形式主义 精神分析
作者
孙焘,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副教授(北京100073)。
责任编辑:
陈凌霄
来源: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P59—P68
作为一个美学术语,“意象”基于中国古代美学并正在发展为一般理论概念。从先秦典籍中的“象”到《文心雕龙》首次出现“意象”,到宋代以后在文艺批评中的大量运用,意象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概念。20世纪,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把意象引入现代美学话语,叶朗进而将之提炼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以意象为核心的美学理论还在继续发展中,并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
一种理论的发展水平体现为其解释力的深度和广度。如果将意象学说的研究和讨论范围限定在“中国(古代)美学”的范畴,无疑会制约其发展成为具有更大有效范围的一般理论,无助于整合国外学术成果以回应当代的理论关切。在文化碰撞交融的今天,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生命力体现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一般美学理论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
首先,一般理论要能为讨论范围划界。
就美学理论而言,包括美感与非美感活动的区分,“美”跟“丑”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理论上讨论丰富多样的“美感”或“审美活动”,需有一个较宽泛的基础概念,至少要比“美”的范围大。但如果一个理论概念至大无外、无所不包,以至没有哪种活动和现象不可以囊括其中,也就取消了这个概念的意义。以“意象”作为核心理论概念也要面对这个难题:或者,把意象作为美感活动的特有产物,所有的美感现象都有其意象,无美感则无意象;或者,扩大意象的解释范围,把美感意象作为诸多意象的一种,并为美感划一个大致的边界或提出一种划界的原则。第一种思路很难成立,仅就常见的学理讨论,“象”来自卜筮易占,指向的多不是美感现象,而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也并非专为解释美感现象。本文采用第二种思路:美感意象是一种特殊的意象,另有非美感意象。有待回答的是:如何概括美感意象的特点?美感与非美感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
其次,如何在美学理论上克服“主客对立”的解释困境?
仅强调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等并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
现代汉语的概念术语倾向于双音节词,而古代术语则以单字为主。对“意象”概念的一个可能的误解,是把“意”和“象”分成两个对等的概念,又徒然讨论两者的关系。这种误解也有超乎术语本身的理由。王夫之对“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的特别强调,暗示着“景”和“情”有发生分离的可能。虽如此,“情景”还是比“主客”更适合成为理论建构的结构性要素。
叶朗把“情景”置于意象学说的关键位置,“中国传统美学给予‘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情景交融’。……这里说的‘情’与‘景’不能理解为互相外在的两个实体化的东西。而是‘情’与‘景’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关键是如何解释“交融”。已有论者提出:“‘情景交融’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述,而不是科学的定义。‘情’指的是什么,‘景’指的又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交融的,又交融在何处,交融之后为什么又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愉悦的情绪,这些都需要回答。”
最后,作为从中国思想脉络中发展起来的一般理论,还要在整合既有的(主要是西方的)学理资源基础上,扩大对美感和艺术现象的解释范围。
有人认为“‘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就是,要么固守中国古典美学的立场而无法涵盖西方的美,要么就是将意象的概念泛化,只保留其情与景作为艺术品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说法设定了“情与景”无法吸收西方的理论和解释中国古代文化之外的艺术、美感现象。其实,探索的脚步早已迈出。从朱光潜吸收克罗齐、布洛等学者的观点,到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研究者借鉴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意象”已不再限于一种古典的文艺批评概念。本文则另从艺术学、心理学领域引入两种学理资源:形式主义理论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新发展,并以两者的交汇互补作为美学思考的他山之石。
虽曰“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但为论述方便计,还是暂就“意”和“象”分别展开——形式主义理论侧重于“象”,而精神分析则重在“意”,其各自的发展都提示了两者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有助于把意象学说的“情景交融”说得更清楚。
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近代可溯至康德,奠基于贝尔和弗莱,集大成于卡西尔和苏珊·朗格。贡布里希对艺术史的理论阐释也与形式主义有所呼应。形式主义理论把美感归为特定的“形式感”,强调构形而非再现,创造先于模仿。朗格之后,因拙于解释构形的心理动力,形式主义学说逐渐式微。但这种理论在美感和艺术分析方面的精卓见解不应随之湮没。
精神分析心理学派则长于解释心理动力。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由弗洛伊德开创,其关于潜意识的揭示今已成常识。弗洛伊德用“升华”解释梦、想象和艺术创作。但弗氏过于强调性驱力也引起广泛质疑,其对美感、艺术的解释也因忽略形式因素而显得粗糙。比如朗格对弗氏精神分析提出质疑:是什么使得诗不同于梦和神经官能症?人们不会嘲笑一位睡眠者的梦做得笨拙,但却可以指责诗人的作品拙劣。
精神分析学说在弗洛伊德、荣格之后的发展有更多可供美学吸取的理论和方法,尚未引起中国美学界的充分关注。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1896-1971)是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其影响深远的概念“过渡性空间”将想象力和创造力置于人格发展的关键环节,他有关攻击欲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哲学中的主客关系问题和形式主义美学的“生命力”概念。英国心理学家肯尼斯·莱特(Kenneth Wright)的《镜像与调谐:精神分析与艺术中的自我体认》(2009)梳理了温尼科特及其后继者的创见,为精神分析的新发展与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结合架设了桥梁。
意象是对存在意义的显现。这在形式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较充分的阐释。
形式主义美学突破了欧洲传统哲学中根深蒂固的“模仿说”或“反映论”,强调形式对于“意义”的积极构建作用。贝尔提出 的“有意味的形式”不易理解,朗格则更简单地说明了“有意味”与“无意义”之间的差别:人能从环境的噪声中敏感地捕捉到音量并不大的说话声,因为后者“具有不同的秩序”,而艺术形式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对此,贡布里希说得更加形象:“我们的大脑是如此渴求意义,它一旦得到唤起,就会不停地寻求和组合,好像它时时都对意义如饥似渴,时时准备吞吃一切能够满足这种渴求的东西。”这种渴求和冲动甚至会为原本无意义的事物编造故事,如夜空中无规则排布的星光点,被欧洲人视为狮子星座,南美印第安人则看成一只龙虾。这并非“反映客观”,狮子、金牛、射手等是构建一种世界图景的语汇,而龙虾、浣熊之类则构成了另一种图景。
具有形式感的艺术塑造了人对世界面貌的感知。朗格说,“艺术是公共的财富,‘被感受的生活’的确切表现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并且为人们铸造了客观世界。只有当自然在想象中构造起来并且与感受的形式相一致时,我们才能理解它……世界似乎变得有意义并且是美的,可以通过直觉‘把握’。”“艺术是人们感受的学校,是他们抵御外部和内心之嘈杂的城堡。”朗格举例说,华兹华斯美化了读者的词汇,巴尔扎克影响了读者的反讽感,绘画领域的雷诺阿和莫奈以其艺术塑造着人们的视觉经验。“自然物只有面对艺术想象时才是表现性的,因为艺术想象发现了它们的形式。”一个例子就是贡布里希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在惠斯勒画出雾之前,伦敦没有雾。傅雷也说,“古人形容美丽的风景时会说‘江山如画’,这才是真悟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的卓识,这也真正说明自然美之借光于艺术美。……没有艺术,我们就不知有自然的美。”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宗白华提出的著名论述:“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
为构成一个能显现意义的完形,首先要创造一个幻象领域,让形式疏离于现实,脱离世俗的职能。伟大的艺术家凭借其创作活动,通过形式和符号帮助普通人体会到现实生命中的完整性,是为“美”的现实意义。朗格说,“人生是支离破碎的,除非我们赋予它以形式。……艺术深深穿透个体生命的原因在于,它为世界赋予了形式,它表达了人类的天性:感受性、活力、激情,以及终有一死。”这里的“形式”不是与人心人情无关的“客观形式”,而是精神世界的构成性要素。此即王夫之所谓“景非虚景,景总含情”。
多数艺术家以技艺为首务,形式主义者则对此给出理论支持。大自然无所谓技艺,人生现实中的技艺多是谋生工具,而艺术意象则得自创造性的构建。朗格提出,悲剧艺术的核心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内容”,而是创作者用戏剧当中“预示未来的行动”构成“悬搁的形式”并造就的“命运的幻象”。也就是说,悲剧之“美”不在一桩英雄死亡的事件,而在该事件在舞台上的呈现。
形式主义理论从意义建构角度指出形式之于美感的作用,但该理论也有其缺憾,主要是无法解释说明虚构想象与艺术创作的驱动力。
创作欲从何而来?人为什么要构建幻象世界?朗格略提及“炽情”和“生气”:“这种炽情是真实的感受,不是音乐符号化之物,而是使符号生生有力之物。它是艺术家对于作品的生命内容具有感染力的兴奋之情,在它失落的地方,符号是冷冰冰的。……它在最终的产品中显现自身,然而永远是一个无意识元素。”“所有成功作品中皆蕴含‘生气’。”但朗格的“有生气的形式”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一样都语焉不详。
形式主义理论多集中于艺术学理论。美学讨论的范围要比“艺术”更宽泛,还要包括那些一般不属于艺术领域的问题。
在此不能展开讨论“何谓艺术”,但至少可以列举诸如自然美和“日常生活之美”等美学问题。即便我们同意傅雷的“自然(美)模仿艺术”,也仍然可以追问:为何在有些情况下自然美得以显现,而另一些情况下则不然?
精神分析重在解释各种人类活动的心理动力,也包含了“为什么欣赏/创作艺术”“为什么追求美”等。弗洛伊德曾把一切人类活动的动力归为“快乐原则”,美感则是被压抑的性欲“升华”的结果。在其思想发展后期,弗洛伊德还注意到人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欲,名之为“死本能”,与追求快乐的“生本能”相对。温尼科特则把求乐与攻击都归为原初的生命力,理论更为简洁一贯。
温氏学说的核心是早期母婴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塑造:人与世界、他人的关系都重现着母婴关系中最初形成的互动模式,无论是支持性的还是创伤性的。无内无外、“主客不分”的婴儿一方面要求得到滋养和保护,另一方面也通过咬、打等攻击方式探索外部世界和自我边界。婴儿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是喂养自己的乳房,其后则是养育者本人(一般是母亲,也可以是其他承担母职之人)。婴儿在攻击中获得了初步的掌控感,形成关于“客体”的最初经验,建立了主客互动的基本模式。随着婴儿逐步将“非我”(母亲)从“我”中分离出去,婴儿觉得这个客体是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婴儿从母亲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然后在镜子中反观,自我意识逐步成形,亦成为美感的源头。
温尼科特为母婴的良性互动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抱持(holding),并以此解释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如果养育者在承受婴儿的攻击后没有离开,婴儿就体验到一个稳定可靠、可享用的外部世界。如果养育者出于无私的爱,跟小小攻击者愉快嬉戏,那么婴儿所面对的对象就是安全、友善的,攻击性即转化成积极进取的创造性。反之,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抱持,攻击性就演变为破坏性,或者导致怯懦自卑(向内攻击),或者凶暴好斗(向外攻击),又或两者兼具。总之,生死同体,生命力最初就伴随着攻击——因爱而转为创造力,因冷漠和控制而成毁灭欲。“抱持”又需有度。温尼科特提倡“刚刚好的妈妈”(good-enough-mother,或为“60分妈妈”):婴儿在确立了基本的安全感后,母亲应适度放手后撤。一定程度的未满足,有助于孩子发展出自己的探索能力,也为其他社会关系(父亲、同伴、陌生人)进入生活留有余地。无微不至的照料(及控制)让孩子迟迟不能自主成长,成年后恐为所谓“巨婴”。
温尼科特认为,“适度的未满足”是个人心理成长的关键,也是想象和创作之源。婴幼儿会因养育者偶尔不在场而感到焦虑,但之前得到充分呵护和满足的体验又让他/她可以在想象中创造陪伴者的替身,即“过渡性客体”。最初可能是一块带有母亲气味的柔软毯子充当了母亲的替代者,之后是用毛绒玩具、各种道具和仪式化行为来构建自己的幻想世界,再后则借助更复杂的游戏、象征性词语、虚构的故事人物等进入“文化”。所有这些都不是成人眼中幼稚可笑的小玩意,而是有意味的意象,是一个安全世界的载体、一个可信任的陪伴者、一种让人体验到可控感的上天礼物。“(过渡性客体)是婴儿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强烈的体验保留终生,并在艺术、信仰、生活幻想和创造性科学工作中表现出来。”
始自婴儿期的幻想不仅是个人性的。“我们可以分享这种幻觉体验,如果愿意,我们甚至可以聚集到一起,并在类似的幻觉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团体,这是人类群聚的自然基础。”在基督教仪式中,红酒和面饼并不仅仅是食物,还是基督的身体。国旗不仅仅是一块五颜六色的布,还是集体认同“想象的共同体”的符号载体。这类“不仅仅是”构成了人类文化无穷无尽的发明创造,成年人与儿童在此并无本质的不同。在这里,“意象”之“意”得到了实证性阐发,并初步跟“象”联结起来。
温尼科特的关注重点还是作为符号化开端的婴幼儿世界。若要进入人类文明的无限空间,还需有更丰富的形式。肯尼斯·莱特的《镜像与调谐:精神分析与艺术中的自我体认》吸收了温尼科特的“镜像”理论并以另一位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丹尼尔·斯特恩的“调谐”理论加以补充。这一步的发展为意象学说提供了更直接的支持。
“调谐”的英文attunement本是音乐术语,即对乐器的调音。斯特恩借这个词表示:婴儿像是一个发出各种声音的“乐器”,而抱持性的养育者则是一位耐心的“调音师”。“母亲持续地‘读取’着伴随着婴儿活动的情感起伏,包括那些攻击性的表达,并回应以能够刻画婴儿‘体验’之轮廓的声音和姿势。经由这种刻画,母亲以一种外部形式重造了婴儿的体验。”母亲体贴婴儿那些不断变化而又无形无状的愤怒、焦虑和喜悦,以自己的表情、肢体动作“返还”给婴儿,而婴儿的感受、观念由此得到了可感的形式。这既是日后理解和表达的基础,也是艺术欣赏与创作的起点。
回到人之初,意义的理解和表达何以可能?理论上,婴儿是情感表达的主体,母亲是其情绪状态的“认识者”,但情感表达的形式又是母亲提供的,婴儿则是模仿者。这最初的“错位”例证了何谓“主客不分”:母亲并非被动地“认识”“反映”婴儿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哼唱、轻抚、扮鬼脸都加入了她自己的心绪和表情。婴儿的感受也并非一个现成的待表达物,而是在模仿中逐渐成形。最原初的表达体验正是人与人亲密合作、共同创造的结果。如果人在婴儿期得到了这种积极回馈,成年后也易同情共感,忧世之忧,乐人之乐,此即中国古人所谓“知音”。良好的养育者是人的第一个知音,更为其造就了知音、共鸣的基础能力。反之,过于自恋、控制欲太强的母亲则不尊重孩子的真实感受,把自己的爱好形式强行输入,造成了婴儿心智的“殖民地化”,导致其成年后发展出种种迎合性、面具化的“假我”。
广义的艺术(以及精神分析治疗)为那些未得到良好养育的人提供了疗愈机会,帮助他们学会体认隐幽的人性,表达深微的情愫。
莱特提出了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动力因”,即弥补幼年时期的母职缺憾,为成年的自己创造一个能够友善回应的养护者。由此,形式主义者强调却未阐明的“有意味的形式”即可被视为一种可共享的情感容器,使人重获被掩盖或遗失的自我。莱特用诗化的语言解释了艺术形式的心理学意义:“歌唱,是把你活在我之中的样子交还给你。”
莱特还提出了早期养育体验与艺术体验的异同。从相通的方面看,最早的创作活动发生于每个人生命的最初期,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应答。经由作品的联结,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应答的关系,重现并继续完善着生命之初的美好体验。
但就实际创作过程,艺术家与婴儿则不能相提并论。婴儿完全不能驾驭表达的形式,只能被动地接受养育者的回馈;禀有天赋且长期训练的艺术家则能调动各种形式为我所用,能整合各种为社会共同接受的技巧,生成可被广泛接受的艺术意象。
经由吸收形式主义的“有意味形式”和精神分析的“过渡性客体”等理论资源,本文开头提到的三个理论考验——美感边界问题、主客关系问题和理论一般性问题——都可收拢到对核心概念“意象”的追问:如何理解“情景交融”?
首先,情景交融造就了意义世界的丰富内容,其中包括了美与非美的区分。
我们无法仅通过研究“审美对象/客体”为“美”划界。翻开艺术史和走进博物馆,今人视野中的“审美对象”往往是宗教、民俗、社交等一般活动的道具。从一幅画的“对象属性”中无法拷问出“美”的标准,且不提还有崇高、滑稽等更复杂的情形。另外,面对同样的景色或形式主义者强调的“完形”,为什么有人能体验到美,有人无动于衷?
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讲“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甲骨文的“兴”字像众手托盘而起舞之形,故有“起、举”之义,彭锋还进而提出这种“起”更接近表演而非劳作。美感之“兴”不只有抽离旁观式的“审美态度”,也有精神状态的整体提升,同时幻化出境随心转的“景”。小孩子在最初的母婴镜像回应中咯咯发笑手舞足蹈,在“过渡性空间”中幻想骑着扫帚飞上天,都是美感体验和艺术创作的源头。后来的游戏、仪式、艺术则为这些早期的情景交融体验提供越来越丰富的形式。
美感与非美感的界限,虽难以抽象地给出概念界定,但可以用案例明示:在游戏中,小孩子当然知道自己在客厅里骑的是椅子而不是马,但他能为椅子所处的现实世界与马儿奔腾的幻象世界划清界限;在戏曲舞台上,演员可以打破“第四堵墙”跟台下观众逗笑,但并不妨碍众人因台上之表演而恍若亲见秋江扁舟、幽闺后院。
其次,“情”与“景”并不对等,“情”是“交融”的主导因素。
“情”既不是“刺激—反应”的被动产物(反映论),也非形式主义理论那种神秘的“审美情感”(自律论),而是幻化景致的能动性、构成性力量。
客体是主体的镜像,是生命力的呈现方式。最早的“主客关系”并不是发生在“人和客观事物”之间的“我与它”的审视关系,而是发生在婴儿和抚养者之间,是“我与你”之间的活泼泼的互动,包括一种转化为创造性的攻击行为。客体在“有生气的形式”(朗格)中成形,这是在人我未分的混沌阶段由抚养者与婴儿共同创造的结果,而创造的心理驱动力则是爱——与人联结的需要,其中具体有被关注的需要、主动驾驭关系的需要、自由表达的需要等,又随逐渐成长和社会化而发展出了对美的需要、艺术创作的需要,以便在越来越冷硬的主客关系中有力量生存下去。
早期经历造就的人际“共鸣”体验还使人敏感于相关物之类比,也增强了人际融合感和分享能力。在前语言阶段里体会到这种融合经验的人,会觉得哲学家们谈论的“主观意识”与“客体形式”之间的分隔、“审美主体如何对审美客体做出审美判断”之类问题难以理喻。
最后,除了“情”是基于人性中深刻的、普遍的需求,不仅限于某种特定文化,同样,“象”或“景”也可突破文化背景的限制。
叶朗把“象”与作为美学概念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象’,西方艺术家喜欢称之为‘形式’,中国古代艺术家则常常称之为‘物色’或‘景色’。……当人把自己的生命存在灌注到实在中去时,实在就有可能升华为非实在的形式——象。”严格地看,学者们会有足够的论据说明中国古代的“象”(或“意象”)不能直接等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形式”。但在一般理论层面的“意象”并非不能涵摄西方美学概念。合理吸收形式主义理论,反而可能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基于物质之声、色、形等的“外在形式”更有理论解释力。理由有二:其一,意象不是任意的某种“客观形式”,而更接近于“有意味的形式”或朗格所谓“完整的幻象”,是属人的而非属物的。其二,意象不会拘于形式的物理属性而被强划为时间/空间艺术(意象)等,更易支持通感性的美感范畴,如《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等。当然,要在理论上更充分地阐明意象概念,还需要更多的自觉建设。
美感与非美感现象的边界在多变的生活中形成和调整,无法仅通过理论概念来做界定。“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的体验也可算是情景交融的例子,却无法让人产生美感——哪怕是“广义的”美感。但意象学说可以把它们包纳进来,在美学理论内部为美感与非美感的划界给出操作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能否让人“兴”,有何评价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有何作用,等等。
前面提到,理论上克服“主客对立”的思维困境是美学理论的重点之一。
首先要反思何谓“主体”。
温尼科特的早期心理发展理论消解了单子化的“个体”,斯特恩、莱特等对形式因素的洞察亦令“外”与“内”的难题稍得解释。养育者的声音、表情等形式固然“外在于”婴儿个体,但由于养育者体贴着婴儿的感受,又在镜像式互动中跟婴儿一起创造,使其“经验”成形与学习发声、表情、肢体姿态等能力同步发展,孩童会觉得这些“外在”形式本就是“我的”。驾驭熟悉的形式构建一个有妈妈、伙伴、仙子的幻象世界会让孩童觉得安心和有趣。这就是最早的“兴”的体验。日后的技能学习、美感体验以至艺术创作是这一过程的复现,只是幻象的种类和规模扩大了,形式也更具有社会合作性,可记录、革新、传播和评判。
意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在心还是在物?这些问题并无意义。温尼科特提出:贝多芬的交响乐等艺术作品、初民们的神圣仪式、孩子们玩的游戏等究竟发生在什么处所?是在“外部”的“客观世界”,还是在“内部”或者“主观”?他自答,这些活动既非“内”(主观)也非“外”(客观),而是位于“第三区域”或“中间区域”,即“过渡性空间”。“过渡性”源于通过幻想获得安全感和可控感的早期心理机制。就此空间及其中的事物,成人和孩童之间要有一个默契:不要去问“这是不是你假想出来的”。这个“假戏真做”的道理普遍适用于游戏、仪式和美感体验等情况。方士庶《天慵庵随笔》谈书画艺术时提出“虚而为实……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也持此观点。
意象正是生成于“中间区域”或“过渡性空间”,其意义不在“反映现实”而是为了“创造世界”。但在理论上还需解释美感的“可传达性”和“可公认性”。据反映论,“客观现实”保障了艺术的普遍传达性,主观想象则是个体孤立的活动,无法得到公共认可。但在精神分析处理的案例里,即便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人狂想也有迹可循,一般的想象和创造更是有范式的。
艺术的可分享性来自创作者对人类共享的基本形式的精妙捕捉和驾驭。在精神疾患和艺术创造之间还有十分广阔的中间地带,比如游戏、神话、仪式等众人共同参与的意象营造。我们不必急于在连续的色谱上为红和黄划一条明确的界线,而首先要看清红和黄的本色,以及它们在整条色谱上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