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rlin 1900 in colour
本雅明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文章里写道:“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长大成人的过程是一条贯穿着“不能回头”魔咒的过程,时间也许是线性的,但人可能不是。我们在时间上行走,走累了就停下来,不自觉地望向童年,这时你会发现,那个曾经柔弱无忧时刻需要依护的孩童竟化作坚强的河水,承载起了整个生命。
小说家司屠曾写过这样的句子:“不管是多么大型的动物,途经一片树林时都是小动物。”“在远处的一片田野里,人人都是小人。隔着许多的时空去看,过去的人类都是孩子。”
/ 1900 年 前 后 柏 林 的 童 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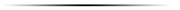
瓦尔特·本雅明
徐小青 译
一九三二年,身居国外的我开始明白,我即将和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作长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告别。
我的内心曾多次体验过“接种疫苗”这种预防疗法的益处。因而在当时的处境中我依旧遵循此法,有意从心中唤起那些在流亡岁月中最激起我思乡之痛的——童年的—画面。而就像不可使接种的疫苗主宰健康的身体一样,这思念的情感也不应该主宰我的精神。我努力节制这种情感,在不可追回的社会发展必然进程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偶然经历中审视昔日的时光。
这种节制的结果是:传记中虽具连续性但不能展现深刻经验的部分完全隐退了,随之隐去的还有我的家人和孩时同伴的外形容貌。相反地,我努力把握住那些包含着市民阶级子弟在大都市中所获得的经验的画面。
这些画面应该接受它们自己的命运,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虽然这些画面尚未像数百年来对乡村童年的回忆那样获得对田园风情的特有表达形式,但这些都市童年的画面或许能够预先塑造蕴含其中的未来之历史经验。至少我希望,从这些画面中可以看出其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失去了他童年时代曾经拥有过的依护。

1900年前后,极端和快速发展的柏林是高度军事化的威廉帝国的中心,在当时欧洲空前繁荣的大都会中,相对后起的柏林展现出非凡的活力。1905年,柏林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两百万,并成为欧洲居住最密集的城市。1900年前后的二三十年中,这个城市进行了根本的重建,其宏大的规模和纷繁的变化使城市的历史和过去几乎淹没其中。本雅明出生并成长于柏林这个城市。他的家住在柏林的老西区,也就是著名的商业街“裤档街”的附近。通过儿时家佣的引领,通过童年的伙伴,青少年时期的放浪,好友的指点,也通过在巴黎的经历,本雅明认识并不断重新发现了柏林。
西洋景
西洋景的特别引人之处是,你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观看都是一样的。因为银幕和座位都是圆形的,所以每幅画面都会走过每个座位。你从两个小镜子中望进去,画面映现在远处黯淡的背景上。棚子里总有空座,特别是在我的童年将要结束时,西洋景已经渐渐不时髦了。人们习惯于坐在半满的棚子里周游世界各地。

观看西洋景的观众
西洋景里没有那种看电影做周游时让人慵懒疲倦的音乐。虽然西洋景里的那种声响有点儿吵人,我却觉得比电影里的音乐要好。那是一种铃声。每当一幅画面跳离屏幕,会先出现一个空格,以便给下一幅画面留出位置,那时就会响起几秒钟的铃声。每当铃声响起时,挺拔的山峦,窗棂明净的城市,浓烟蒸腾的火车站,葡萄园的每一片藤叶都浸透了离别的感伤。于是我确信这一次无法看够那些美景佳处,我决定第二天一定再来,虽然这样的决定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我还犹犹豫豫时,把我隔在外面的木柜后面的整个布景就震动起来,小画框里的画片晃晃悠悠地向左侧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期尚且盛行的西洋景艺术在二十世纪就绝迹了,小孩子们是它的最后观众。画面中那些遥远的地方对他们其实并不总是陌生的,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有一个下午,在那座透明清晰的叫做艾克斯的小城前,我望着米拉波广场对自己说,那梧桐树遮护下的石头小路,不就是我曾经游戏过的地方吗?
如果下雨,我便不在门口的五十张样片的目录前停留。我直接走进放映棚,发现北欧狭窄海湾里和椰子树下的那种光芒和傍晚我做家庭作业时照亮书桌的灯光是一样的。除非有时灯泡突然坏了,使得那自然景色变得黯淡无光。这时它默默静卧于灰色的天空之下。其时,如果我更加留意的话,似乎还可以听得到其中的风声和钟声。

电话机
或许是因为电话机的构造,或许是因为记忆的缘故——肯定的是,小时候,电话机里的回音听起来和今天的迥然不同。那是一种夜的声音,没有缪斯为它报信。那声音所来自的夜就是万物诞生之前的那个夜。隐藏在电话机里的声音就像一个新生儿。电话机和我是同日同时生的孪生兄弟。我得以亲身经历它怎样度过了备受歧视的最初几年。后来,当枝形吊灯、壁炉屏风、棕榈盆景、落地支架、雕花灯台和凸窗雕饰这类曾在客厅里闪烁的装饰品早已衰败和被淘汰时,电话机就耀武扬威地告别了阴暗的过道,迁入了年轻一代所居住的光线明亮的房间,就像神话中被放逐山谷又凯旋归来的英雄。电话机成了年轻一代寂寞中的安慰,它给悲观厌世的人带来最后一线希望,被抛弃的人与它分享榻床。当初和电话机那种被放逐命运相配的刺耳声音现在也因为大家的期待而变得柔和了。
很多使用电话机的人并不知道它的出现曾经在家庭中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我父母亲中午两点至四点习惯午休,如果这时候同学打来电话,铃声听起来就像警报声。此时父母不仅从午休中被吵醒,他们更感到可以心安理得地午休的那个时代受到了威胁。父亲和官僚机构意见不合的情况屡屡发生,有时他甚至对着电话机暴跳如雷,向申诉机构发出恐吓。而父亲更大的发泄对象则是那个电话机手柄。他摇那手柄达几分钟之久,简直到了忘我的地步,这时候他的手就像一个跳狂旋舞的异教僧侣。我心惊肉跳,我肯定,电话机那头犯了错误的女公务员一定会受到被手柄摇出的电流击倒的惩罚。
那个时期的电话机受压抑和受排斥地被挂在过道深处隐蔽的角落,一边是装着脏衣服的箱子,一边是煤气表。在那里,电话铃声把柏林市公寓中的恐怖放大了几倍。每当我摸摸索索地穿过黑黑的过道,惊魂未定地去结束那恐怖的铃声,把头伸进两个像哑铃那么重的听筒之间时,我只有束手就擒,无望地听任于话筒里那个声音的摆布了。什么都无法减轻这个声音对我的控制,我无力地承受着它对我关于时间的思虑、我的计划以及我的义务感的摧毁。就像作为媒介的巫师任凭神之声的摆布,我也心志全失地听从了电话机那头发出的第一个神圣的建议。

农贸市场
首先,你们不要以为它被叫作“农贸市场”(Markt-Halle)。不,那时候人们把它念作“塔乐区”(Mark- Thalle)。就像这两个词由于在发音上的习惯性混淆而变得含糊不清,失去了原来的意思,那些市场的画面也随着我对集市的过于熟稔而变得模糊不清,完全失去了买和卖的基本含义。推开前厅装有沉重的、被旋紧的弹簧拉得颤颤悠悠的门。目光首先盯住了被养鱼水和冲洗水弄得又湿又滑的瓷砖地面,走在上面很容易因为踩到胡萝卜或莴苣叶子而滑倒。在编了号的棚板后面端坐着那些行动艰难的售货女人。她们是掌管可买卖的谷物的女祭司,是兜售各种田里长的和树上结的果实、各种可以吃的鸟类,鱼类和哺乳类动物的赶集的女人,是拉皮条的女人。这些被绒线裹着的庞然大物不可一世地在售货棚之间互相交流着,不管是通过大钮扣闪烁的光芒,通过拍打围裙的声响,还是通过胸脯起伏的叹气声。她们的裙沿下不正是在沸腾,在汹涌,在膨胀着吗?这不正是真正肥沃的土壤吗?这些市场的商品:野果,甲壳动物,蘑菇,大坨的肉和芥类蔬菜,不正是这个市场的守护神亲自投入她们怀中的吗?她们一边把自己献身干它,与它无形地交欢作乐,一边漫不经心地靠在木桶上,或把链子松弛的卖货秤夹在两膝之间,默默地审视着川流而过的家庭主妇们。这些主妇提着沉甸甸的网兜或口袋,牵着小孩艰难地在又滑又臭的过道里往前挪动。
 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
水獭
就像人们试图从一个人住的房子和这幢房子所处的地段得出关于这个人气质和禀性的印象,我也这样揣测着动物园里的动物。鸵鸟在雕有斯芬克斯和金字塔的饰墙前一字排开,河马在宝塔中像巫师一般,它仿佛正在与被它侍奉的魔鬼交合。从鸵鸟到河马,没有一种动物的住处不让我热爱和敬畏。
但是在这些动物中单凭其居所的地段就使自己与众不同的则并不多见。它们住在边缘,动物园与园外咖啡馆和博物馆相接的部分。在这些地段的住户中,水獭是最引人瞩目的。它离动物园三座大门中坐落在列支敦士登桥边的那一座最近。这座门是三座中最少被使用的,并且它还通向园中最死寂的区域。迎候参观者的那条林阴路,因为两旁吊灯上白色的圆球,很像埃勒森或巴特皮尔蒙特的某条僻静街道。在动物园里,这样的角落由于被荒置,显得比古罗马浴场更古老。先前,这些角落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蕴含着即将来临事物的特征。那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角落。就像人们说有的植物可以使人具备预见未来的能力一样,有些地方也具有同样的神奇作用。那往往是些僻静冷清的地方,或者是长在墙边的树,或者是死胡同或是人迹罕至的前花园。在这些地方,一切原本尚未来临的事物仿佛都已成过去。
水獭的住所就是在动物园中的这类区域。每当我迷了路走到这里,我总是欣喜地从喷泉池边望过去,在那里喷泉就像在疗养院中央那样高高耸立。这就是水獭的笼子。这是一个真正的兽笼,因为这只动物所住的人工水池的四周被粗大的铁条封着。这个椭圆型水池以分布着的小小的假山和洞穴作为背景,它们是作为水獭栖息的场所而设计的,但是我却从未在那里见到过水獭。于是我经常在这个无底的黑色深渊前无休止地等待着,期望着能在什么地方发现那只水猢。但是就算我终于发现了它,也肯定只有短短的—瞬。刹那间,这个熠熠闪光的蓄水池居民就又在湿漉漉的黑夜中消失不见了。这个人们饲养水獭的地方当然不是一个蓄水池。但是每当我朝那水里望去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全城的雨水都灌入了下水道,为了汇集到这里,滋养这只动物。因为在此居住的这只水獭十分娇生惯养。对它来说,这个空荡潮湿的洞穴不仅是栖身之所,也更是一座庙宇。这只水獭是一只雨水的圣兽。我弄不清它究竟是从这雨水中诞生出来的,还是仅仅受到它的溪流的滋养。水獭总是特别忙碌,好像它在它的洞穴里不可缺少似的。但我还是在美好的日子里久久地把额头贴在栅栏上,怎么也看不够它。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它和雨的那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因为当雨水用它的有时细细的,有时粗壮的牙齿把一天中的分分秒秒缓缓地拉得更长时,美好的日子就显得更美好,漫长的日子就显得更漫长。它就像一个小姑娘乖乖地把头低在这把灰色的梳子下面。我贪婪地望着那雨。我等待着,不是等它慢慢小下来,而是等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地簌簌飘落。我听见它敲打着窗户,听见它从屋檐流下,潺潺地注入下水道。在好雨中我受到完全的庇护。而我的未来在雨中也潺潺地向我流来,就像人们在摇篮边唱起了小曲。我十分地明白,我们在雨水中成长。站在灰暗的窗户后面看雨的时候,我仿佛就在水獭的身边。但是,只有再次站在它的笼子前,我才会觉察到这一点。那时我又得久久地等待,直到那个黝黑闪烁的身体跃出水面,随即又飞快地窜入水底,去做紧急的事情。

一则死讯
那时我大约五岁吧。有一天晚上,当我已经躺在床上时,父亲出现在我的房间。他来和我道晚安。他不太情愿地告诉了我一位表哥的死讯。这位表哥年纪已经很大,和我也不怎么相干。父亲斟酌着其中的每个细节,我对他的叙述有些漫不经心。然而对于那一夜房间里的气氛我却铭记在心,好像我当时就预见到某一天我还会和它发生瓜葛。在我成年后,听说我的那位表哥死于梅毒。我的父亲来到我的房间是因为不想一个人独处,但是他找的是我的房间,而不是我。那个晚上,父亲与房间都不需要知己。

捉迷藏
我对寓所中所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都了如指掌,回到这里,就像回到一幢可以确信一切如旧的房子。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屏住呼吸。在这里我被一个实体世界所环抱,我深深地了解这个实体世界,它默默地与我亲近着。正如只有被施行绞刑的人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绞索和绞架,站在门帘后面的那个孩子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白色的、飘飘幽幽的东西,变成了魔鬼。他蹲在餐桌下面,桌子使他成了庙宇的木制神像,那四条雕花的桌腿就是庙宇里的四根柱子;孩子在门背后自己也就成了门,他与门一起装扮成一副重重的面具,像巫师那样使每一个没有戒备的进入者魂不守舍。他万万不可被找到。当孩子做鬼脸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如果时钟敲响,他的脸就会保持这副鬼样子。对于这种说法,我在捉迷藏的时候才知道有些道理。找到我的那个人在桌下把我变成僵硬的神像。永远把我像幽灵一样织人门帘。或者施魔法把我一辈子定在沉重的门里。而我则在那个入来抓我的时候大叫一声,把身体里那个使我中了邪的魔鬼放出。是的,我不等他对我下手就发出了自我解放的怒吼。就这样我不知疲倦地与魔鬼厮杀拼斗着。而寓所也成了面具的聚宝库。这些隐秘的地方就像空空的眼窝和呆呆的嘴巴,这里一年一度被藏进礼品。我对法术的了解于是成了学问。我像一个工程师那样为父母的阴暗寓所解除了法术,并在那儿找到了复活节彩蛋。

驼背小人
小时候,我总喜欢一边散步一边透过铺在地面上的栅栏向下窥视。这种栅栏让人可以向橱窗里观望,橱窗前的栅栏下有一个洞。这种洞穴是给地下室天窗透气和透光用的。这些天窗与其说是开向露天的,还不如说是开向地的深处的。我的好奇心由此而生,我透过脚下栅栏的铁条向下张望,为了在这种一半露在地面的地下室里看到一只金丝雀,一盏灯或者一位住户。如果我白天的期待一无所获,当天夜里事情就会反过来,在梦里会有目光从地下室向我注视,让我动弹不得。这种目光是地下那个戴着尖帽的精灵向我射来的。它刚使我毛骨惊然,便随即骤然消失。因此当我有一天在《德语儿歌集》中读到下面的诗句时,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我想走下地窖,开桶去把酒倒;那儿站着一个驼背小人,它把我的酒罐抢跑。”我认识这群喜欢恶作剧,喜欢落井下石的家伙,而且他们以地窖为家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群无赖”。坚果山上偷小公鸡和小母鸡的夜贼——大叫“天要黑啦”的缝衣针和大头针一一都是同样货色。他们可能对驼背小人更知底细。而我却难以接近他,直至今日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妈妈早就向我透露过他的存在。“笨蛋向你问候。”当我打碎了什么或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妈妈总是这样说。现在我终于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了。她说的就是那个盯着我看的驼背小人。小矮人如果盯着谁看,谁就会心不在焉。他既不留心自己,也不注意那个小矮人。他神志恍惚地站在一堆碎片前:“我想走进厨房,给自己做一小碗汤;那儿站着一个驼背小人,它把我的小锅打碎。”他出现在哪里,我在哪里就会变得两手空空。我望洋兴叹,眼看着一切渐渐变小。直到几年后大花园变成了小花园,大房间变成了小房间,大长椅变成了小长椅。‘已们缩小了,仿佛和小矮人一样长出了驼背。那个小矮人到处抢在我前面,堵住我的道路。他并没伤害我什么,只是这个灰灰的倒霉鬼不时让我重新忆起那些几乎被我遗忘,然而曾经属于我的东西:“我走进小屋,想吃麦片糊糊;那里站着一个驼背小人,已经吃了我的半碗糊糊。”小矮人经常这样地站在那儿。只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而他却总是盯着我:在我躲藏的地方,在我伫立的水獭笼子前,在冬天的早晨,在走廊里的电话机前,在蝴蝶翩飞的布劳郝斯山,在铜管乐声中我的冰道上。他虽然隐退已久,但是他的声音如同煤气灯的咝咝响声,在世纪的门坎上对我轻声叮呼:“可爱的小宝宝,唉,我求求你,请为驼背小人一起祈祷!”

《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英文版封面
|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早在一战前夕,他就积极参与了寻找新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青年运动”。二十年代中期,本雅明的教授资格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遭到拒绝,从此他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在三十年代初的德国,本雅明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批判者了。他的写作风格独特,并且不拘泥于散文、文学评论或人文科学论文的文本划分。 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不得不逃亡国外。1940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本雅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波特博服用过量吗啡身亡。
文章摘自《驼背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02
编辑:野行人
([email protected])
#飞地原创整理,转载请提前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