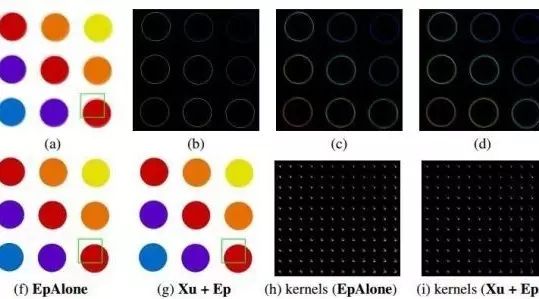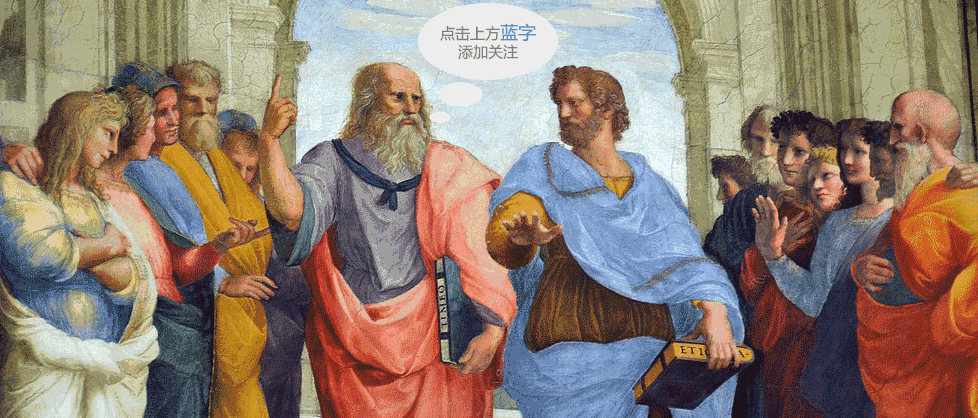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一个哲学家的自我认知
本文选自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哲学自传的体验》序言

俄罗斯总能孕育出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丝毫不比西方哲学家的逊色,更有其独特和深刻之处,但在他的《自我认知》中,也能看到他的思想主要受到康德的影响,还有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作者在这本书中以自述的方式描述了自己学习哲学的过程,“在我写的这本书中,不会有臆造,但会有我对我的生活的哲学认知和思考。这一哲学认知和思考不是关于过去的回忆,这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它发生于当下的一个个瞬间里”。这本书并不难读,甚至可以说是有趣。
别尔嘉耶夫: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以理论体系庞杂、思想精深宏富享誉西方世界。一生共发表有43部著作、500多篇文章。1874年3月6日生于基辅。他的家庭属于俄国的开明贵族阶层,受到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这使他从小就既有贵族的孤傲,又全身心地追求自由。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数千年来,已有无数的哲人智士提出过这个问题,留下了各式各样的解答,但似乎还没有一种答案能圆满地解决它。人是一种充满悖论的生存,他既高贵又卑劣,既仁慈又残忍,既痛苦又快乐,既自由又奴役,既崇尚精神又沉溺物质,既理智又激情,由此铸成了一个幽邃难测的司芬克斯之谜。
作为一名生存论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同样无法回避这一难题。他的研究便从探索人的个性作为起点,“人即个性”。他认为,只有当人以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性进入此岸世界,方能阻止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继续堕落,打破桎梏人的秩序,重新建造一个充满神性、良知的新世界。
按照别尔嘉耶夫的理解,个性不属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它属于伦理学和精神的范畴,与无限性密切相关,并不混同于周遭世界的有限形式。个性是动力的,而非静态的,但又是变化中的恒定、多样性中的统一。个性是有理性的生存,但又不被理性所决定和限制,它充满了非理性的激情,具有戏剧般的张力。个性是主体,甚至是“主体中的主体”,是真正的存在,它只能走向创造,而不应被客体化。至于个性的实现途径,则是抗拒和超越。
现实世界充满了邪恶、奴役、欺诈、不公、混乱,唯有坚决抗拒本能的堕落,在苦难的剌痛中激活自身才能凸现个性,向往上帝之国,走向拯救的可能。“超越,是一个蕴含着动力的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是一种深刻的内在体验。具体而言,意味着在自己的生存中体验地狱、深渊、灭顶之灾,顿生阻断之感,引发创造的举动”。人是动物,但又不仅仅是动物。动物只有条件反射,没有思想和超越。人却不同,他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满现实,就是他的敞开性。人哪怕处在生命的谷底,也依然会向往超尘脱俗的高远天空。
但是,强调个性不等于个人主义,更不是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者躬行自我隔绝,自我肯定,把个人作为展力的竞技场,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作豺狼关系。在本质上,个人主义的行为是一种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行为,是向外抛出的行为。个人主义对统治、强力、功名、享乐的企盼和渴望使人沦为客体的奴隶,在奴性地对待“自我”以后,又不得不奴性地对待“非我”。这样,个人主义在扼杀了别人以后,也戕害了自己,因此造成了精神核心的丧失。个性则不然,它植根于自由王国,“具有亲和的倾向,希望达成人们的兄弟友谊”。
具有个性意识的人,其服务意识也极强,他们时时肩负着人类的永恒的使命。他们丰盈、充实的孤独与个人主义者的寂寞、孤芳自赏不能同口而语。个性既是精神的生存,又是具体的生存,它在渴慕上帝、渴慕神性、渴慕天堂的同时,并不回避尘世的苦难,而是以一种“俯临之爱”向下介入,去拥抱承受着灵与肉煎熬的人们,帮助他们脱离金钱、情欲、功名、利禄的诱惑与奴役,去成就个性,成为自由人。
自由高于存在
人的个性能否实现,与自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传统的本体论认定,共相——普遍的事物是真正的存在,殊相——个别的事物是派生的、从属的和虚幻的存在。理想、理念的存在是真实的,至于多样的、个体的世界不过是第二位的、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的。这样,它就把一切个性的、自由的元素强行纳入了一个普遍的、必然的王国之中。客体化的决定论控制了自由的生存。别尔嘉耶夫坚决反对和拒斥这种理论,他认为,正是个性、殊相包含着普遍、共相,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概念的生存,一切必然性、客体化都是幻象,都是虚假的生存。
关于“存在与自由”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声称,“自由高于存在”。因为,自由并不是由存在所引出的,自由植根于‘虚无‘,植根于‘无底’、‘非存在’”。存在是静止的、凝固的,是自然主义臆想的事物,是抽象的概念,它指涉自然、本质,指向物和抽象本质的既定秩序,是世界的客体化和理性化,是精神被异化了的世界。自由则不然,它是动态的、开放的,是具体的精神。它指涉创造、真理,是此岸世界的阻断和终结,向上帝之国的飞跃,是自我向精神的回归,是主体之个性的确立。
在别尔嘉耶夫的心目中,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更不是强力意志的自由,不是意味着随心所欲的自由。独裁者的自由、暴君的自由是自由的幻象,它实际上是人受奴役的一种变形。表面上,暴君和独裁者在“自由”地“统治”,“自由”地“占有”,甚至“自由”地剥夺他人的“自由”。实际上,他们已被客体化、异化的世界控制着,成为某种理念的奴隶,成为某种被抽空了具体生存的玩偶。因此,别尔嘉耶夫提醒人们,要警惕对自由的滥用。“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它完全不是轻松自在的事物,而是意味着一份艰难、一份沉重。
把自由看作轻松自在和无拘无束的同义词,是一种颓废的自由观。那样的话,创造的责任就会被消费的本能所替代,自由就在虚假的定位中逐渐退化,最终完全丧失自身。实际上,自由在更多时候意味着自由的斗争,它是对客体化、必然性、决定论的世界的反抗,自由是扩张和创造,是个性力量充盈的显示。自由是上帝赋予人去追求真理的义务,而追求真理的道路布满了荆棘。自由的最高境界是精神生活的自由,自由的最低境界是物质生活的自由。由世界的物质性走向精神性,由碎裂走向整体,由暂时走向永恒,人断地完善自己,去贴近上帝,这是别尔嘉耶夫所理解的自由之路。
创造是人的使命
在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哲学中,他最感兴趣的不是“自由在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理念,而是社会生活中它的影响之主要形象”。自由的真正问题是创造的问题,人们通过自由,可以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一种与此岸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换句话说,自由的最大义务就是创造。
创造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根本目标,是人的使命所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零碎的、混乱的、充满了缺憾的现实。人是一个小宇宙,他是世界的中心,存在的中心。作为个性的生存,他超越于世间万物之上,拥有变革现实的内在需要,以求趋达无限和永恒。如此,创造的行为就成了人脱离异化世界的突破口。
别尔嘉耶夫自述,“关于创造,关于创造的使命之主题是我一生的基本主题。对我而言,这一主题的构成并不是哲学思考的结果,而是内在的体验,内在的领悟”。在他看来,创造把人从恐惧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是源初独到生命,既不面向过去,也不固向未来,它面向的仅是永恒。创造是人由堕落的世界向崇高的、神性的世界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站立在律法伦理学和救赎伦理学之外,创造者以创造证明自身。
创造者和创造对拯救和毁灭一类问题毫无兴趣。创造行为具有自足的价值,它不受任何外力的审判。因此,别尔嘉耶夫希望建立一个创造伦理学,以摆脱虚伪的道德束缚和非人性的规范制约。在创造伦理学中,惩罚的恐惧与永恒苦难的恐惧不起任何作用,创造性和神性是同一的。基督教伦理学仅有关于救赎的道德,缺乏道德的创造,这是它在现代衰落的重要原因。在创造者与社会的关系上,別尔嘉耶夫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诚然,创造者是孤独的,创造活动有着强烈的个体特征。
但是,创造者决不囿于自我,恰恰相反,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的扩张,创造的目标永远指向自我以外。因此,创造的的成果总是具有世界的、全人类的、社会的特征。实际上,创造意指的是人超越自我的道路。它在展现人之个性的同时,最大可能地蕴含了人的共性。
人的精神拯救
别尔嘉耶夫认为:“哲学和神学的沉思起点既不在于上帝,也不在于人,因为这两个起点都遗留着不可克服的断裂性”。以往的有神论把上帝想象成天堂的君主,把神性生活想象成天堂的帝国主义。上帝被描绘成一个残暴、傲慢、封闭的独裁者,成了一种绝对的存在,握有至高无上的权杖,任意对人施行奴役和凌辱。别尔嘉耶夫指出,这种做法使上帝变成了偶像崇拜最后的栖息所。在此,他抨击了索洛维约夫的“万物一统”理念,认为后者依然包含了抽象化和客体化的弊端,其中没有任何生存性。
一旦人被剥夺了与上帝对话的自由而成为奴隶,上帝也就成了决定论的上帝,顷刻间便会由主体的生存转变为客体的存在。而依循无神论者的思路,人是一个自足的存在,他是世界的本体。人成了自己的尺度和标准,人是自己的最高存在、最高价值。这一点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人类学中尤有显著的体现。人无限地膨胀,被神化,最后被抬高到原先的上帝之尊位。仅从表象上看,这似乎是对人的一种提升,自我的高扬。
实际上,人已被抽掉了具体的、鲜活的生存性,同样石化为一种封闭的存在,从而丧失了创造的可能。“倘若人就是上帝,这将是最无希望、最平面和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无神论认可人的自足性,也同样意味着认可了此岸世界的自足性。这样,此岸世界中的种种丑陋与邪恶也便没有了消除的必要,真正完满的世界也就永远不会到来。
在《自由精神的哲学》中,别尔嘉耶夫写道,“宗教生活的本真现象是人与上帝的相遇和交会、上帝向人的运动和人向上帝的运动”。人和上帝都不是抽象、绝对的概念,而是创造的生存。上帝与人是面对面站立着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运动。上帝诞生于人之中,人诞生于上帝之中,没有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上帝的存在,唯有人这一上帝的创造之存在,才使上帝成为上帝,上帝与人一起现身。
别尔嘉耶夫在此的思路暗合了里尔克的一首名诗《当我死后,上帝,你可怎么办?》中的祈祷辞:“你失去我就失去了你的意义,我死后你就没有了家。”同样,没有上帝,人的存在也失去了任何意义,他与生俱来的缺陷与不足就找不到修正的参照,灵魂也失去了寻求的目标。与此相伴随的是,他的人性与自我永远沦入了无底的深渊。人是上帝的创造,上帝是人的主题。
维系着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是一种爱,是无限的精神之渴念。这种爱之关系的体现是双向的运动。上帝向人的运动是一种向下的运动,是天空俯临大地的运动;人向上帝的运动是一种向上的运动,是大地飞升天空的运动。圣子基督的出现是这两种运动的具体化,他兼有神性和人性。
基督的降临,为尘世带来了天堂的、纯洁的、神性的元素,他主动为人类的罪孽、堕落、腐朽承担责任,承受走向十字架的苦难,以自己的生和死给芸芸众生以启示,让堕落的人抛却堕落的世界、净化自己的灵魂,转向上帝,应和上帝的呼唤,满足上帝的爱之渴求。神人基督是爱者与被爱者的统一体,他既是爱的施与者,又是爱的接纳者。“通过基督一神人,赎罪者,世界之拯救者,来自上帝和人,来自天惠和自由的两种运动交合到了一起。”
上帝以天惠的能量帮助人战胜罪孽,激发人的自由之爆发力,人则以自由之纵深回应上帝,向上帝敞开自我,藉此继续世界这创造的事业。别尔嘉耶夫告诉我们,人不是奴隶,不是虚无的存在,他是上帝之创造事业的参与者。上帝需要人,需要他来证明自己的创造,丰富自己的创造;人需要上帝,需要他来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最终摆脱此岸世界的羁绊,成为精神的、永恒的和崭新的人。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这是镌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口的一句格言。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便是响应这道神谕的一次出色的尝试。在我看来,这是他最充满灵性、最能显示其创造个性的一部作品。正如作者的自述,这部著作“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忏悔录”,而是他的哲学命运史,他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作为一部自传,别尔嘉耶夫所要叙述的不是个人的外在经历,不是一系列事件的逻辑发展,而是自己内在的精神历程。
这一点与作者对时间独特的理解有关。别尔嘉耶夫把时间划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三种。宇宙时间是一种数学时间,它是可以分割的时间原子,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具有节律的同时,受到了宇宙的切割,被植入了致命的病菌,人在这一时间中生活,死亡便无可幸免。宇宙关注的是普遍,是共相,是自然,根本不在乎人的个性和整体性。
历史时间是一条无限伸展的直线,一方面,它凝聚将来,在将来中等待意义的揭示;另一方面,它又依附于过去,历史的事物由记忆和传统建构而成。历史本身关注的是抽象性和中间性,因此,它忽略具体的生存,是个性的客体化和异化。历史在寻找过去时,会产生保守主义的幻象,认定过去是美好的、真实的、圆满的;当它投向将来时,又以为将来是意义的终端,是美好之完成,从而把现在作为工具、手段来牺牲,奉献给虚无缥缈的存在。
在別尔嘉耶夫看来,历史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在自己的限域之外,也即是说,历史的意义只在历史终结以后才显示出来。别尔嘉耶夫最为推许的是生存的时间,生存时间是一个点,它着眼于现在,是一种内在的时间,属于主体世界,它不经由数字的计算,不能组合,不能分割,它不是永恒,但又关联于永恒,是永恒的符号和象征。每个人内在地体验到瞬间,在瞬间中进行创造的同时,也就溶入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