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是一篇深度访谈,约8000字,需要阅读10分钟。
在刚刚揭晓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年轻导演黄进执导的《一念无明》获得男配、女配、新晋导演三项大奖。

《一念无明》
这部影片于前几日在国内公映,虽然排片和票房难言理想,但获得口碑非常高,
「影向标」评分暂居今年华语片第二名,
仅次于金马奖最佳影片、另一位大陆年轻俊彦张大磊的《八月》。
导演
黄进
与编剧
陈楚珩
为一对恋人,两人同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专业主修电影艺术。他们这对导演、编剧组合很早就确定下来,曾于2011年香港鲜浪潮短片比赛中初试啼声,获2012年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提名。

黄进和陈楚珩
2013年,时逢香港电影发展局于推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两人凭《一念无明》获首届大专组优胜奖,得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影片在两百万的预算下,拍了十六天,演员曾志伟、余文乐都是零片酬出演。
《一念无明》于2016年完成,成为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唯一港片。初初在香港,只是一系列小规模放映,口碑逐渐发酵,后势强劲,后来在金马奖、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及金像奖上收获颇丰。
我们认为,黄进导演未来将成为非常重要的香港导演,因此应该从最早的时候密切关注他,见证他的成长。一个月前,虹膜特邀香港影评人乔奕思在香港采访了黄进导演,下面是采访全文,非常精彩。
地点:香港北角1563 at the East
采访人:乔奕思

黄进在片场
虹膜:在《一念无明》获得广泛的赞誉之后,很多媒体都介绍了你与编剧陈楚珩的求学经历。请问你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呢,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黄进:我的成长经历比较简单,是个幸福的人。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生活在简单、稳定、融洽家庭里。我在公屋长大。成长虽然没有什么很值得炫耀的东西,但这种无风无浪我认为已经很幸福,很感恩。
有时候有人问我写的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经历,其实很少是我的,反而是一些状态,一些思考,让我能够从某些缺口进入一个角色,进入一个戏剧中。
很难说所有东西都是要经历过才能够拍成电影。透过电影,观众可以体验一个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在别人的生命中关照自己,但是你要求观众去做这个事之前,导演也要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行。你不能要求每个我拍摄的东西都要经历过。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关于人的情感方面,如果情感是真实的,人性是真实的,人的关系是真实的,很容易就能找到你能够喜欢上的地方。五百年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可能配套不同,硬件不同,但五百年前的爱恨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我相信有些东西是永恒的。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就算是发生的框架不同,也是每天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为什么观众那么受到触动,可能这个就是原因。
虹膜:你和编剧陈楚珩选择了躁郁症这个比较特别的题材,而且与香港的「㓥房」(注:把一套房子分割成若干独立小间分别出租)现实紧密相关。你们如何尝试去拉近与这个题材之间的距离?如何丰富电影的真实感?
黄进:其实大量的东西真的是来自访谈,现在看到的电影只是冰山一角。其实在幕后的东西,观众是看不到的,也是访谈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例如曾志伟作为一个货车司机,他拿着很多货车司机的真实背景故事。他这个角色有自己的人物背景,在哪里出生、读书、初恋、几时见到金燕玲,都隐藏在故事后。

「㓥房」
虹膜:其实每个人物都是有小传的?
黄进:是的,每个人都有的,这个也由编剧陈楚珩来写。这个很重要。只要角色的背景故事足够丰富,演员就能很清楚这个人为何走到镜头前面这一步,当下这个情况如何改。
我给出任何一个情况,甚至说明天要拍的戏不一样都好,演员都应该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因为这个人是活的,我并不是因为效果、计算,说这个人到了这一步就要做什么,而是这个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黄大海这个人是存在的,阿东这个人是存在的话,他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想?会怎么做?
这个也是我们老师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电影永远是跟着人走的,故事不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如果人的情感是真的,他在哪里都是可以有戏剧的。
尤其是在香港。人物是有很多东西做的,包括很多观众也被这个故事所触动,都是因为演员能够感受到人物。当他们很重视人物情感的时候,观众就能够感受得到。

虹膜:你们做了哪些访谈?
黄进:集中在精神病患者,有些是康复了的,很多案例都是不一定能够康复的,只能够尝试与病症相处下去,很多是社工。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访谈对象是一个以前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后来他去做社工了,他们很集中去做关于精神病、情绪病的社区支援,他也有比较立体的观点。
还有医生,一些私营的医生,也会有不一样的观点。我们也访问了患者家属,还有牵涉到其他,货车司机、教会等。其实能够涉及到的我们都会去问、去听。往往现实才是带给你最多戏剧的地方,你如何去设计都不够真实生活那么令人惊讶。因为,命运就是这样。
所以故事里面很多对白、戏剧的内容、情节都是真的。很多对白是其实有人这么说过,说给我们听。教会那条支线,原本是来自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的。

虹膜:就是方皓玟在教会做分享的那场戏?
黄进:对。其实那个分享本来是为了修补关系,所以将亲人带去教会。但本来以为自己准备好了的分享,却演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有时候就是这样,即使很爱也好,会用错方式。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有时候能够伤害你的都是你最爱的人。你越爱越重视,就会有越大的机会伤害对方。这些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

方皓玟饰演未婚妻Jenny
虹膜:关于教会那场,方皓玟用了多长时间去演,是很顺利的几个take就过了吗?
黄进:方皓玟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我一直也有和她在猜、在研究这个表演应该如何进行。因为我们拿捏着一条很窄的线,很容易就走歪了。如果邪气了一些,让人感觉到一点刻意的报复、伤害,就不好。
如果过于温柔,又没有了那个力度,很难掌握。作为导演,我知道想要什么但我不知道怎么演出来,她作为一个演员能拿捏到一条这样窄的线,真的就走了过去,我觉得很感动。我之前也是知道她可以做到,但没想到可以做得那么好。
我和她相处了之后,觉得她很厉害,她蕴含着很多表演的能力,当然和她的经历有关。通过教会的表演,我能够感受到她是个很自主的演员。自主的意思是她能够操控自己,操控自己的情绪、肢体。她掌握得很好,你不会觉得她是做出来的,她表现得很自然,这个很厉害。

Jenny教堂戏
虹膜:我看完教会分享这场戏之后,对这个角色不讨厌,反而印象更加深刻了。
黄进:这个就是难的地方,她能够带来这样一个那么大的伤害之余,你不会觉得她是坏人。这个也是贯彻整个《一念无明》的宗旨——没有一个是坏人。就算里面的妈妈怎样怎样,带来了多大的痛苦,我都不觉得是一个坏人。他们只是很执着,很软弱或者很爱,但是他们无形中造成了很多伤害。
每个演员都拿捏得很好,也让我们有了一个共识,我们没人是坏人。对于演员来说很重要,演员自己也知道。港产类型电影是这样一个套路,如果他是一个奸人角色,那么他够奸诈吗?
《一念无明》不是一个令人很开心的故事,里面会有一些坏的事情发生,但我不想将坏的东西推到一个人身上,说是因为这个坏人就算了。因为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是大坏蛋,虽然存在,但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绝对的坏人。

金燕玲饰演阿东母亲
虹膜:正如你说,你和方皓玟沟通的时候,她能够很快找到最好的表演方式。那么余文乐这个角色,阿东,是个情绪病人,也需要有很精确的定位。你是怎么和余文乐沟通,怎么和他定位这样一个并不是坏人的角色呢?
黄进: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是来自很多真实故事,我们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消费去做这件事,甚至很多尝试都是想突破一些标签,透过电影、戏剧让观众感受到一个真实活着的人,让你用可以和他相处的方式去阅读这个人,理解这个人。
大家有这个共识的时候,就会很小心。不是为了效果,而是会想这个人是否真的会这样,或者我们的呈现是否真实。这个对演员来说也是不同的演出、思考方法。

曾志伟先生,是一个很精准的演员,我们经常让他不要这么准,因为他真的很尖锐,很厉害。他长期以来的演出锻炼,让他很了解镜头。他作为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可以做到很多,前提是他明白我们要的是什么。
每个人看着剧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演出的方法。比如说余文乐,一来他很怕做那些很张狂的演出,二来他相信阿东这人。其实阿东那个角色并不是很悲哀,他的一些struggle(挣扎)都是希望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准则框架,他想去做一个正常人。余文乐很好的把握住了阿东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都尊重这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
虹膜:作为导演,你认为对阿东这个角色来说,哪场戏最关键?
黄进:很多都很难,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吃巧克力那一场。不仅是表演上,生理上也很难。那场其实我让他吃了很多。我一开始只是需要一个数量,一个力度,但是他对自己的表演也很有要求,也想要那个状态——是那个巧克力治愈了阿东。

阿东在超市吃巧克力
治愈,其实是很抽象的东西。我不想折磨他去做这个MOMENT,但他很坚持,他要求自己这么做,吃了很多。余文乐的很多表演让我很感激,正如我刚刚说的,我有很大责任去守卫这个故事,很执着做好这件事。
但当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演员一样给你相同的力度,他基本上也会奋不顾身去做。我也知道里面很多场合余文乐用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去表演,其实很伤身,用了很长时间去复原、再抽离。
他也决定将这些演员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而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值得演员去贡献那么多。他看着我这样一个新导演,也不知道这一部电影出来结果会怎样,如果我拍坏了怎么办,他也决定了去博一搏。当然我不知道他真实是怎么想的,但我是很感激的。

阿东照顾母亲
除了教会那场戏,我还喜欢他帮他妈擦尿那一场。其中的情感击中了我。母亲与儿子一开始还互相伤害,进入了一个私密空间后,去到一个赤裸的地方,阿东望着妈妈帮她擦尿,你可以发现他们两个都很爱对方。
他们不懂得如何相处,但互相很需要彼此,没了谁都不行。我看演员的演出是很刺中我的。当然写的时候我有想象过那场戏怎样,但远不及演员演得那么动人。
虹膜:在你和编剧陈楚珩面对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是如何思考创作者与题材之间的距离的?有没有想过是要近一些还是远一些,主观一些还是客观一些?
黄进: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距离是怎样的呢?

虹膜:整个故事中没有非常激烈的东西,比如说金燕玲饰演的阿东妈妈在浴室死亡的那一段,是刻意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的。但在很多时刻,又尝试拉近,比如阿东女友在教会分享那场戏,还有最后阿东躁郁症恶化的几场内心戏。你和编剧陈楚珩考虑过主观和客观的问题吗?还是很自然就选择这样处理了?
黄进: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你觉得这个这么暧昧的距离是否适合呢?
虹膜:对我来说,在很多场口,镜头的远近、创作者的选择都出乎我的意料,避开了既定的表现方式。所以,你和编剧陈楚珩之间就这个问题是没有讨论过的吧?
黄进:我觉得编剧陈楚珩是比较近的,而我拉远了一些。我整天想到Michael Haneke, 他也是那种「后一点」的感觉。这不代表他不关心人物,但他保持了一种平静的批判。我不能够将我和他类比,但创作者如何看待题材,这一点很重要。

《笼民》(1992)
张之亮导演的《笼民》,粗中带浪漫,一群麻甩佬,穿着底裤唱歌。他的处理就近一些,人文一些,批判少一些,没有那么硬。可能这种处理方法,并不是我抗拒的,完全是因为创作者的性情不同。
我有时候凭直觉,所以没有审视过这样对不对。不过有些决定是很直接的,比如说我们一早就决定不拍浴室中到底发生什么就一定不拍。
当然阿东妈妈是怎么被击中的,流多少血,死前的样子,这些都不是重点,也容易带观众离开重点,重点是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重点是这个人以后怎么活下去,而不是那些激烈的画面。
坦白说我不会忍心拍这种镜头,如果我那么相信这些人物是真的话,我并不会拍,所以我很早就决定了。这也是阿乐这角色一个很重要的演绎基础。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日杀他妈妈的是他自己,还是他的病?甚至会不会是有意识的,认为这样会对她妈妈比较好? 有一个镜头是,镜子裂了三片,阿乐也在演绎中不停思考,怎么去做,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与演员沟通的核心就是,除了他知道自己令他妈妈走了之外,他一直都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他杀了他妈妈。这个留白也给了演员更大的空间去表演。说回距离,我觉得我自己是偏冷的,尤其是戏的前三分之一到一半,到后来我就近了一些,镜头上能反映出来。
虹膜:镜头上有、情绪上也有,可以清楚见到一个导演在很有意识的演绎什么。
黄进:对,这个也是有很大压力的,要很真实、很认真的去处理这个题材。也在于我作为一个作者,要为这个电影的视点、姿态负全责。
虹膜:刚才你说方皓玟在踩着钢线,我觉得你也是这样。
黄进:是的,很少人能够理解到这点。

虹膜:电影中有一些重要场景发生在教会。你跟编剧陈楚珩有没有这方面的宗教信仰?
黄进:我俩都没有。我们各自曾都有过教会生活。中学的时候我是基督教的,我小学是天主教,但这个都不是重点。教会那场戏我们不是在指向、针对信仰宗教,我们是在指向人。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很高举你的爱,你怎么做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不是的,对方接到的才算。
你的意图是个源头,对方收到的又是什么呢?可能是个炸弹。我们如果很爱对方的话,是不是更加需要去学对方需要什么?不然什么都是空谈。 不是说教会是这样,其实人都是这样的,信仰当然是导人向善,但是地上的人执行的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多提醒自己的。
我们心爱的人有没有因为我们的爱而被爱,我们有没有真的了解过对方,如果没有的话,你发出的爱对方收到的时候就已经变了。演员方皓玟和我对此有很明确的共识。她演教会那场戏很自主,能够调整得很好。
当然在演出的时候,她也有自己也看不完整的东西,我们就去提醒她,因为她的表演功力,过程比想象之中简单。其实我作为一个导演无法表演出来,反而她作为一个演员能很好的操控自己。

虹膜:处理教会的戏份,也是很大的挑战。你拍这场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小心些什么?
黄进:其实没有,反而现场拍的有些就是基督教徒,这个演不出来的,信徒或非信徒都要多思考,我们爱他人的同时,对方有没有被爱到,是不是我们满足自己就算了,所以我也是很坦白在做这件事。有人不舒服的话,也就不在这场戏里面了。
虹膜:那电影片名呢,是谁选的?是否与佛教有关?
黄进:这个片名《一念无明》是编剧陈楚珩选的。其实当初我们写完之后,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片名,首先想到英文标题Mad World,很好理解,世界疯了,「疯的不是人」。
但是《一念无明》延伸得更远,更加贴切,是说你有没有看到事情的实相。我们一直追逐的决定、执着,其实是不是不需要的?真正的珍贵的我们并不知道,里面很多关系都是这样,相爱的人互相伤害。
或者是一些愚昧、不了解产生了互相伤害。电影中很贯彻的就是,真的没人特别坏,但我们看的不清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虹膜:你既是导演,也是剪辑。电影也不是跟随事件顺序而来的,有很多跳跃,有很多平行剪辑。其实剧本是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样的叙事策略,还是你在剪辑的时候再创作的?
黄进:其实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跟剧本的,整个重点大致一样,还原程度很高。我们没什么心思在现场再创作,因为我们没时间。与原剧本相比,有一点比较不同。我现在剪的这个版本是将金燕玲的戏份再散开了一些,剧本中就更聚拢一些。
因为我剪得时候我想她再「阴魂不散」一点,再缠绕阿东多一点,那阿东与父亲之间的情感、关系其实最后都是指向妈妈。这样观众通过金燕玲的这条线索,可以对这一家人的关系有个整体的关照。
虹膜:你之前在香港城市大学,是谭家明导演的学生,修过他的什么课程?
黄进:全部,他主要是教script writing, directing和editing(剧作、导演和剪辑)。

谭家明导演
虹膜:除了谭家明之外,电影这一块,你的养分有没有来自哪个导演、作家?
黄进:其实很窄,未必能在我电影里面体现。比如说杜琪峰。他对画面的想象,节奏的想象,给我很大的启发。韦家辉那种宿命感——他们两位也是这样看事情的——用一种神一般的角度去看事情,有时候很直观的,很影响我。
我也曾在银河影像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跟游乃海写剧本。跟他写剧本的方法和我以往的方法很不同,虽然很难说如何不同,但也是影响到了我。
另外Michael Haneke,启发我如何看待电影、人物,一个作者的世界观是怎样。当然技艺很重要,但有时候更重要的是作者的世界观,他是怎么看的。同一件事同一群人,不同的导演做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看世界的方法不同。更深一些,我很喜欢Steve McQueen。

Steve McQueen作品《饥饿》(2008)
他与Haneke有些相似的地方。Steve就更流动一些,有一种很强的人文关怀,但同时也很批判。不是正邪批判,而是想说每个人都是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只不过在历史里面身不由己,互相伤害,比如《饥饿》中的人物,Suffer得很紧要(受尽磨难),却没有谁是坏人,只是各人在这个历史或政治的漩涡里面身不由己,互相伤害。
导演强大的不是关于技艺、调度,而是在于看问题的方式。
虹膜:你和编剧陈楚珩喜欢的导演、电影相似吗?
黄进:她永远比我走得近一些。她很喜欢塔可夫斯基。情绪上流动很多。我比较冷一些,看的也可能宏观一些。但她的东西对我来说很珍贵,她永远dig(挖掘)得到一些我dig不到的很深刻的东西。

虹膜:所以这种组合出来的效果很奇妙。
黄进:对,如果用她的方法去拍,就是另一个《一念无明》。就说那个距离问题,我没有认为我的距离是特别的,我只是直观地去做。
虹膜:在一些报章的采访中,你提到和编剧陈楚珩存了很多题材。你们之后再拍电影的路线或者定位会是怎样的?
黄进: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筹备下一部电影了。所以之后发生的事无论好不好,都没有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拍的不好的东西,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我们要进步的地方我们很清楚。那么之后有很难得有大家的肯定,我们自己回首再看是不停摇头叹息的,会发现有些地方距离自己的期望还是差了一点。
下一部电影未必会一样的写实,是一部没有什么明确的议题的电影。我相信电影是个很强烈的媒介,可以影响他人,不是站在一个高地。我们希望换一个类型看到一些不同的观众,但我们创作的初衷不会改变——寻找情感的真实。如果你当电影是个Art Form, 内容是没有变过的,但是form我们会继续探索。

《烈日当空》(2008)
虹膜:我看到《一念无明》的执行监制是麦曦茵(曾凭《烈日当空》200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导演提名),城大毕业的,她在这部电影有帮忙,你们是不是在城大就认识了?
黄进:对,她是我的师姐,大我两三年。她在这个电影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除了一些监制上很实际的工作,她也很理解一个新导演面对的纠结、创作的状态、空间。因为她也经历过。她曾经也是个很新的导演,所她很明白我创作上面的状态,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很多时候她是我的心灵导师。她明白我需要什么,有时候可能我需要多些空间,有时候她知道我需要时间,有时候可能我需要一些建议,她能够明白。一个和我很接近的人能帮助我,我很珍惜。
虹膜:《一念无明》会不会在内地上映?
黄进:会的,应该会迟一些(注:已于4月7日上映)。
虹膜:版本上有区别吗?
黄进:应该内容上就没有,你也可以看到没有什么敏感话题。

虹膜:那你接下来是否会到内地去拍戏呢?
黄进:我不抗拒。有时候这个问题会被曲解成你是否会妥协。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合拍片甚至国产片,都是一种做电影的方法。你需要用什么方法去完成一部电影视乎电影需要什么。
每个作品都是独特的。我是为了创作去拍电影,而不是为了做一个导演去拍电影,所以我更需要聆听作品需要什么配套,聆听这个BB(婴儿)需要什么,如果下次他说他要回大陆,他要这样的配套,如果有很合适故事,那我会去做。
但暂时可能不会,因为我未必能驾驭到,我想先做好眼前的东西,但是态度上面我不抗拒不反对。很坦白说有很多导演是需要这么一个制作规模和资源才能够发挥他动人的地方。很多香港电影人如果不拍国产片、合拍片,哪能拍出那么多精彩的东西?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形式就不去做,去否定所有。

虹膜:如果拍摄《一念无明》时有更充裕的资金,你会用在哪里,是后期的制作,还是其他?
黄进:我会想让故事说慢一些,现在整个电影有种太准确的感觉,就像所有东西就是做好就走了,效益有点高,因为我们没有资源,能拍完就很厉害了。如果多一点资源,我未必会加一些特别的内容,我会想说慢一些,然后希望各个岗位的人会有更多资源去做事,无论是音乐还是美术。
美术就借了很多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些岗位可能是义务来帮忙的,演员也是。各个岗位都是算一个艺术家,我作为一个导演有责任给他们相应的空间去给他们创作,反而给人压抑、局限我也不开心。所以我不想做一些天翻地覆的东西,我想大家都放慢去做,或者有充足空间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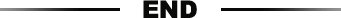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
精彩内容
影向标 | 《一念无明》并不完美,但他偏要给10分
这就是去年最棒的香港电影,忍了一年终于可以推荐了
曾经是香港最具独立精神的导演,如今也堕落为投机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