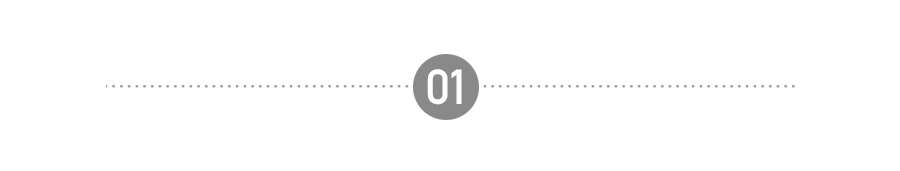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捧哏
2023年年初,董润年拍完了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年会不能停!》。同年底,电影上映,因为切中当下的职场生态和官僚主义,既讽刺,又鲜活轻松,获得超10亿元票房和豆瓣8.1的高分,成了年度黑马影片。
在《年会不能停!》的首映礼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说,董润年的天津人基因终于觉醒了——这部电影董润年也是编剧。
“其实我是天津人里最不幽默的。”董润年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从血缘上来说,他祖父母来自山东,爸爸在北京长到八岁时去了天津,但知青时期在哈尔滨度过,与哈尔滨姑娘结婚、生子。董润年家从不说天津话。他和同学聚会,“所有同学都比我幽默。”
他更擅长贫嘴、接下茬,放在相声里,就是捧哏。除非技艺超群,捧哏往往是舞台上的配角,但实际上捧哏需要掌握比逗哏更多的段子,才能时时点破或深化。这似乎也是他的天性使然,对抒情和崇高过敏,时不时想戳破它们一下。“和朋友相处,或者自己在家,也是爱说个怪话,有一种想要解构严肃和正经的欲望。”
因此也很好理解,从毕业后第一次编剧写《清明酒家》到《年会不能停!》,董润年写了不少喜剧。
2024年11月,他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播出,《不讨好的勇气》。主角吴秀雅过着外人看来的舒适生活,在大公司人人挤破头想进的内宣部谋职,与颇有前途的男友谈婚论嫁,如果不是意外讲了一次脱口秀,她大概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哪里有问题。
《不讨好的勇气》(以下简称《勇气》)和《年会不能停!》(以下简称《年会》)的剧本创作是同步进行的,并且共享了一套故事背景和职场素材,但它们又是截然不同的戏剧尝试:
《年会》通过一名钳工被错调、官升三级的故事来揭示大公司这个系统如何被维护,《勇气》则假想了它的反面,在系统中兢兢业业工作的人真的过得好吗,如果要从这个系统中脱离出来,很可怕吗?24集电视剧,本意是侧写一种脱口秀行业的初始生态,同时讨论职场女性的处境,更深一层,是鼓励对自我保持诚实、勇敢。
大公司是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社会场景之一,人的社会化、新的劳资矛盾乃至整体的时代氛围,都在其中发酵。它像极端高压的战场而使董润年十分着迷。从2017年到2022年,董润年陆续采访过不少打工人,第一轮采访,大家都在抱怨领导和公司;第二轮,更多人开始焦虑,对经济形势产生隐忧;第三轮,无论如何要保住一份工作成了打工人心态的最大公约数。
其中最让董润年感到好奇的是,“一个好端端的人进去(职场)就异化了,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看那些上班的人,“好像人人都会(上班),但据我观察,也不是真会,有人在那假装,假装好像应该怎么样,甚至这些假装我都怀疑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
《年会》与《勇气》都是对表象的戳破,前者以讽刺,后者以治愈。

▲《年会不能停!》 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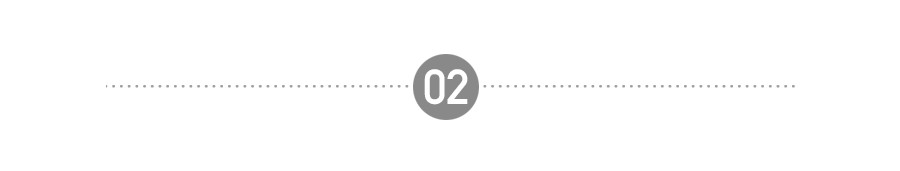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棒喝
董润年15岁的时候就想成为导演,因此高考前独自前往北京参加了艺考。他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到研究生毕业。但是毕业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做编剧。
起初其实运气不错,他没当过枪手就有了正式署名的情景喜剧,导师带着他一起写的电视剧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但这时候他单独去见导演、演员们,却发现对不上话,被推翻、拒绝。有一回,他写的剧本已经拍完一半,还被叫到剧组去,说是需要调整。去了,聊完,他才发现自己原本写的后半部分几乎要全部重来。
渴望被认可而不得,又害怕冲突,董润年那时候有了讨好心态,“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东西,为我做的工作而满意而开心,逐渐就会答应很多可能不应该的诉求,比如交稿时间,或者剧本的改动。”
最颓丧的时候,他有话但不说出口,听到电话铃响就会心跳加速,避而远之。他也没办法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因为不敢见人,更别提和他人共处一室办公,只好整天昼伏夜出,埋头写作。如果没有人找他,他就半个月不出门。
“整个人面无血色。”他的妻子、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工作搭档应萝佳说。偶尔应萝佳拉着丈夫出门逛街,也感觉他心不在焉,“我就会觉得说,你没有活在当下,很不尽兴。”
那段时间董润年反复问应萝佳: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编剧。“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不写),因为他真要放下,真觉得自己不适合,他不会这么问我。”应萝佳说,她大多时候还是鼓励董润年,也帮他想过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扭转作息。
因为在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剧组担任制片人,应萝佳每周都要和编剧李晓明碰头开会。李晓明说他早睡早起,长年在上午写作。这个方法被应萝佳带回家,告诉董润年,并很快起效。
“在我身上,它确实是改变我焦虑状态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有时候极大的内耗,其实是那件事情一直拖着不敢碰。”董润年说,早上就开始写作可以减少内耗,况且,“这个行业的特点是熬夜比较多,早上确实没人打扰你。”
写到2009年,一天下午,董润年忽然觉得自己会写了。“差不多就是这个点。”他停下,掐了一下手机,屏幕显示下午4点半,“可能就是写的字数足够多了。”他粗略估计每年要写60万字,写就是他的方法。
“以前我老觉得说要保情节,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后违背了人物内心的发展,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两者并不完全是矛盾。”这样的顿悟时刻,在禅宗里叫作“棒喝”,棍棒击头,或对其大喝,以启悟对方。
“血色又回来了。”应萝佳笑。
那之后,董润年与导演管虎合作《厨子戏子痞子》《老炮儿》,为导演宁浩编写《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剧本,并且在2019年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成了电影导演。
在《不讨好的勇气》中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吴秀雅误打误撞在酒吧讲了一次脱口秀,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那家酒吧的招牌上两个字一大一小,远看像“捧哏”,近看是“棒喝”。

▲《不讨好的勇气》 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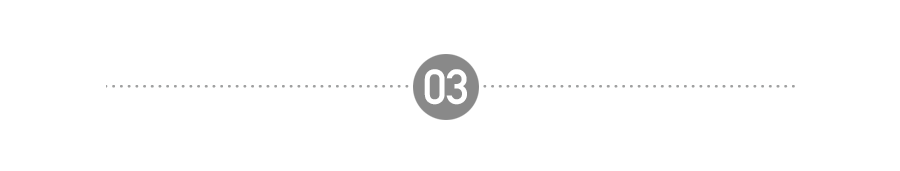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剧作的螺旋
与董润年的温吞内敛不同,应萝佳是个直爽的南方人,浙江省慈溪中学的最佳辩手。她和董润年在大学时认识,毕业后结婚。
头十年里应做制片人、宣发,董只管写剧本,相安无事,甚至可以互相支持,互为主心骨。比如应萝佳在职场遇到难处,会寻求董润年的建议;董润年每次写完剧本,第一个就给应萝佳看,结果往往是被指出漏洞,气人的是,妻子往往是对的。
“这个事我有一阵子怀疑过,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不正常啊。我说是我运气太好了呢,前辈子积德遇上这么个人,还是怎么着?”应萝佳说,“直到我们开始一块儿工作。”
“说明同事就是地狱。”董润年在一边幽幽接了一句。
应萝佳发现自己有些想法无法再转述给他人的时候,她决定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年会》和《勇气》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俩的争吵变得频繁且激烈起来,“(生活中)有些事他其实让着我,但是工作没法糊弄,创作就是容不得半点虚假,不对就是不对。”
不过他们多数时候吵架时间短,半天到三天不等,最后还总能吵出一些新想法。“在吵的过程中才真正明白我们在表达什么,有时候就是他写的东西我误读了,我按我的理解出招,然后开始别扭,吵着吵着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把真正的表达写出来。”应萝佳说,“还有就是,我们互相在很生气、很拧巴的过程中,倒是也能激发一些潜能。”
比如2020年,董润年和应萝佳因为《年会》的剧本大吵一阵,濒临放弃的时候,他们冒出了写一部关于脱口秀电视剧的想法。那一年,《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播出并破圈,线下脱口秀行业蓬勃发展。
过完年,董润年和应萝佳就去了一趟上海,跟三十多个脱口秀演员见面、采访。“跟年终做述职汇报似的,一个一个往办公室走,你是12点到1点,我是1点半到两点半。”脱口秀演员童漠男说,“比我们董事长问得还细,咱们董事长都没有问过我们,什么事你怎么想的。”
这些脱口秀演员后来都参与了《年会》和《勇气》的拍摄,担任编剧、策划甚至演员。童漠男经常被叫去参加剧本会,他没见过应萝佳和董润年争吵,倒是经常见到应萝佳把剧本推翻。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就差那么一点。”应萝佳以前经常这么说——董润年又在一旁捧哏:“天亮了以后还是会黑的。”
现在她说:“做影视剧就是螺旋式上升。”
“螺旋式上升,这是我跟应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童漠男简直快要击节赞叹,“在我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应老师就如此开导我说,这就是螺旋式上升,漠男你不要慌,大家不要慌,稳住。”
《年会》的剧本写了五年,完整的剧本被推翻过七八次。但2021年《勇气》启动后,两个剧本交替进行,其中一边卡壳,就切换到另一边。《勇气》的细腻、顺遂消解了《年会》的焦灼。
虽然将背景设置在2015年的《勇气》与当下语境存在时差——脱口秀行业在九年里经历了火爆、暂停和复苏,打工人心态也渐趋保守,时代已经转变风向。但对于还在不断摸索、尝试新内容的创作者,它切实地提供了抚慰。
“有一段我们会陷入这个项目(《年会》)是不是根本不适合我们?其实做不起来?要不别做了。到这儿再去写《勇气》,在那写主人公怎么去突破,怎么鼓起勇气。跟我们的创作心境非常像,要鼓起勇气去碰《年会》,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互文照应。”应萝佳说,就像从未来的全知视角看眼下,“是不是我们也坚持一下,就可以有所突破?”
如今看来,也正是应萝佳所说的温情、积极,和董润年对崇高的习惯性消解、对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好奇,共同组成了《年会》和《勇气》的底色。

▲制片人、编剧应萝佳 图/受访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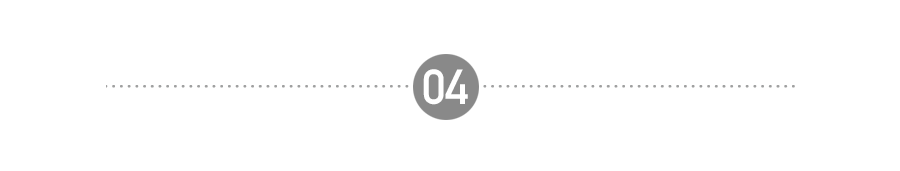
不讨好谁?
“其实‘不讨好’后面缺少一个宾语,就是说,不讨好谁?”在第一次采访时,董润年说,“我们天然地会认为是不讨好别人,但其实当你要面对自己的时候,也不能讨好自己。”
在他的故事中,人物百转千回,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迷宫。《被光抓走的人》讲的是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也是对自我的不坦诚;《年会不能停!》中胡建林、马杰、潘怡然发现了那些矫饰的自我麻痹的东西,必须作出抉择;《不讨好的勇气》里,吴秀雅与男友郑昊分手,理由是以前的她有所掩饰,但郑昊说,如果你一开始展示了真实的自己,未必我会不喜欢你。
“你真的了解你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当你面对真实的自我,你接受得了吗?你承受得了自己真正的内心吗?”董润年重新讲到了毕业时那段颓丧时期,焦虑有一个非常具象的表现,“就是我每天快结束的时候都会回看这一天,然后充满了懊悔,哎,我刚才要是多写一点就好了,或者打电话的时候那么回答就好了,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但后来我觉得引发这种内耗的重要原因,其实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才总是在做一种实时的反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真正的松弛和快乐的源泉是你能自洽,能够接受自己的欲望、不足之处,接受自己的渺小和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差距。”
他一直知道自己想做导演,但做导演“是个概念”,并非一劳永逸的事,他需要不停问自己的是,做导演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把自己的观点传达出去获得共鸣,还是为了创造这件事情本身?
做导演甚至是一件越来越复杂的事情,“其实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观众都在流失,观众可能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看短视频,对我来说,讲什么东西就变得很重要。现实主义的创作最根本的是要探讨新问题、探讨真问题,只有这两个,观众才有可能来看。”董润年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难度是,任何事情我们都很难形成共识。当观众对这个东西形不成共识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表达?”
后来他发现自己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中途有一阵子忘记了。他说起初二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1995年,世界电影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开始引进好莱坞大片。董润年看的第一部是《亡命天涯》,第二部是《真实的谎言》,第三部是《阿甘正传》,第四部是《狮子王》。
看完《阿甘正传》,董润年很震惊,从没想过电影可以这样拍。回到家他开始默写整部电影,那是他人生中记下的“第一个剧本”,他觉得特别开心。
直到今天,他仍觉得创作本身确有其迷人之处,“我们在模拟一个世界,这就像科学家在做的事,通过模拟试图找到某种世界运行的真相,去解释它,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人的命运到底是被什么左右的?我后来意识到我做导演,其实真正痴迷的是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