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白先勇先生在豆瓣上讲《红楼梦》,引起了很多网友围观。
鱼叔一下子就想起,曾经给你们安利过根据白先生小说改编的两部电视剧。
描写同志群体的
《孽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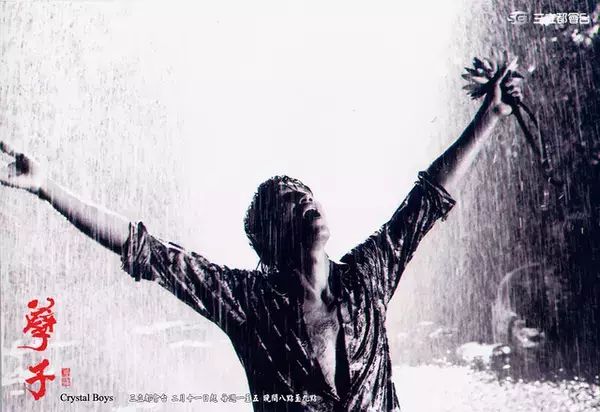
描写1945年代空军爱情故事的
《一把青》
。

其实,台湾还有很多
文学大家
。
有趣的灵魂太少?那是你书读的太少。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套纪录片——
他们在岛屿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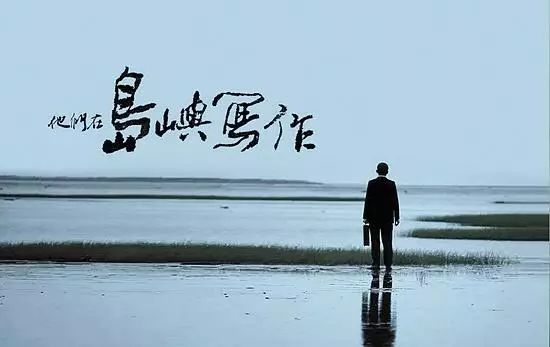
这是介绍台湾文学大家的系列纪录片。
最初2011年制作的有6部。
分别是:
以
林海音
为主题的《两地》;
以
周梦蝶
为主题的《化城再来人》;
以
余光中
为主题的《逍遥游》;
以
郑愁予
为主题的《如雾起时》;
以
王文兴
为主题的《寻找背海的人》;
以
杨牧
为主题的《朝向一首诗的完成》。
2014年到15年,又增加了7部。

每一部都取得了不错的分数,可看过的人却寥寥无几。
今天,鱼叔就来重点推荐下其中一部——
他们在岛屿写作:姹紫嫣红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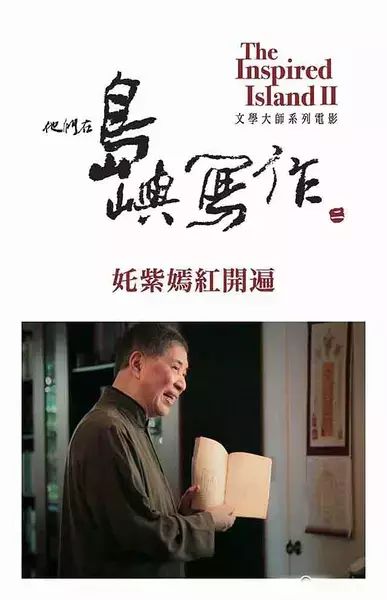
这是一部关于白先勇一生著作和事业的纪录片。
“文学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志业。”
一听白先生的第一句话,很多怀有文艺梦想的人就要泪目了。
多少人能够说出这句话,把文学当成是一生的志业。
白先勇自述,他的一生对于一些人物,对于一些
被流放的边缘人
,有一种心理上的
认同,和
同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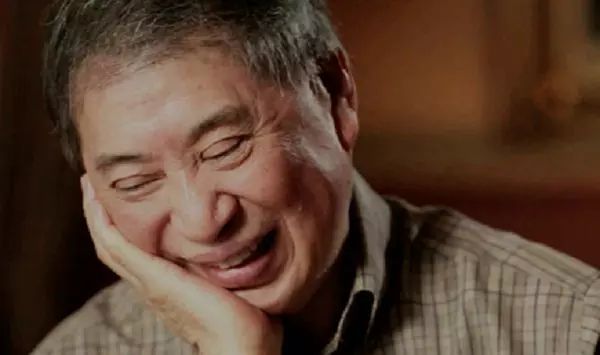
曾经,法国《解放报》做过一个采访,问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
你为什么写作。
白先勇说:
我写作,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那种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
他真的做到了。
正是因为他对人类心灵痛楚的同情、共情,才让他能创作出一部部打动人心的作品。
这样的想法,跟他的毕生经历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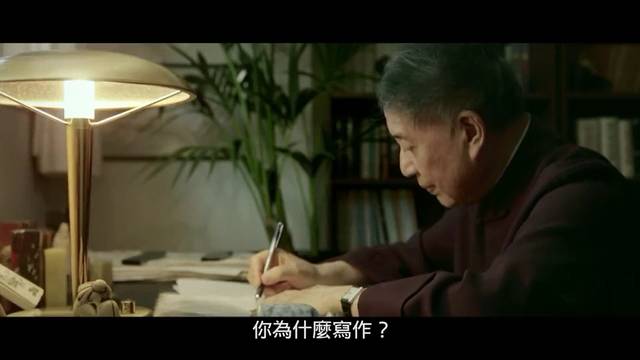
1937年,白先勇出生在
广西桂林
。
桂林是他的根,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就不多说了。
只说一个细节。
当他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之后,受邀回到桂林。
他一顿三餐外加宵夜必须要吃
桂林米粉
,正常人吃二两就能饱了,他要吃三两。
吃完还不过瘾,还要再加一碗。

别人都怕他撑坏了。
他却说,
乡愁是填不满的
。
桂林米粉的味道,是他记忆中童年的味道。
1947年,他才十岁,在上海养病。
生肺病的四年时间,他
完全独处,与世隔绝
。因为怕他传染给家里其他孩子。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被
打入冷宫
。
正是因为自己
有过病痛,有过孤独,有过与世隔绝的苦楚
,所以他从小就非常
敏感
。
对别人内心的痛楚更敏感,感受力更强。
他说,那个时候开始就喜欢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浪漫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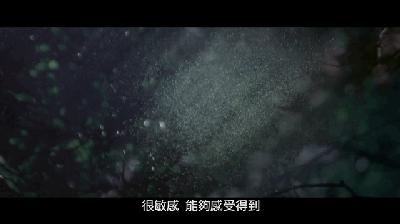
上大学时,他跟几个同学
办文学杂
志
,内容以新、以善、以真为主,取名为《现代文学》。

好像要自己弄个五四运动出来。

当时办杂志,一群穷学生向成名作家约稿,很难。
小说数量不够怎么办呢,白先勇就自己写几篇,所以才用两个笔名。
《玉卿嫂》、《月梦》
都是那时候的作品。
编辑写稿印刷都自己来搞,穷得不能再穷的杂志。

“明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明知赔钱,也在所不惜。”
现在读当时写的这些年少轻狂的字句,白先生笑到不行,
“那时候口气大得很呢,在老师前不知天高地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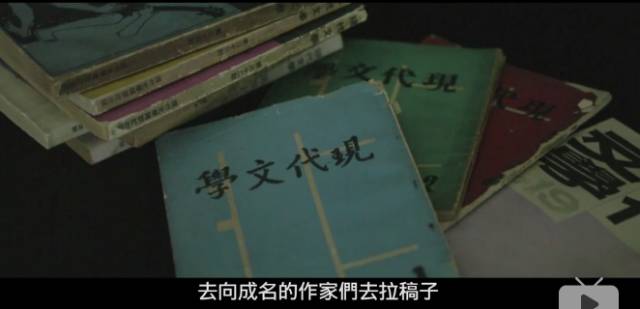
台湾戒严时代,气氛比较
保守和肃杀
。
但是还有一个小空间,给文青发挥余地,所以
文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寄托。
那时候他们说自己
是“迷你文艺复兴”
。
很多后来有名的年轻人,都曾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包括
施叔青、三毛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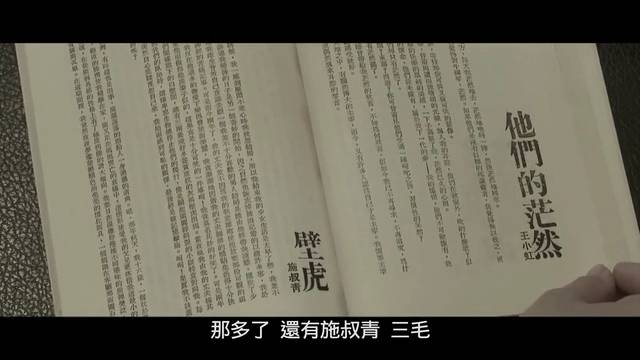
当时办杂志,
以文会友
,交了一堆朋友。
现在想想,白先勇说这是自己在
文学上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

1963年,母亲去世,他就要到美国去念大学,课业又重。
那一年是
极为沉重的一年
。
他大病一场,胃出血,差点死过去。
来到美国之后,就开始创作
《台北人》和《纽约客》
。
《台北人》是一本合传,有将军,有夫人,也有普通老百姓。
从南京迁到台北的这些人,他要写的是这样一群人:
金大班、尹雪艳、朱青、钱夫人。。。
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命运,但其实是时代命运。
人们飘零之后,就会寻找一个归属,精神归属。
他记录下了时代变迁下这些人的飘零,在小说中收容了这些人的苦痛和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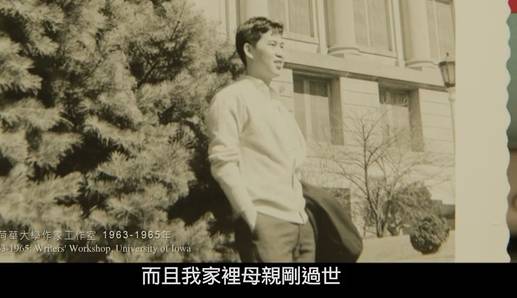
即便到了美国,他也没有停止对《现代文学》的关注。
杂志缺钱经营,他就把自己的薪水、房子、稿子全都搭进去。
《现代文学》停刊几年之后的复刊,对他来说有很大意义。
复刊之后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逼着白先勇把
《孽子》
写出来。
在他的好友看来,《孽子》的最大成就,就是可以认同台湾也能开展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可以代表
岛上的生命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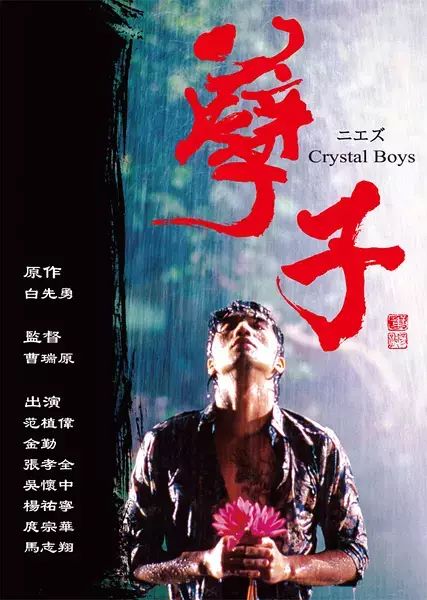
《孽子》改编的电视剧,鱼叔之前推荐过。
与现在比,在三十年前的社会,
同志还是个社会禁忌
。
但是,白先勇说,他写的是同志题材,但更重要的是
同性恋的人
,人字很要紧。
父子、母子、兄弟、爱人之间的情感,这才构成一个人。
当失去家园之后,他们寻找一个立锥之地。
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
有时候一点点的相濡以沫,就是人生的一点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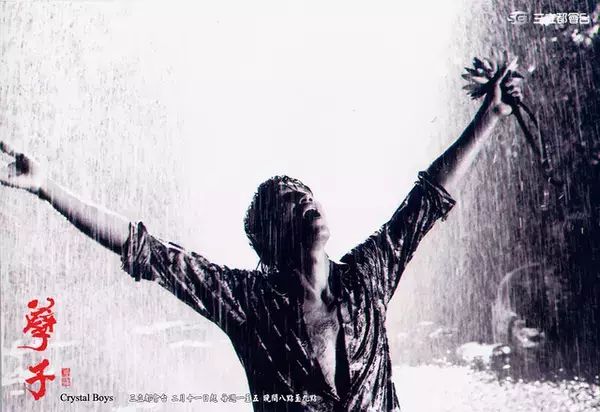
他的老朋友以前问他,你想干什么啊。
他说想
开孤儿院
。
写了《孽子》之后,他朋友说,你的这部作品就是一座孤儿院。
同志被父亲、被家庭、被社会、被父权性的象征机构放逐,他们精神上变成孤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能够使得天下苍生有所庇护,容纳不为社会所容之人。
他在《孽子》中,为这些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所。

在拍《孽子》电视剧之前,也是经历了很多周折。
当时公共电视正好要拍这部剧,但这个提议就遭到了怀疑,
又是公视,又是八点档,
这么敏感的题材能行吗?
但是在播放过程中,有一个家长打电话到电视台,问可不可以加一个字幕。
他说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儿子,希望他能看到这个快回家。

看了他的作品,更多的人明白了、理解了自己原先不曾理解的人事物,这是一种莫大的收获。
白先勇一直为他人提供心灵上的庇护所。
但是,当别人问他,你的家乡是哪里。
白先勇一下子答不上来。
因为他出生在广西桂林人,但很小就出来了,在台湾也住过一阵子,后来在美国住了很久。
他认为,家乡不是地理位置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
他说,
自己的家乡是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觉得好像回家了。
他对于昆曲的喜欢,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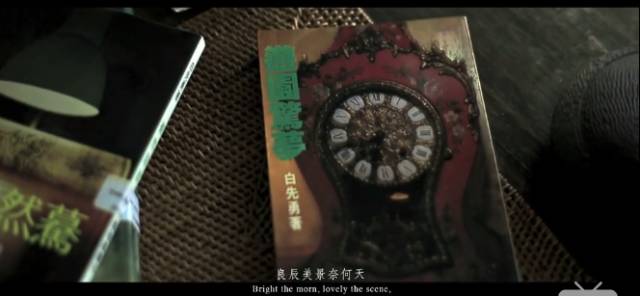
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改写
《游园惊梦》
,第一次把昆曲搬上舞台。
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又做了
青春版《牡丹亭》
,开始公映。
十年后再回头看这一路走来的过程,他觉得还算做出了点成绩。
很多人对他的做法打个问号,《牡丹亭》里的爱情那么缓慢,现在年轻人真的会喜欢?
他很笃定地说,会。
因为这是我们斩不断的根。

他会做这个事情,还跟自己的经历有关。
在这之前搬一盆佛茶花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医生告诉他,两条血管已经堵塞了90%,立刻拉进手术室手术。
这样
大难不死
之后,他觉得是佛要他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一来,他就动了念想。昆曲的振兴大业,他必须参与进来。

一个民族的灵魂,就在于他的文化。
而当时的昆曲中,演员老,观众老,表演方式守旧,吸引不了年轻观众。
他打破时空,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写。他开始
革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