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全国大部分地区酷暑高温,这里发掘一点女性所经历的沉重历史,在漫长炎夏为大家带来一丝寒意~
 现代产房已经看起来整洁、文明,但仍然给人以孤独、隔离之感
现代产房已经看起来整洁、文明,但仍然给人以孤独、隔离之感
生育是属于女性的,男性在漫长的历史中鄙视它、贬低它——这来自于对生育本身的鄙视——在绝大多数文明中,丈夫被隔离在生育过程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认为生产过程“不洁”,这不仅是指实际意义的血污等,也是指对于女性生殖器官、女性生育力的妖魔化认知。
许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禁忌,女性的月经和生育被视为不洁,在基督教文化中,女性的生殖器官被视为魔鬼的象征,在一些文化中具有神秘的能力。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写道:“‘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

女性生殖器官在许多文明中被视为拥有神秘的力量
现代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试着对其进行祛魅以及反污名化
许多文化将女性的生殖力量视作原始、神秘的,这可能反映了男性对于女性把控生殖过程的焦虑。
人类学家发现一些地方有过“产翁制”,即在女性生产时,男性也在屋里做出要生孩子的姿态,当孩子出生,丈夫就会把孩子抱过来“坐月子”,而女性则马上起来恢复一切劳动,大家前来看望丈夫,并且对于丈夫的“劳苦功高”进行安慰和祝贺。这种看起来非常怪异的制度一般被解释为男性想在生育活动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的努力。
当男性的努力并不以如此直接而且怪异(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啊)的方式开展时,男性就可能出于对女性生殖力量的恐惧,而对其进而进行文化上的贬低。
生育过程被视为不洁的,生育过程中和生育过后的妇女在许多文化中被视为带有不良物质或者力量的存在,例如在印度的一些地方,目前在分娩时和分娩后的十天都是“不可接近”的,在中国,长期的传统也是男性(包括丈夫)不可进产房——目的当然并不是消毒,也不是“男女大防”。这除了将女性生殖活动视为“不洁”以外,也可能与生育常常带来疾病和死亡有关。
在许多文明中都能找到针对生育过后的女性进行“净化”的仪式。
在佛教中(佛教是一种在教规上非常歧视女性的宗教,在性别平等这一点上远不如道教)还有针对女性生育之“罪愆”的《血盆经》,因为根据传说,妇女生育过多会触污神佛,生育对于妇女来说是罪业,会死后堕入血盆地狱。“血盆”自然是对于女性生殖器官和生殖过程的恐怖化描述。这些文化上的渲染在很强程度上造成,或者进一步加强了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负罪感和厌恶感。

不过《血盆经》算不算佛教经典也有争议,
这是一部融合了中国的孝文化的、后来才在中国流传开来的经书
和其他领域一样,产科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之中)。严格来说生育并不是一种疾病,在漫长的历史中,生育被视为自然,在人们的家中得到处理,而并不作为医学的对象。女性自己处理它,可能与其它动物的做法并无区别。18世纪的医师描述印第安人的生育过程:“自然是她们唯一的接生婆。她们的生产过程很短,几乎没什么痛苦。每个女人都在一个私人的小屋里生产,甚至没有一个同性别的人来服侍她。在冷水中清洗自己过后,没几天,她又回到她平时的工作中。”但是,人类的生育是一切动物中最为困难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直立行走使得骨盆变小,另一方面人类的头颅增大。可以说,这是进化的代价。上面对于印第安人生育状况的描述应该是顺产的状况,在存在难产的情况下,这样的自然生产过程可能就要遭遇死亡,这时候就需要更加专业的人士介入。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营地》就记述了一位白人医生去印第安营地帮助一位难产的印第安妇女手术并且为她接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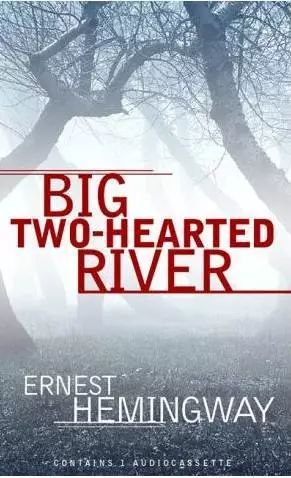
《印第安营地》是海明威杰出的短篇小说,收录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大二心河》中,这部短篇小说集以尼克·亚当斯为主人公,写出了一代青年在一战以后万念俱灰的心理氛围
在这一含有女性最隐秘也影响最深刻的体验过程中,女性互相扶助,但扶助者在历史中是完全无声的。
在漫长的历史中,医学依赖经验,是经验的汇总;因此,妇女更适合接生——男性不可能具有生育的经验。在绝大多数文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在产房里忙碌的往往是一些年长的女性,她们由于经验而被视为可靠的被依赖者。这里涉及对接生婆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产婆往往被视为落后和野蛮,在许多现代人熟悉的文艺作品或者是资料中,产婆往往是这样的形象和作为:
“他还记得那个接生婆,把那些锈不拉叽刀刀铲铲放到火上烧一烧就向里捅,秀秀可倒霉了,血流了一铜盆,在送镇医院的路上就咽气了。成亲办喜事儿的时候,二蛋花了三万块,那排场在村里真是风光死了,可他怎的就舍不得花点钱让秀秀到镇医院去生娃呢?后来他一打听,这花费一般也就二三百,就二三百呀。但村里历来都是这样儿,生娃是从不去医院的。所以没人怪二蛋,秀秀就这命。后来他听说,比起二蛋妈来,她还算幸运。生二蛋时难产,二蛋爹从产婆那儿得知是个男娃,就决定只要娃了。于是二蛋妈被放到驴子背上,让那驴子一圈圈走,硬是把二蛋挤出来,听当时看见的人说,在院子里血流了一圈……”
——刘慈欣《乡村教师》
“收生婆已经守了七天七夜,压根儿生不下来。偏方儿,丸药,子孙娘娘的香灰,吃多了;全不灵验。到第八天头上,少奶奶连鸡汤都顾不得喝了,疼得满地打滚。王老太太急得给子孙娘娘跪了一股香,娘家妈把天仙庵的尼姑接来念催生咒;还是不中用。一直闹到半夜,小孩算是露出头发来。收生婆施展了绝技,除了把少奶奶的下部全抓破了别无成绩。”
——老舍《抱孙》

传统的产婆形象
这些令人冷到骨髓的故事将产婆与文明彻底对立。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肮脏、愚昧和残忍的产婆和接生方法。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产婆承担了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接生任务。
在芭芭拉·艾伦瑞克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的《女巫、产婆和护士:女性医治者的历史》中,她们介绍了男性医学精英的崛起是如何建立在对于女性医治者的迫害和抹杀基础上的:她们被套上巫术的罪名送上火刑架,又在近代科学的话语体系中被任意描绘,作为肮脏、无知和迷信的象征。
一些医学史学者宣称,产科与其它医学领域相比发展更慢,是因为女性长期垄断这一行业;更多的医学史学者宣传,只有男助产士完全取代了女助产士,产科学才能成熟。这样的宣告背后的观念是:女性是愚昧的,只有男性才代表了进步、技术、科学和光明。但是,在漫长的经验医学过程中,女性用经验引导了生命的传承,用血肉之手承担了重任。接生婆掌握了大量与女性生理结构有关的知识,但她们并没有把这些知识系统化。由于女性往往既不掌握文字,更不掌握话语权,她们的知识可能仅仅限于口口相传;许多产婆可能根本不识字,更不用说拿她们的知识加以理论化和发表了。她们积攒的知识和技巧并没有形成诸如论文、专著这样的作品,更没有进入医学院。这也就阻碍了这些知识量上的积累和质上的飞跃。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雅典的接生婆对于女性的生殖系统了解比希波克拉底更多,但希波克拉底被奉为西方医学始祖,而雅典的接生婆却没有留下姓名,更糟糕的是也没有留下她们的知识。由于对于解剖的禁止,关于怀孕、分娩和催生方面的知识完全来自于女性自身的经验。男助产士所写的书则错误百出,描绘胎儿和子宫的图片位置完全错误,直到哈维根据解剖才正确地描述了女性生殖器官。
在我们熟悉的影视剧中,“烧开水”已经是古代产婆的标配,用以洗手和可能用到的器械(例如剪刀);但近代产科学一个非常著名的曲折就是产褥热——许多在医院分娩的女性很快高烧死去,而在自己家中分娩的妇女却安然无恙;维也纳的医生赛迈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通过调查发现这可能与解剖尸体的习惯有关,而那时候医生并没有洗手的习惯。那时候还没有对于细菌和病毒的认识,因此赛迈尔维斯提出“死亡微粒”,认为医生的手把死亡微粒带到了新的病人身上。这一发现引发了医学界的狂怒,因为这种说法亵渎了他们“神圣的洁净”。赛迈尔维斯被送进了疯人院,知道巴斯德发现的细菌证实了感染的机制,洗手这一要求才得到实施,200年的产褥热才走到终点。

现代产科是男性书写的学科。女性的贡献或被抹去,或被带着鄙视描述为野蛮和落后





